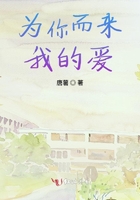安奇刚眉头紧锁,说道:“他们不知用什么办法威杨国武南下,掳掠了秦家小姐,如适才秦帅府上言道,乃是为了索取边关兵符。这中间必有重大图谋,这里死的都是蒙古鞑子,想来也必与那瓦剌国师有关。”方晖听他说到秦帅,猛地一惊,忙问道:“秦帅现在哪里?莫要被那黑衣人折而复返了!”
话音未落,安奇刚身边一名锦衣卫低声道:“有劳方公子挂怀了。”方晖向他望去,见他帽檐压得低低,却正是秦海,心想他一来仍是挂念女儿,二来扮成锦衣卫杂在安奇刚的大队里,确是神不知鬼不觉。当下道:“秦帅当真算无遗策,小房子衷心拜服了。”秦海只嗯了一声,再不接话。
众人人马大队,已自惊动了巡夜的官兵,见是安奇刚在此,便不过问,这样来一闹,天却已经亮了。秦海见天色已明,点了点头道:“想来小女命中该有此劫。杨国武不知因何被迫,竟然投敌,我也是难逃其咎。既然如此,我便去兵部详禀此事,若是边关变乱难以收拾,小女这些小小的麻烦,可也算不了什么。”方晖与安奇刚见他说得郑重,都是不敢接话,但见未曾寻到爱女,秦海失望痛心之色,仍是溢于言表。
安奇刚计点锦衣卫送走秦海,向方晖道:“方少侠,就别重逢,可还与我同到刑部去,见见王大人?少侠在沧州击退魔教光明左使,王大人可是赞不绝口呢。”方晖哦了一声,说道:“只不过是旧部、残部而已,那光明左使,也不过是自封的罢了。况且那些人不过是受了瓦剌国师手下汉人奸细的蛊惑,上当罢了,我便要去向王大人禀明此事。”目下秦小文被掳,旧约五子下落不明,心想以锦衣卫之能,若是他们去查,却比兵部帅府的人有用的多。当下不及多虑,径往刑部来见王亦宸。
不远之处,一黑衣人在一处残破民居的二楼之上,静静地望着锦衣卫离去,缓缓地道:“这少年的功夫,莫非便是传说中的降龙十八掌么?可他内力之中,阴阳变化得古怪,却又是为了什么?”转过头来问道:“丫头,这少年是你爹请来的高手么?明知不是我的对手,却拼死了赶来救你?”身旁一人,委顿在地,冷哼了一声:“他只是我一个普通的江湖朋友,你要杀便杀,莫要多啰嗦。”却是秦小文。
那黑衣人冷笑了两声,说道:“你这丫头机灵古怪得很,被杨国武框出沧州,不出一时三刻便发觉有异。若不是我见你身上武功奇货可居,你当我会留你命在么?我适才想发出响箭示警,转移你等藏身之处,却被那少年击落,枉自送了这许多人的性命。”秦小文想到他适才尽杀众人的辣手,也是不寒而栗,说道:“那些人都是你的下属么?你为了掩藏自己形迹,不问情由地统统杀光,还有人性么?”
黑衣人淡淡地道:“人性?你这丫头,又知道什么是人性?废话莫说,我们启程吧。”
方晖与安奇刚向王亦宸备言前事,王亦宸点了点头道:“此事我也摸不着头脑,适才我已下令,锦衣卫附近各眼线,已四散搜索秦姑娘和旧约盟诸位少侠去了,想来不出今天午时,定然有些消息线索。边关尚无消息,不过兵部即使将使秦海挂帅,亲临边关,以防不测,方少侠大可放心。”方晖点了点头,又问起欧阳露辞官出走之事,王亦宸却说不知为了何事。
众人自上午一直等到日头偏西,各路锦衣卫的探子陆续回报,说并无发现,自沧州而来的百十人,直似凭空消失了一般。旧约盟五子,出沧州之前,曾一路打探那杨国武大队人马去向,一路追踪至城外,也是没了踪迹。众人彷徨无计之时,安奇刚忽道:“那秦家小姐,依照方少侠说法,武功既高,又极为聪明机变,她能一早看出端倪,书信告急,又能在同宣胡同遗下珠钗以为线索,显是未遭毒手,既是如此,我们再去城西附近查看,或许能查到些什么。”方晖点头称是,不及等待王亦宸拨派人手,先自往城西去了。
城西同宣胡同,居民不多,房屋弊旧,往来多是贫民,方晖略一思忖,在此等地方,秦小文虽说不上衣衫华贵,但必是极惹人注目,若有人见到,势必甚为扎眼。哪知四下里打听,却多说未有见到。方晖记挂旧约盟众人安危,心下不安,思前想后,若敌人要挟秦海不成,此刻秦海挂帅北去边关,必然掳掠了秦小文向北。念及由此,一路往京城北门而来,心想以秦小文聪明,必在城内留下什么暗记。
方晖于这京师城西,本就不熟,向人问了路径,那同宣胡同的居民,却多为原住之民,指点的都是快捷小道,方晖又是思虑重重,三绕两转地,抬头一望,却是鬼使神差地走到了西门来。
方晖见走错了路,心下暗叫糊涂,正欲回转,眼睛一瞥之际,却见城门口一处馄饨摊的招牌之上,划着长长的一道波浪线。方晖心中一动,当下也不多话,走近那馄饨摊,要了一碗馄饨,此时太阳西斜,刚过未申之交,却未到了晚饭时分。方晖漫不经心地吃了几口,跟那老板闲扯了几句,问道秦小文形貌、身着黑衣之人经过此地。那老板想了一想,说并未见过,方晖心想若是那黑衣人便算掳了秦小文经过此地,也必乔装改扮,便是问也问不出来的。
见无甚线索,方晖立起身来结账,递过银钱之时,借着西斜阳光的照射,却见隔壁桌子上也有一道浅浅的痕迹,与那招牌上的波浪之形并无二致。这一来,方晖便留上了心,在那桌子旁细细查探,但见痕迹浅浅,却是人指甲刻上去的。
方晖心下恍悟,自怀中摸出秦小文所写的那封书信来,细看那落款之处的长长一笔。果见那一笔,笔势起伏,与这桌上指甲所刻画的波浪之形,殊无二致。方晖此时不禁暗赞那秦小文聪明,写书信之时,到得最后,必是形势紧急,不及再写,她轻描淡写地划这一边,比划又不复杂,旁人任从何处见到这一划,都不会在意,她却可随时随地乱画,沿途留下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