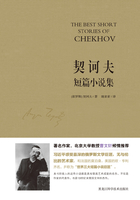德佑八年腊月初九正午,得胜回朝的王师由大武门经过,过护城河,一路由承天门逶迤进入紫禁城。午门广场上的八十一门礼炮依次响过,身穿戎装的皇帝骑着一匹通体乌黑的骏马,出现在午门广场前的御道上。
文武百官在御道两旁候迎,这时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簇拥着从午门左右的小门进到紫禁城,王师在午门广场上列队站好。
皇宫的内眷都在金水桥的内侧,远远看到皇帝在马上的身影,都拜了下去。
所有人都低着头的时候,我偷偷抬头瞟了一眼,想看看萧焕披着甲胄是什么样子的。等我抬头的时候,正好看到午门旁的侧门里,有一辆马车开了进来。
那是辆翚车,车里坐着的是后妃,过午门而不用下车,就算是从侧门进来的,也算是极为尊荣的恩典。
我猛地想起,皇贵妃杜听馨不在候迎的队伍里,我怎么会到现在才发现,我回来之后,从来都没有在紫禁城里看到过她。
她随驾出征了。
我不想让自己想,可是念头不听使唤似的飞快转了起来:杜听馨随驾出征,她一直就在山海关城内。当我和萧焕在库莫尔帐中的时候,她就在几里外的山海关城中;我和萧焕回到山海关的时候,那个房间里甜腻的薰香是她的;当我回到紫禁城后,她正陪着萧焕和库莫尔订立和约;昨天晚上萧焕急着要连夜赶回去,是因为她还在军中等着他。
心里那个沙沙沙沙的声音越来越大,直到完全充盈了我的耳朵,锣鼓齐响的大乐,静道太监的吆喝,全都隐退到了这个声音之下,我终于明白那条咬着我的虫子是什么了。
妃嫔们依然没有抬头,我却慢慢站直了身体,萧焕骑着马从汉白玉长桥的那一头缓缓走来。
同我想象的一样,他穿甲胄也很适合。
正午的阳光照射下来,黄金的铠甲,被黄金铠甲包裹的骏马,都泛起了金黄的光晕。光晕的正中,他的面容清晰,仿佛一个天神,从云端徐徐走来。
归无常说得不错,有些人,天生就是给人景仰的。
骏马越走越近,那个年轻皇帝的眉目也越来越清晰,我却开始懵懂,这匹华丽的骏马驮来的是不是那个在江南的秋风中对我微笑的年轻人,我曾以为他的那种温柔只属于我的那个年轻人?
萧焕乌黑的双眸撞上了我的目光,看到我的失仪,他的眼中却没有惊疑,他也没有笑,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目光中有的,是淡淡的温和。
我身后是一片匍匐的人群,他身后是另一片匍匐的人群,我看着他不曾从我脸上移开的淡定目光,忽然间觉得,他是在一个遥远的不知名的河岸的彼端。
黑色的骏马从御道上走过,我的目光追着他的身影,在我们就要擦肩而过的时候,他忽然向我笑了笑。
我瞟了一眼四周俯着身子的妃嫔宫女,考虑着要不要也回个微笑给他,腰上却突然一紧,身子就腾了起来,等回过神的时候,我已经坐在了萧焕身前。
这可是在太和门广场前,文武百官、后宫内眷和数千将士都看着呢。我吓出了一头冷汗,连忙回头压低了声音:“你干什么?疯了吗?”
他轻轻笑了,没有说话,却在马肚子上一夹,骏马吃痛,离弦的箭一样射了出去,直冲太和门。
百官和妃嫔都还匍匐着没有起来,御道两旁的仪仗队因这突如其来的变而故震惊,都愣着不知道该干什么。余光里,我瞥到司礼监掌印冯五福气急败坏地跺了跺脚,低喝一声:“都愣着干什么,快跟上。”
扛卤簿的小太监听了,慌忙拖着沉重的家伙小跑着跟在后面,看上去有点狼狈。
我挑起嘴角,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
太和门转眼就到,萧焕在门前勒住马,笑了笑,问:“高兴了?”
我笑着点头:“不过我觉得你一定是疯了,简直像离谱的无道昏君。”
“不错,我也这么以为,做了回胡闹皇帝。”他笑叹着,自己先跳下马来,然后把我也接下马。
冯五福领着小太监刚好紧赶慢赶地赶了过来。萧焕放开我的手,退到御道正中站好,我也退开,站在御道旁分给内眷站立的地方。
冯五福慌慌张张地喊了声:“起。”这个字被立在御道旁的小太监一连声地传了出去,跪伏在广场上的人群才都起身,仍旧低头,顺着礼仪的程式,各自走到太和门前站齐。
面前这群垂着头的人,有多少确切地看到了刚才的那一幕,有多少人在暗暗揣测刚刚发生的这一切的意义,而从明天开始,紫禁城内外又将有多少的传闻?
毕竟自萧焕十二岁即位以来,不要说庆典祭祀这种大场合,就算是日常和臣僚之间的应对,也从没听说他在进退仪容上出过什么差错。因为这一点,他在少年时还曾被拍马溜须的言官盛赞为生有明君容德。
这样想着,我忍不住看了站在御道正中的萧焕一眼,他已经又神色凛然地目视前方,任由光禄寺那些礼仪官摆布了。
凯旋庆典很隆重,随后的大宴也热闹至极,因为这次主要是犒劳戎马劳顿的将士,而军官们大多要比文官豪放肆情得多,所以气氛较之以往也轻松很多。
觥筹交错之中,我悄悄放下手中的酒杯,拉了拉身边御座上萧焕的衣袖,他微微侧了侧头,带点询问地看着我。
我扳过他的头颈,飞快地在他脸上吻了一下。
他连忙轻咳一声,坐直身子,脸上却有些泛红。我低下头偷笑,管他几个人看到,他们要看就让他们看好了,隐秘的快乐充盈上来,这个时刻,连坐在萧焕右侧的杜听馨投过来的幽幽目光,我都不想再留意。
坐好了的时候,殿下有道淡淡的目光投了过来,父亲持着酒杯看着我,没有表情,刚刚那些,他应该都看到了。
我别过脸去,不再看他。
大宴一直持续到华灯初上,太和殿内殿外点满了烛火,照得殿前的广场亮如白昼,紫禁城的夜晚难得这么明亮温暖。
酉时刚到,内眷们就开始陆续退席,我也离席向萧焕请归,萧焕点了点头:“时候不早,皇后先回寝宫。”
今天是逢十的日子,他没说让我早点歇息,就是说待会儿会召我去养心殿侍寝了。
我点头表示明了,行礼:“臣妾告退。”抬头看到坐在萧焕身侧的杜听馨眼神淡定如水,正静静地看着我。
我突然想到,杜听馨生长在紫禁城内,帷幄之间邀宠弄权的事,不知道看过多少,可那次陷害我的时候,她却用了那么容易被识破的方法。
她是不是明白萧焕一定会护着她,所以故意那么做,以向我示威?
难道那个时候,她就看出我对萧焕还没有忘情,知道总会有现在这么一天,我会明白过来原来我不能容忍萧焕身边还有别的女子和他在一起柔情蜜意?
她在那时就种了一粒种子在我心里,而我直到那颗种子已经长成参天大树,撑得胸口发疼,才意识到它的存在。
原来我一直都小看了杜听馨,这个被膝下无女的太后夸赞为冰雪聪明,视为掌上明珠,十三岁就以诗名艳绝京城的才女,绝对不是一个只是皮相光鲜的绣花枕头。
这一刻我应该妒恨交加的,但是我心里那个沙沙的声音已经没有了,从内金水桥上萧焕对我展开笑靥开始,那个声音就没有了。无论身处何处,无论顶着什么样的身份,那个笑容都没变过,那是那个青衣儒冠的年轻人在江南的秋风里给我的微笑。第一次看到这个笑容的时候,我就想,我一直在等的那个东西终于来了吧。
我抬头向杜听馨笑了笑,我想这一定是我最灿烂的微笑。
杜听馨眼中的淡定迅速褪去,换上了失神的惊愕。
我转身走出了太和殿。
回到储秀宫,卸了脸上的脂粉,换了便装,估计时间还早,就倚在灯下看了会儿书。
我兴趣比较低俗,从小到大都只喜欢看野史和笔记小说,碰到经传诗文就头疼,因此爹常说我胸无大志,不学无术,我也不理他,照旧捧着我的传奇小说看。
这次看的是小山刚从宫外书肆买来的志异小说,叫《镜花缘》,内容新奇有趣,文笔也流畅诙谐,怪不得小山说这本书近来在市井间很流行。
看着唐敖和林之洋、多九公在千奇百怪的国家游历,不知不觉夜就深了,看看桌上的西洋座钟,已经过了亥时。我放下书,正准备沐浴等着养心殿的人来接我,冯五福就笑眯眯地来了。
他行了个礼:“万岁爷吩咐,就寝前还想和娘娘说会儿话,不必净过身之后再去,另在养心殿备有热水,待到寝时再洗。”
我点了点头:“知道了,请冯公公先行。”
冯五福一路把我请到停在储秀门外的鸾轿上,等我坐好了,他忽然说:“万岁爷离京月余,积压的事务很多,万岁爷的身子却经不起连夜操劳,待会儿到了殿里,还望娘娘能设法提醒万岁爷早点歇下。”
我忍不住挑了挑眉毛,冯五福交代这种事情给我,已经有点把我当成自己人看的意思,于是我笑着点头:“那是一定,就算公公不说,我也会提醒万岁的。”
冯五福一边笑着应道:“这就好,这就好。”一边把轿帘放下。
轿子离地,摇摇晃晃七拐八绕,最后终于停下,我裹着斗篷从里面艰难地钻出来。紫禁城里就是麻烦,储秀宫到养心殿这点路,我抬抬腿就到了,还要坐轿子,真是养的闲人太多,非得找点事儿出来才行。
养心殿前殿东暖阁是皇帝的卧房,西暖阁就是御书房,屋里的南墙上装着玻璃窗,以便采光,萧焕通常都是在窗下的软榻上批阅奏章,看书写字。
我刚下轿,就在门外看到了窗里的灯光和萧焕模糊的身影。
石岩照例守在门口,我向他点头笑了笑,就走了进去。
暖阁里只有萧焕一个人,他坐在窗前,正伏在榻上的矮桌上看奏章。
我走到桌前,一巴掌把他手里的折子扣到桌子上:“你要幽会的人来了,还不快放下这些无聊的玩意儿?”
他抬头笑了笑:“看得忘了,这么晚才叫你来,等的急了吗?”
“在看一本很有趣的小说,时间也过得挺快。”我笑了笑。
“噢?是什么?”他用手支住头,淡笑着问。
“一本市坊间新流行的小说,你肯定没看过。”我笑着向他眨眨眼睛,“如何,你的皇后这方面消息很灵通吧?”
他笑了笑:“说起来我年少时也曾迷恋过一阵笔记小说,觉得其中微言大义,比四书五经中的义理有趣多了。后来老师说身为天子,那些小说家言,看点就好,不必太多,我就没有再看。现今就算想看,也没这工夫了。”
他虽然称父亲为凌老师,但其实那时父亲已经贵为内阁首辅,只是领个虚衔,并没有真正授教于他。他现在说的这个老师,是时任负责辅导太子的詹事府正三品詹事,真正教导他十年有余的吴甫名,不过吴甫名已经在德佑三年染病死了,要不然现在萧焕亲政,肯定会对他委以重任。
我从来没听萧焕在人前提起过自己小时候的事,就笑了笑:“反正我整天也没事,要不然我把看过的讲给你听?”说着挑着眉毛看他,“对了,你不是说有话跟我说?什么话?”
夜已经深了,窗外没有风,殿内殿外都阒静无声,他默然地看着我,跳跃的烛火下,那双深黑的眼睛里隐隐有细碎的光亮,亮光渐渐汇成一抹笑意,从他的眼角流溢出来,终于占满了整个脸庞。他轻轻笑着:“突然忘记了。”
我眨眨眼,看看他灿烂的笑脸,再眨眨眼,然后扑上去掐住他的脖子:“你耍我是不是?”
他轻笑出声,清脆的声音在我耳际回响,仿佛有排流苏从那里抚过,痒痒的。
我把手从他脖子上滑下去,滑到他的后背,轻轻环抱住他。
靠在他的肩头上,有个念头悄悄从我心底钻上来,犹豫了很久,我还是决定把它说出来:“萧大哥,我们一起洗澡吧。”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舒服,他猛地咳嗽了两声,最后轻声说了句:“好吧。”
一个大男人,怎么比我还容易害羞?怪不得会被库莫尔当做娈童调戏,老这么温温吞吞的下去不行,我决定今天晚上就把前几天向老宫女请教过的闺房秘术使出来。
洗完了澡上床,这天晚上下来,我明白了两件事情:第一,“那个”原来不是每天晚上只能做一次;第二,做“那个”原来可以很愉快。
迷迷糊糊地快要睡着的时候,我把头埋在他胸前:“萧大哥,这么下去,我真的会替你生孩子吧?我不想给你生孩子。”
他把下巴轻轻放在我头顶,问了句:“是吗?”
我把脸静静地贴在他胸前,没有回答。我脸下他的皮肤有些凸凹不平,是我刺中的那剑留下的疤痕,绵绵延延居然有两寸多长。
有什么温热的东西从我眼里滑了出来。等我生育出了皇储,父亲会不会想要弑君立幼?目前为止,萧焕已经从他手中抢走了太多权力,他已经发现了吧,这个年轻而看似文弱的皇帝完全不是他能够控制的。
能不能不要再争了?这句话我说不出口,因为我明白,就算说出来了,那两个人的脚步也不会就此停下,他们早已陷入深渊,再也无力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