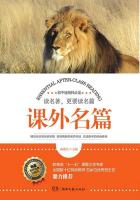弗朗兹在清晨醒来时,仍被萦绕在心头的幻觉扰得脑子里一片混乱。
上午他就要离开维斯特赶往科罗斯瓦了。
他计划在彼特森尼和利瓦扎尔参观完现代工厂后,在卡尔斯堡休息一天,再到特兰西瓦尼亚的首都逗留几天,再在那儿乘火车一路游览匈牙利的各省,完成他此次旅行。
弗朗兹走出客栈,他眼睛上戴着双筒望远镜站在平台上,他激动地认真观察着被太阳清晰映照在奥加尔高原上城堡的轮廓。
他的思绪一直在犹豫着:到了卡尔斯城堡要不要履行自己的诺言?是否把喀尔巴阡城堡的情况反映给当局呢?
当弗朗兹承诺让村子重获安宁的时候,他确信城堡是一帮匪徒,或者至少是一帮嫌疑犯的避难所,他们不想被人发现,因此采取了一些手段避免人们接近他们。
但通过昨天尼克的一席话,晚上把整个事件仔细考虑了一遍。他改变了决定,一直犹豫不决。
科茨家族的最后子孙鲁道夫男爵失踪了,整整五年没人知道他的情况。传说他离开那不勒斯不久便死去了。
这有可能吗?关于他的死有何为证?可能鲁道夫男爵还活着,假若他还活着,为何不能回到他祖先的城堡呢?难道他唯一亲密的朋友奥凡尼克不能陪他回城堡吗?如果这个神秘的科学家就是在此地引起民心不安的恐惧现象的导演和幕后策划者呢?
人们也许会认同这种似乎合理的假设。是啊!凭鲁道夫男爵的性格和习惯,如果他回到城堡,肯定会尽量使人远离他。
但就算假设成立,弗朗兹又能怎样呢?去扰乱男爵的生活于他有什么好处?他正犹豫着,罗兹科从后面赶上来。
他向弗朗兹提出了他的想法。
“主人,”罗兹科说,“是鲁道夫的可能性很大,他一向神神秘秘的。噢!假设果真如此,您还是别掺和进去了,让维斯特村这些蠢货自己去看着办吧——这是他们的事,我们没必要为此操心。”
“不错,”弗朗兹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认为你说得对,我的好罗兹科。”
“我是怎么想怎么说。”罗兹科朴实地答道。
“至于柯尔兹老爷和他的村民,他们现在明白该怎样对付城堡里所谓的鬼怪了。”
“是的,主人。其实他们所要做的只是去通知卡尔斯堡的警察。”
“咱们用过午餐就走。”
“我都准备好了。”
“咱们先绕道去普利萨山再转回希尔河河谷。”
“为什么,主人?”
“时间允许的话,我想再走近点仔细看看这座神秘的喀尔巴阡城堡。”
“那又何必呢?”
“我突然觉得很有趣,罗兹科,仅仅是一时心血来潮,它浪费不了半天时间的。”
罗兹科对这一决定很不赞同。他认为,即使旅途顺利,这也没什么好处。它只会勾起痛苦的回忆,这是他想尽力避开的原因。可现在他很为难,只得听从主人执意要做的事情。
弗朗兹——像是受到某种不可抵制的诱惑——感到被城堡紧紧地吸引住了。他不知道,这种吸引力是否缘于他在梦中听到的丝蒂娜唱的斯特芬罗那首优美的歌曲呢?
罗兹科对此很担心,因为他还记得村民提到尼克受到神秘声音的警告,而他因违抗而受到了惩罚。于是他想到,主人也听到过那件事,现在他只是到城堡外的墙角下看看,这也许能平息他激动的心理。
弗朗兹显然不想使他的计划让维斯特人知道,那样他们很可能会和罗兹科一样苦劝他,于是他告诉罗兹科不要泄露秘密。所以人们目送着他走出村子沿着希尔河向下走时,都相信他们是去了卡尔斯堡。但弗朗兹早在平台上观察到了雷特亚扎山外有条通向乌尔干山的路。这样不必通过维斯特村就可爬上普利萨山到达城堡,村里人也就不会发觉。
到了中午,乔那斯面带谄笑地呈上账单,尽管有些过高,但弗朗兹还是二话没说就结账走人。
柯尔兹老爷、可爱的米丽奥塔、哈默德、帕塔克、弗利克,还有许多村民都来向他们道别。甚至尼克也走出了房间,看来他很快就能恢复健康了——医生觉得这是他的功劳。
“祝你们幸福,”弗朗兹特别对尼克说,“祝你和你的未婚妻永远幸福。”
“我们衷心地感激您。”姑娘说着,脸上充满着幸福。
“祝您一路平安!”尼克补充道。
“好的,借你吉言!”弗朗兹答谢说,尽管他的眉头微锁着。
“伯爵先生,”柯尔兹老爷说,“请您不要忘了您曾许诺把消息通知卡尔斯堡当局。”
“我记住了,柯尔兹老爷,”弗朗兹答道,“但可能我在旅途会有些延误。您自己也清楚了结此事最直接的方法,那城堡很快便不会再在维斯特善良人们心中引起任何恐慌了。”
“说起来轻巧,”哈默德低声咕噜。
“做起来也容易,”弗朗兹答道,“不出两天,只要你们乐意,警察将会让一切真相大白。”
“除非——那极可能——那是些鬼怪。”弗利克发表议论说。
“那就走着瞧吧!”弗朗兹微微耸了耸肩。
“伯爵,”帕塔克说,“要是您跟我和尼克去过,您就不这么想了!”
“我会吓坏的。”弗朗兹说,“如果我的脚也那么莫名奇妙地被纠缠住的话!”
“脚——哦,伯爵,或者不如说是靴子!除非你认为我是在说梦话——”
“我当然不这么认为,我不想就此事再做解释。
但是如果警察来探查喀尔巴阡城堡,可以肯定他们的靴子会和警察一样守纪律,按规定他们必须穿靴子,不会像你的一样长在地上。”
对帕塔克说了这番告别的话之后,弗朗兹最后一次接受了金玛阡客栈掌柜的谢意——说他十分荣幸尊贵的弗朗兹伯爵屈尊大驾光临小店等。与柯尔兹老爷、尼克及其未婚妻,还有其他人道别后,他朝罗兹科示意,两人便快步走下大街上路了。
一小时不到,他们就抵达了雷持亚扎山脚的希尔河右岸。
罗兹科决定不再多费口舌了,因为这不会起任何作用。作为老军人他习惯于服从命令。一旦弗朗兹遇到生命危险,他会奋力帮助他脱险。
又连续走了两个钟头,两人止住脚步稍事歇息。
在此处,瓦拉几亚的希尔河朝右边逐渐弯曲,在贴近大道的地方拐了个大弯。另一面距此1里路左右,是普利萨山和奥加尔高原。弗朗兹将离开河岸攀登山峰,如果他要翻山到城堡去的话。
选择绕这么长的弯路是为了避开维斯特村民。可这明显地使城堡与村子间的距离增加了好几倍。不过他们到达奥加尔高原的顶峰时天应还是大亮,这使弗朗兹有时间从外面来欣赏城堡。然后,等到天黑才再回到维斯特,即使沿着大路走也不易被人瞧见。他计划在利瓦扎尔过夜,那是个位于希尔河汇流处的小镇。第二天白天再继续赶往卡尔斯堡。
他们休息了半小时,弗朗兹陷入回忆之中,一想到鲁道夫可能就藏身在城堡里他便莫名地激动不已,但他一言未发。
罗兹科费了很大的劲才没说出口来:
“不必再去了,主人!别去管什么城堡了,咱们还是回去吧。”
他俩开始沿着河谷前进,但首先他们得穿越浓密的灌木丛,地上有一个个冲得很深的坑,这是由于在雨季,希尔河有时河水暴涨,巨浪滔天的洪水溢满了地面,把它变成一片沼泽。这给他们制造了前进的障碍,也延误了不少时间;他们用了一个小时才绕到乌尔干大道上来,那时大约是下午5点钟。
普利萨山的右坡没有那种尼克必须用斧子开路才能穿过的森林,但他们不得不面临另一种阻碍。有堆得很高的石堆,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突然陡立的巨石和深深的洞穴;巨大的石头,好像阿尔卑斯山的冰山一样林立着,所有这些杂乱无章的大石头都是山体滑坡时从山顶滚落下来的——事实上,那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拥挤的一大堆。
费尽了体力,攀登了一小时,才爬到石堆顶端。看来这也是嗒喀尔巴阡城堡的一道天然屏障罗兹科期盼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没有出现。
到了大石阵和陷坑的边缘,就登上了奥加尔高原的外层山峦。在这荒漠的中央,可以更清晰地观察城堡,但好多年来,没人敢冒险靠近它。
必须指出,弗朗兹主仆是从北面接近城堡的,而尼克和帕塔克则从东面到达围墙,这两面围墙形成一个很大的夹角,顶角的顶点是城堡的主楼。但要从北面进入城堡是办不到的,因为北面没有吊桥和暗门,而且墙特别高。但进不进去无关紧要,反正弗朗兹并没打算到里面去。
弗朗兹站在奥加尔高原时已是7点半了。面前这片古老的建筑群耸立在暮色之中,颜色跟普利萨山上岩石的那种陈旧的颜色一样。左边,围墙猛然拐弯,侧面的夹角处耸立着棱堡。在有垛口的围墙上方顶部,露出柏树的奇异面目。
弗利克没有看错,根据传闻看,鲁道夫城堡只有三年活头了。
他俩静静地看着中间耸立着坚固的城堡主塔的建筑群。毋庸置疑,在那看似混乱的一大堆景物下面,仍然有着隐蔽的富丽堂皇的地下宫殿,迷阵般长长的走廓,像古马格亚要塞至今还遗留着的埋藏在地下纵深处的宫殿。除了这个神秘的庄园外,没有别的府邸更适合科茨家族的最后子孙让世人忽略自己,这个真相没有人会了解。弗朗兹越是认真思索,就越觉得鲁道夫肯定藏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喀尔巴阡城堡里。
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城堡主塔里有人居住。烟囱里没有冒烟,紧闭的窗子里没有发出丝毫响声。什么也没有——甚至鸟叫声——这便更衬托出这座阴森森的庄园的寂静。
弗朗兹激动地凝视着围墙内的城堡,看了好久,这里曾经弥漫着节日的欢笑和武器的铮鸣。可他什么也没说,他心里想着另一件事情,那就是对往事的追忆使他思绪万千。
罗兹科想让弗朗兹安静一会儿,尽量不去打扰他,甚至连一句话都不说,以免打断他的思绪,但当太阳滑下普利萨山梁、夜色笼罩着希尔河谷时,他便不再沉默。
“主人,”他说,“天色很晚了,已经8点了。”
弗朗兹似乎没有听见。
“该回去了,”罗兹科接着说道,“如果咱们想在客栈关门前赶到利瓦扎尔的话。”
“罗兹科——别急——是的——等会儿我们就走,”弗朗兹答道。
“我们要花一个多小时,才能回到山谷那边的大路上,那时天早黑了,走大路时不用担心让人发现了。”
“再过几分钟吧,”弗朗兹说,“咱们就下山回村子里去。”
弗朗兹从一到达高原上,就站在原处没动过。
“不要忘了,主人,”罗兹科继续说道,“黑暗中再穿过那些岩石堆就很困难。甚至大白天都很困难哩。请您原谅我多嘴——”
“好吧……咱们这就回去,罗兹科……你先走……”
看样子弗朗兹好像是身不由己地留恋在城堡前,可能是被一种内心无法抗拒的某种神秘预感给留住了。他是否也像帕塔克所说的那样被吸在围墙下呢?不,他脚下没有任何机关、任何罗网,他可以自由地在高原上行动,只要他愿意,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绕着围墙走。
可能他正有此意?
罗兹科想到这里,他最后一次说:
“快走吧,主人。”
“好的,好的。”弗朗兹答道。可脚下却仍没有移动。
奥加尔高原已完全黑了,暮色渐渐向南移动扩展到城堡上,其轮廓已变得很模糊了。不久什么都看不清了,除非有强光从城堡主塔的窗子里发出来。
“走呀,主人,走吧!”罗兹科说。弗朗兹刚要跟他走,突然棱堡的阳台上,那棵古怪的柏树旁边,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
弗朗兹停下脚步,怔怔地望着那个身影,越来越清晰了。
那是个女人,长发披肩,身穿一件雪白的白色长袍,双手伸向前方。
这件服装,不正是丝蒂娜在最后一次演出《奥兰多》的最后一幕中穿过的那件么?
是的!肯定那就是丝蒂娜,默立平台,手臂朝弗朗兹伸着,用她那热切深邃的目光望着他——“是丝蒂娜!……是她!”他叫道。
他朝前扑过去差点跌倒在护城河边,如果不是罗兹科一把拉住他的话……但是身影随即消失了,丝蒂娜不见了。
这又何妨?
那确实无关紧要。一秒钟就能让弗朗兹认出她来了。他叫喊起来:
“她!……她!……还活在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