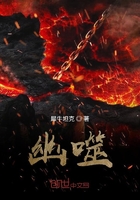一天,他买了一匹瘦得风都能刮倒的毛驴。到了没人的地方,把手里仅剩的一个铜砣砣,往驴尻子里一塞,就拉上到老地主家门口去了。老地主一见说:“哎呀,你这个穷鬼!哪里弄来了这么个瘦驴,哪里来的哪里去。不要站在我的门上,看了让人丧气!”“咳!老人家,我的这个毛驴你别看它瘦,会屙金尿银呢。”“咦,会屙金尿银?那就卖给我吧?”“行!卖就卖给你。”“那你先叫屙些金给我看一下!”“哎呀,你不要急,拉到房子里慢慢屙嘛。老人家,不相信了你过来看。”说完吹破天把驴尾巴揭起来让地主看,地主一看,真的尻门眼子里有个黄砣砣,“你看,这马上就屙出来了。”地主贪财得很,赶紧就把驴拉进房子去了,“好,好,你要多少钱?”“我暂时不要钱,你给我一些粮食吧。”地主一听光要粮食,还不好办吗?大声喊:“管账的,给这个穷小子装上几口袋粮食。”粮食一拿到家,吹破天在庄稼汉跟前牛皮烘烘地说:“给你!粮食拿来了。”大家一看,粮食真吹回来了,高兴地分了吃去了。
第二天,老地主找他来了:“哎,你这个驴咋么屙的呢?昨晚上没屙,是不是还有个啥方子没给呢?”“对!就是有个方子呢。你把新单子拿出来,铺在上房的地上,四个角角把灯点上,它才屙呢。”地主就回去了。单子铺在上房,四个角角都把灯点上。“伙计们,都来。我今天买了一头屙金尿银的驴!”伙计们一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哟,这就好了,以后发开钱了,毛驴子一抬尾巴就够咱们花几年的了。”
老地主看得来了精神:“等一等,先拉去叫驴好好吃上些。”一下煮了一大锅绿豆稀饭,硬按着叫驴喝上。驴肚子喝得太饱了,拉到单子上站下以后,尻子憋得不行,又加塞了个铜砣子挡着呢,在地下乱蹦乱跳。老地主赶忙说:“快准备好,就屙了。”驴肚子憋得尾巴都耸起来了,两个眼睛睁得圆圆的,尻门眼子里的铜砣子一闪一闪的。老地主实在等不及了,拿个钩钩子一钩,铜砣砣刚一滑,“扑哧”一声稀屎就喷出来了,把老地主喷了一头的稀屎。“这个狗日下的吹破天,我得找他去,我把他打死呢!”一去就把吹破天抓住了,“你这个狗日的!你害得我好苦。我存下的好单子都屙得不成个样子了,还把我老汉喷了一头稀屎。咋么屙金尿银的?你今天不给我赔,我把你砸死呢!”又对着伙计们说:“去!你们给我把他裤子扒了,关到那个磨房去,往死里打!”
吹破天挨了一顿打,裤子了、褂子了都叫撕坏了,晚上冻得不行,他就推磨。第二天赶早,老地主说:“去!给我看去,把那个穷小子冻死了没有?”伙计到磨房一看,哟!他热得满头流水。“哎哟!大冬天,咋把你热得满头流水的?”“咳!我穿的这是火龙衣。”“你那顾了腔子顾不住尻子还叫火龙衣吗?”“对呀,我这火龙衣凡人眼睛是看不着的。”伙计马上跑去给老地主说了。老地主不相信又跑来了,果真他热得满头流水的。“咳!穷小子,你的火龙衣卖给我吧?”“嗯,我再也不卖了!”“你不卖?你不卖我非打死你不可。”
吹破天一看地主真信了,就说:“那只好卖给你吧。”就把烂衫衫脱了。“那你要多少钱?”“上一回要了些粮食,这回就不要粮食了。我这是老龙王穿下的衣服,相当贵重。这样吧,你把你的贵重东西拿来,我挑上几样子就行了。”“行!”老地主就把家里藏宝箱拿来,一连开了四道锁才看见了宝珠、玛瑙、翡翠,吹破天胡乱抓了七八件就赶紧跑掉了。
吹破天一走,这老地主给老婆子说:“老婆子,今天这个火龙衣有了,这晚上我们衣服也不要穿了,被子也不用盖了,就盖上火龙衣就行了。”晚上,老两口身上的衣服全脱掉了,把吹破天的烂衫衫子往两个人身上一搭就睡下了。越睡越冷,一晚给冻死了。赶早天大亮了,三个儿子说:“看一下大大妈妈,火龙衣盖上可不要热坏了。”
结果一看,全给冻死了。老汉、老婆一死可不得了,三个儿子找吹破天去了。“吹破天,狗东西!你说是火龙衣穿上能热死,咋叫冻死了?今天可不能饶了你,打死你呢!”“那你咋办?他们老两口享不了这个福嘛,是叫热死的。这样吧,”吹破天走到冻死的老汉、老婆子跟前,瞅了瞅,心想:这个老熊坏得很,死了我都要想个办法治治他。就去弄了个棒棒来说:“这是还阳棒,打一下,看能不能还过阳来。”三个儿子拿上又照着老汉、老婆子乱打了一顿。一看大大、妈妈还是死的,说啥也不愿意了。一下上去就是拳打脚踢,把吹破天打了个半死,搁了个麻袋一装,准备扔到河里去。
半路上,兄弟三个累了,正好跟前有个小铺子,他们三人就进去喝些茶。一个放猪的过来了,看到路上扔着一个麻袋,心想不是黑豆就是黄豆,拿上回去给我的猪吃吧。吹破天觉得有人动麻袋,说:“哎,你别解,别解。我是一个烂眼子,蹲在这个里头捂一捂就好了。你这一解,我的眼睛可咋好呢?”嗯,这个人正好也得了烂眼病,正愁得没法治呢。“哎呀,好人,行个善吧!我这多年的烂眼病了,叫我也捂一捂吧。”吹破天一听,巴不得呢:“行,我就行个善吧。”出来就又把放猪的绑到麻袋里了:“你悄悄蹲着,不能说话,两个时辰就好了。”说完,吹破天赶上猪就走了。
兄弟三个喝完茶出来,麻袋一拖就走。放猪的觉得被谁拖着走开了,那人说是不让说话,他只好悄悄蹲着。到了河边,老大说:“往河里扔呀。”放猪的一下大叫:“不要扔!不要扔!我是放猪的,是在这里头捂眼睛呢。”“哼!你再叫也没用,谁叫你害死我大、妈呢?就这个都便宜你了。”一下就扔到了河里。
没过几天,吹破天他又吆了一群猪从这兄弟三个的门口过。兄弟三个说:“咦?不是明明把吹破天扔到河里了吗,他咋又吆了一群猪来了?”“咳!你们兄弟三个不行。那天你们光把我扔到河边上了,要扔到老里头才好呢,我就不赶猪了,河里面的珠宝多得了得,只可惜我过不去呀,只好吆了些海猪上来了。”兄弟三个又上当了:“哎,你把我们兄弟三个也领到里头发个财去。”“好!我就帮你们发个财。”到了河边,他把兄弟三个往麻袋里一装,“咕咚”扔进去,兄弟三个让他弄死了。
这一来呀,吹破天的名气大得很了,惊动了县官:“哎呀,听说这个吹破天厉害得很,把天都能吹破。我今天看一下,到底是咋么个人。”就打发一个衙役叫去了。吹破天听说来了个衙役叫他,悄悄跑去一看,是个瘙头,心想我得好好动动脑子。这就快快往回跑,他前脚进了门,后脚就听到:“吹破天,你开门!”“开门做啥?”“我们县太爷有请。”“不行,我栽头发呢。”瘙头一听高兴得了不得:“哎呀,吹大爷,你先给我栽上些头发吧?”“行,你把头靠在门上。”瘙头刚靠在门上,吹破天“啪”的照头给了一凿子,“哎哟!哎哟!”瘙头抱上头跑回去了。“哎哟,不得了!县太爷,那个吹破天好厉害,给我头上来了一下,头发没栽上倒钻了个窟窿。”
县官又指着另一衙役说:“你去!你去叫去!”吹破天知道闯下祸了,早早就在村口等下了。一看来了个烂眼子衙役,还是那个话,他前脚进了门后脚就听到,“开门了!”“我上眼药呢,你干啥?”烂眼一听有眼药:“那你给我抹上些眼药。”“好!你进来吧。”烂眼子又看不清楚,吹破天过去抓了一把辣面子,给烂眼子眼睛抹了。一下烂眼子疼得跳蹦子呢,又哭又叫地跑掉了。县官一看是烂眼子哭着回来了:“哼!我叫你吹破天今天给我好好吹一下!”官服一穿,就找吹破天去了。
一见面:“你就是吹破天?”“我就是,老爷。”“听说你吹的歪得很唦?来!今天老爷我看一下你能把我吹得咋么个?”吹破天一听,假装说:“唉,老爷,我能吹个啥呢?不行,不行!”“不行?你得跟我到县衙去!”吹破天说:“老爷,你看你骑着大白马,穿着大蟒袍。你等一等,我去后院里把我的大白猪骑上。”县官一听,“你骑猪干啥?”“哎,你骑着大白马,我光骑个猪就行了。”就去把大白猪骑上,一拉猪一哼,二拉猪一哼。吹破天说:“县太爷,我的这个猪可比你的马跑得快,拍一拍走八百,按一按走两万。”县官一听:“好家伙,你这个猪拍一拍走八百,按一按走两万,一定是宝贝,你换给我。”“那不行,县官大人,不能给你,我这个猪嘛,是认衣服不认人。”县官一听:“那好,我的衣服你换上。”就把蟒袍脱了,把吹破天的烂衣服一穿。
吹破天说:“还要换马呢,县太爷。”“行!”大白马又换了,这就两个人比赛呢,看谁跑得快。县太爷说:“你先走,不要叫宝猪一走开把你的马蹄子踏下了。”吹破天鞭子一抽,大白马“噔噔噔”地跑掉了。这县太爷不急不忙地朝猪屁股上一鞭子,猪“哼哼”叫了一声;他又抽一鞭子,猪“哼哼”又是一声;又抽了几鞭子,猪只是哼哼叫着不朝前走。他三抽两不抽的,那吹破天已经到了县城,直直地骑到县衙门里了。瘙头啦、烂眼子啦一看县太爷回来了,都上来接来了。“衙役们,你们赶紧接吹破天去,那个东西不好好走,骑个大白猪落在后头呢。”衙役们赶紧去了。瘙头和烂眼子受了吹破天的骗,正气得了不得。
又说县太爷,把猪一顿打死了。这伙衙役到了跟前,管他三七二十一,把他抓上就回了衙门。吹破天说:“给我打死这个吹大牛的穷小子。”这下瘙头、烂眼子比谁都跑得快。县太爷挨不住了:“哎呀!我是县太爷!我是县太爷!”吹破天穿的官服么,谁还多疑呢?“打!叫他嘴犟。”结果县太爷被活活打死了。县太爷这一死,吹破天就当了县太爷了。
讲述:李翠英 采录:韩爱荣卢华英
不懂装懂害死人
很早以前,哈密有个箍桶匠叫张厚,老家是甘肃玉门的。张厚长年在外做手艺、跑买卖,赚了些钱。到了晚年,就把儿子接来,让他学学手艺,并帮着管管账。一晃娃子来了一年了。快过年的时节,有个老乡回老家过年,打他们家门上过。铺子里生意正忙呢,张厚和娃子商量:“铺子忙,过年过节,正是手艺人挣钱的时节。你来头一年,就不回去过年了,托老乡捎上五十两银子回去,让你妈和你媳妇把年过得红火些。再请人写个信,把情况说一说。”儿子一听:“不就是给家里写个信吗!何必请人?还是自己写吧。”张厚听了怪高兴的,到底是我的儿子,信写上和银子一齐包上交给了老乡。
老乡骑着毛驴一路上紧赶慢赶,一天擦黑时,到了张厚家。把东西交给张厚的婆姨,喧了几句,急忙赶回家去了。那婆媳俩看到五十两银子高兴得了不得,可是两个都不识字,只好把信收起来等明天请人念念。两人一黑里都没合眼。
二一天赶早,两人又是打酒,又是买肉的,都弄停当了。请一位老先生来家看信,老先生美美吃了一顿。吃罢喝罢,晃晃悠悠戴上老花眼镜,慢慢念着:“哈密铺内事务多,又亡一人,不能回来,托人捎回五十两,材埋过年。”老先生念罢长叹一口气:“不幸,真不幸呀!”婆媳二人还没明白,赶紧问是咋回事。老先生解释说:“哈密铺内死了一个人,捎回五十两,弄个棺材过年前埋人。”婆媳两人听罢一起放声大哭,媳妇哭怕男人死掉;婆婆哭怕老汉死掉,连是谁死都闹不清楚,就哭得伤心得不成。
婆婆连夜跑到娘家找娃他舅合计到哈密搬尸。正是过年,家家都要用钱,一时也借不上,只有干着急。别人家欢天喜地,门上贴的红纸对联,他们家只好贴白纸对联。
正月初三,老乡起身回哈密,路过张厚门口,心想:进去问一下,看有啥事。走到门口一看,门上咋贴上了白纸对联?将要进去,一想:不行,我是走远路的,闯丧事不吉利。赶快掉头就走了。回到哈密,老乡先去给张厚报信:“你老家死了人。”张厚一听差点跌过去:“是老的还是少的?”老乡说:“我没敢进门,只见门上贴的白纸对联。”老子对儿子说:“我回去看看,你在这看好铺子。”儿子说:“还是我回去,你留下。”老汉怕老婆死了,儿子怕媳妇死了,二人都抢着要回去,谁也不让,最后把铺门关了,两个人一齐回。
二人连夜启程,一路上急死慌忙,昼夜不停往回赶。这天先到他舅门上,张厚说:“你到你舅家去看看,我回家去看看。”儿子进到舅家。一看他妈和舅正吃饭呢,寻思:完了,看来是我媳妇死了。也不言传,放声就哭。他妈一看儿子回来了,也放大声哭:“我的老汉呀!你咋就丢下我不管咧?”儿子说:“妈,你咋咧?我大和我一齐回来,先走家里去了。”他妈还是不信,说儿子哄他。再说张厚回到家,见儿媳妇戴着孝,只当是老婆子死了,哭得跌了过去;媳妇一看公公回来了,又想是她男人死了,也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正哭呢,儿子和他妈、舅一块回来了。大家见了面,都莫名其妙:“真是活见了鬼,这不都是好好的嘛。”他舅问清经过,叫把信拿出来看看。一看骂着外甥:“都是你这个述迷鬼,把点点错了不说,又写几个错字:忙字写成了‘亡’,料字写成了‘材’,理字写成了‘埋’,你不懂装懂,差点害死人。”
讲述:马耀辉 采录:卢华英杜秀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