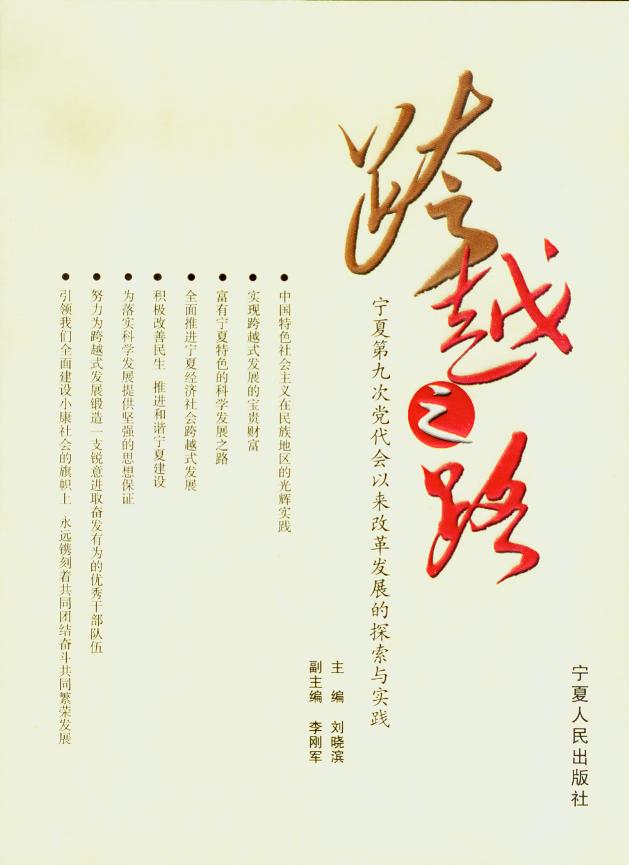凌柯聚精会神地盯着宫墙之上的某处,待那人消失不见,不由惋惜道:“他已经走了。”
“终于走了……快替我打水洗脸。”那老叟扯下花白的头发,露出齐腰的一头乌发。
凌柯打着瞌睡等她梳洗完毕,“我说驸马爷,你又何必如此?回去做他的摄政王妃不好么?”
驸马爷洗净了脸,露出原本清丽的一张脸来,弯弯的眉眼带着笑,却未笑到眼底,“你也看到了,他有佳人相伴,我又何必自取其辱。”
若是何子非再停留片刻,便会识破那老叟的易容之术,轻而易举地辨识出这不知好歹,说着混账话的——许知言。
“可他却未有放弃的念头。”凌柯挑眉道。
知言移开眼,“随他。”
知言辅佐黎皇读书完毕,便往安雅公主的府邸而来。安雅公主是黎皇的妹子,而年轻的帝师便是大黎安雅公主的驸马。
见车驾靠近,侍者高呼一声,“驸马爷到了!”
大门缓缓开启,安雅公主盈盈立在院中,眉角含笑。安雅公主不是旁人,恰是躲避余鹤如瘟神的叶舒。
彼时知言委托冷修找寻叶舒的下落,便将她一同带到了上城。凌柯本想给多年漂泊在外的姑母冠以大长公主的封号,却被她拒绝。
思前想后,不如折衷,凌柯便认了叶舒为义妹,封号安雅公主,如此一来,姑母便可安然住在上城,又不会被邻国那位偏执的摄政王骚扰。真乃一举两得!
此时此刻,安雅公主正挺着微微凸起的肚子,笑问,“这么晚了,驸马还过来?”
“太医说你胎位不稳,需要静养,怎么这便出来了?”知言上前握住叶舒的手,她的手微微寒凉,好似寒冰。
“我每日吃了便睡,身子愈发沉重。”叶舒笑道:“今日出来走走,倒觉得舒服多了。”
看到叶舒至此,知言不由心生愧疚,若不是她当日出事,叶舒也不会落入余鹤手中,哪知余大人是个冷面热心肠之人,毫无廉耻地欺负了“朋友妻”。
叶舒见她面色灰白,料想是遇到了不顺心之事,试探道:“都说他王来了,可是真的?”
知言点头,“确实是他。”
“那时他曾对我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到底是心中有你。”叶舒劝慰道。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她又何尝不是。可是此情此景,他们又如何相见?
摄政王有正妃,安雅公主有驸马。为何她与他之间,总隔着啼笑皆非?
第二日一早,安雅公主便请命去了北境。北境乃是多国交界之处,若是哪一日公主携夫君潜逃出境,也有数十个国家可去。
凌柯唇角一扬,远远望着浑然不知这一切的大陈摄政王,不由暗自叹息:“姑母大人,您这一手真是漂亮!”
凌柯当然是记仇之人,当日何子非的一箭致使他面上多了疤痕,如今就让他被万箭穿心来弥补。
坐观恶龙困于泥沼,妙哉!
何子非远望黎皇,见他对着自己举杯微笑,那笑容中,有怜悯、有期许,甚至有幸灾乐祸?
离京不过半月,丞相齐皓已经忙得焦头烂额,奏章堆积如山,苦等摄政王回来处理。
黎国之行结束,摄政王一行连忙返回西京。
何子非见到那奏章纹丝未动,不由厌烦道:“命你与岳南枝辅佐陛下,奏折怎会这般多?”
齐皓剑眉拧成一团,“摄政王有所不知,南枝有……有了。”
“所以?”何子非唇角下坠,已然不悦。
“她身子柔弱,孕吐反应极强,臣日夜照料……无心朝政。”齐皓倒是实话实说。
“你二人乃朝廷重臣,怎能因私废公?”何子非斜眼瞧了瞧奏折,第一份便是岳南枝请辞的折子。
看到摄政王墨眸微敛,就连站在他身后的韩霖亦躲远了些。
他培养多年的得力臂膀,竟然要主动请辞!何子非只觉太阳穴突突地跳。自太子之乱、楚端之祸以来,朝中官吏不足,又未至殿试之时,此时无人能用,当真令他头痛。
折子一封接着一封,眼看着又是令他不悦的:兵部尚书韩霖告假一月?
何子非压低了声音道:“你又是为何?”
韩霖扭捏半晌,低声道:“提亲。”
吏部尚书一职十分重要,还有谁能补这个缺?林照?不行,此人贪财,不可委以考核百官的重任。
吏部尚书,须公正严明,堂堂正正,令百官信服。
脑海中飞快闪过一张冰冷无情的脸,若说公正,莫过于大理寺卿余鹤。可余鹤不擅交际,又如何能领命吏部?若是假以时日,磨练心志,倒是可用。当务之急,便是给他一个施展的机会……而最近的机会,便是黎国北境与多国官员商洽互市一事。
可何子非怎么也没想到,委派边境的余鹤一去就是数月,迟迟不肯归来,好像北境那偏僻之所比西京还要繁华。
直至小皇帝孔然周岁之礼,余鹤才马不停蹄的回来。典礼当晚,小皇帝于摄政王怀中吮着手指,呆呆道:“娘……”
摄政王面皮一扯,“本王不是娘亲。”
小皇帝六个月早产,能够活命已是万幸。婴孩之时尚且与普通人没有差异,待月份大些,便显得蹊跷起来。每日上朝之时,小皇帝目光呆滞,一两个时辰不哭不闹,起初,也只道是小皇帝懂事,久而久之才发觉,这位天子,竟似是痴呆之态。
鸾太后每日吃斋念佛,以泪洗面。可孩子一日日长大,终究瞒不过世人的眼睛。
何子非看着怀中乖巧的娃娃,何其安静,又何其无辜。太医诊断数次,却都束手无策,难道陈国未来的国君,当真是如此模样?
新皇周岁的典礼直至深夜,值夜的御林军各个精神抖擞,却忽见一道黑影顺势而起,待追上前去,才发觉那是摄政王独坐龙隐殿的廊檐之上,不由悄悄退下。
越是心烦意乱,他便越想要一人独处。
何子非自怀中取出字迹模糊的一片衣襟,那是宫中琉璃冢的地形图。
何子非摄政之后,便彻底封死了琉璃冢。陈帝、魏后、太子孔诏,先太子杨绪、太宰陈倾都长眠于此。自琉璃冢被封之后,其上花枝璀璨,竟生长出独一无二的林园景致来。
“一直以来,我都置你于险境。”何子非握着那片衣角,头疼的厉害。若不是孔轩当日得了琉璃冢的地图,识破了楚端的覆国野心,又怎会有后来突如其来的形势逆转。
长风忽起,吹得他衣袂翻卷。何子非闭上眼,不由喃喃自语,“可你自始至终,却都处处为我考虑。”
一夜头痛,教何子非无心贪睡,只得早起。他正欲考察余鹤数月来的长进,哪知此人便又往北境而去。
岂有此理!
何子非命霜华暗中查访,便带出了些蛛丝马迹,原来除了吏部尚书余鹤,太史令冷修连日来数次往返黎国北境。
何子非唇角一勾,竟是笑了,“连一个提笔之吏都这般不安,莫不是风景那边独好?”
霜华眨了眨眼,声音清灵,“余鹤与安雅公主,私交甚密;冷修在北境有一处叫做令园别居的私宅。”
私宅?何子非眉头一拧,太史令冷修实乃木讷之人,怎么会在遥远的北境有一座私宅,那里究竟是埋着通天宝藏,还是有娇娘美妾?竟然令无欲无求的冷修魂不守舍。
“安雅公主此人如何?”何子非又问。
“安雅是黎皇的妹妹,数月前诞下一女。”霜华朱唇微启,似要多说些什么,却又恰到好处地停顿。
“驸马又是何许人也?”何子非却有些好奇。
“这……王爷何不自己去看看?”霜华忽然仰起脸,分明在笑,眼角却多了泪花。
何子非欲言又止,心上忽然升腾起前所未有地希冀。他迫不及待道:“备马!”
霜华笑中带泪,“早就备好了。”
“多谢。”何子非抬步便走。身子却忽然一滞,被人自身后紧紧抱住。
“是我鬼迷心窍,害得你们天各一方,你恨我么?”霜华不住地哽咽。
“若不是你,我亦不知,她竟比这如画江山更值得眷恋。”言毕,一根一根掰开她纤细的手指,匆忙而去。
黎国北境,虽是偏远之地,却是诸国毗邻之城。何子非起初答应与黎国互市,不过是借口亲至黎国,去找一找那里是否有他想见的人。
凌柯小儿,他定会要他人财两失!
那一日,偌大的西京城中一骑绝尘,只道是紫带金冠,风流倜傥的年轻人策马而出,招摇过市。
东街集市买菜的张大娘红了一张老脸,“哎呦呦,现在的年轻人,都这般英俊哟!”
城守面面相觑,只见一人一骑,如天神下凡般由远及近,“哗”地亮出明晃晃的腰牌,一时闪得军士眼花缭乱。
过了许久,有人惊呼道:“是摄政王!”
摄政王出城了!摄政王出城了!
齐皓闻此,已经是三个时辰之后。他来回踱步,气的七窍生烟,“好个何子非,竟然不声不响便走了,难道要把这个烂摊子留给我?”
怀中的小儿“哇”地一声啼哭起来。岳南枝放下手中的针线活,恰是一件孩儿的小衣。她微微侧首,娇嗔道:“做什么这样凶,吓到孩儿了。”
平日里严厉狠绝的丞相大人,脸上的情绪瞬间垮塌,匆忙哄着宝贝儿子道:“爹爹错了,孩儿莫哭,孩儿莫哭。”
岳南枝掩唇微笑,丞相大人果然色厉内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