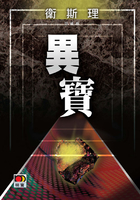子瞳放下碗,刚想说些什么,头脑突然一阵强烈的晕眩,扶着桌沿试图站起身,双腿却虚软得使不上力,她心念微动,低头看了看空掉的汤碗,再回思水婆婆的一番殷切异常的言语,立时明白问题出在汤里,她伸手想去拿汤碗,可眼前一黑,就此昏了过去。
水婆婆见状,稳了稳心神,这才急惶惶地出去报信。
不久,宅中众人见到公子的近身侍卫抱着个裹在棉被里看不清面目的人出去,再来一辆挂着帘幕的马车朝着城外方向驶去。
当天夜里,他们又见到马车驶了回来。
一切进行得隐秘悄然,沧海毫不知情。
直到第三日晚上,君平才惶恐地禀告沧海,说子瞳夫人已昏迷了两天两夜。
“什么?!”原本坐在前厅喝茶的沧海豁地站起身。
“子,子瞳夫人她……自从,三日前傍晚昏迷,到此刻,未醒。”君平结结巴巴地说。
“你们背着我都做了些什么?”沧海沉声说。
“你不用怪他们,这一切是我的主意。”长歌从后面房内来到前厅,身旁跟着前去报讯的君安。
“告诉我,究竟怎么回事。”沧海深吸口气,看着她。
“事到如今,我也不便隐瞒了。”长歌说:“本来我是想让她安静地睡上一觉,趁此机会让君平和君安将她送到别院。按照常理,她应该在两个时辰后醒来,可直到入夜,差不多四个时辰仍是昏迷,君平和君安唯恐有事,便将她带了回来。”
“你给她吃了迷药?”
长歌点头:“是。”
“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是说过暂缓一日送她去别院么?难道你连一日都等不了!”
长歌看着他,美艳的脸上浮起凄然笑容:“我不能让她留在这里,她会成为你复国的阻碍,我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即使你怪罪我,我仍要去做。”
“长歌……”沧海闭了闭眼,“我说过,子瞳那天不是故意伤我的。”
“你不是她,怎知她不是故意?”
“我知道。”沧海肯定地说:“她只是个住在深山里的姑母亲,根本不懂这些算计之事。她和我们不一样。”
长歌柔柔地笑了笑:“可你知道她熟读兵书么?她是个铸剑师。镇日与兵器为伍的人,怎能没有一颗狡猾机巧的心?”
沧海摇头:“就算她确实有伤我之心,那也只是为夺青霜剑。何况这一切只是我们平白猜测!”
“我宁愿错怪她,也不会放过一个任何有机会伤害你的人。”
长歌几乎是哭着说出这一句,然后转身离去,红裙翻飞间,飘成一朵灿烂盛开的花。
沧海看着,顿感浑身力气尽失,向后跌坐在椅子上。他如何不知道长歌对他的情深意重,只是伤到子瞳,他又于心何忍?
这一夜的后院小屋,不再像从前那般安宁。
大夫被下人引进房间,为子瞳诊脉后深锁着眉头说:“从脉象来看,这位夫人是服用了导致昏迷的药物,剂量虽有些过了但早该醒来。只是不知哪里出了差错,竟至长时间昏迷。”
沧海的眼凝成两潭坚冰,冷冷地告诫大夫,“若她醒不过来,你也不必活了。”
那大夫惊恐地擦了擦额头冷汗,心中叫苦连天,却也只能再次低头诊脉,沉思对策。
好一会儿,才提笔在纸上写下认为妥当的药方。
沧海等他写完,说:“子瞳夫人未醒来之前,你就在宅中候着,我会让下人安排一间房给你。没我的允许,决不许离开。”
大夫无奈,只得点头答应。
然后沧海找来君平,让他按照写好的方子去抓药。
他们离去以后,房内只剩下沧海与安静昏睡的子瞳。夜色浓重如墨,同时有大风呼啸着席卷而来,吹得门窗呜呜作响。沧海心中一片惊慌的杂乱。他搬一张椅坐在床边,看着子瞳本就苍白如今更无血色的脸,双眼紧紧闭着,再无初见时冰凉坚忍的光,唇角也失去倔强。
天色就在沧海的凝望与回忆中走向昏蒙,再撕扯着走到隐隐透出稀薄晨光。
长歌出现在屋门旁,已站立了许久,先是看向沧海,再循着他目光见到昏沉在床的子瞳。她缓缓走近,柔声说,“你在意她,是么?”
沧海回神,见到难得憔悴忧愁的长歌,“你们不该对她下药。她是否存心杀我,尚是疑问。”
“你在意她。”长歌执拗地说。
沧海叹了口气,“长歌,你在害怕。”
“我没有理由不去害怕。你心里有了她。”她颤抖着声音说。
沧海摇头道:“我没有爱上子瞳,长歌,我仍是爱你。只爱你。”
“你何必欺骗我,又欺骗自己。”长歌凄凉地笑了笑,“我能感觉到你心里的变化。沧海,我在你身边七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包括你自己。”
“那是因为她此刻昏迷不醒,我很担心。”
“怎样的缘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终究有了动容。”
沧海盯着她看,什么也不说。
长歌微笑,握起他一只冰冷的手,柔声说,“你也累了,回去休息一会儿再来看她,好么?”
“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沧海蓦地脱开她手,语声无比冷然:“因为她再也醒不过来了!因为这样说可以增加我内心的愧疚,从而让我更加珍惜眼前人,对么?!”
他叹一口气,“长歌,我对你的爱,不管遭遇什么、经过多久,都不会变。你只需牢牢记得这一点。”说完,撇下她独自离去。
长歌望着他挺拔清俊的背影,突觉这信誓旦旦的幸福涌进了些许悲伤。
她会记得他的爱,却也不会忘了他今日望着昏迷的子瞳时,眼中流露怜惜动容一如初见她的时刻。
子瞳从昏迷中醒来,是傍晚,小屋里除了她再没有旁人。她试着挪动身子,轻飘飘的。想起身,却使不上足够力气,只能软塌塌地躺着,脑子里一片令人沮丧的纷杂缭乱。
这时她听到有脚步声,赶忙闭上了眼,进来的人挨近床畔,眼睛搜寻过她整个身体,再落到左手的伤口。子瞳感觉得到那目光,充满了担忧与焦灼。
会是谁,沧海么?她想。
沧海坐下来,将头倚靠在床柱边,轻轻的、自语般地说:“子瞳,长歌对我说,我在意你,我告诉她我仍是只爱她。你知道吗?子瞳,这一生都不可能再有女子走进我的心,我和长歌一起经历过太多太多,那些往事已经成为我生命的本身,长歌亦成为我的生命。但是,我发誓会对你很好很好。你想家,我会陪你回去,或者我们一起把你父亲接到风城来,你们就可以每日相见了。但这些都要你醒来才能做到。快些醒来吧,子瞳。我很担心你,你一直这样睡下去就不寂寞么?”
他停了一停,接着说:“我还记得刚见到你的时候,剑炉里的火把你的脸蛋映得通红通红的……你知道吗,你身上有一股让人不能忽视的力量,在你用缝衣服的针制住那杀手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是个聪明机敏的姑母亲。我一直忘了跟你说,那件白色嫁衣你穿起来很好看,整个人就像都在发光一样。子瞳,大夫说要跟你多说话,你虽然昏迷着也是有知觉的。我和你说了这么多,你听到了么?快点儿醒来吧,你那么伶牙俐齿的,醒来跟我吵吵架也好。我知道,你一直睡着,是因为我们对你有怀疑,那么我告诉你,我愿意听你的解释,只要你亲口告诉我你并非存心伤我,我一定会信任你的。”
然后他俯下身去看子瞳,恍惚中她的睫毛似乎扑闪了一下,定睛去看,却仍是动也不动地昏睡在床。
又坐了一会儿,沧海离开。
子瞳等听不到他的脚步声,才睁开眼。“我只爱长歌,这一生都不可能再有女子走进我的心”那一番愿她醒来的话,她真正听入耳的,只有这一句,像在心口狠狠刺了一刀,顷刻间血流成河。她瞪着床顶覆盖的柔软纱帐,一张脸静静的、木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