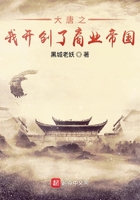我逃出之后,虽然只剩下70多个人,但我并没有灰心丧气,决定卷土重来。我直奔新乡,投靠到国民党保安第四总队上校总队长王三祝麾下,被王三祝委任为联防指挥官,继续进行反共复仇活动。
然而,时隔不久,共产党的大部队就挺进中原——共产党胜利在望。看着实力雄厚的王三祝都自顾不暇,命运难测。再想想自己作为败军之将,手上还沾满了共产党的血,戴着叛徒、汉奸的帽子,我不禁心灰意冷,悲哀至极。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偷偷带上妻妾及家人悄悄逃往郑州,从此踏上了逃亡的路。
当日军灰溜溜地败走之后,我就意识到自己当初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给日本人做汉奸。凭我的智慧与学识,应该非常清楚,日本作为侵略者,必定是失败的下场。而我投靠的日本这个靠山,终归是要倒的。而日本人倒了之后,作为汉奸的我,即使共产党不杀我,老百姓也不会放过我。
10
我带着家眷,逃到郑州,住了一段时间,因为这里离老家太近,不时会碰到认识我的人,很容易被发现,我不敢久留,急匆匆又跑到南京表哥家里。这时候,已经是1948年底。到了南京,我乔扮成商人,改名吴金山,搞到了一张“青丝良民”身份证,谎报原籍为徐州,职业写成经商,同时对全家老少十一口的户口也都作了仔细安排:把他们的原籍都写成徐州。就这样,我一家在风雨飘摇的南京城暂住下来。这时候,我的父亲已经作古,我的母亲及弟弟弟媳都跟随我外逃,因为我,他们已经无法在家乡生活了。
时隔不久,全国到处都成了共产党的天下,解放军逼近长江,南京危在旦夕,在解放军反攻的炮声中,我看到国民党达官贵人纷纷向广州、香港、台湾甚至国外逃跑。我不得不带着全家再次搬迁到苏州。到了苏州,我却发现这地方太小,我们的口音与当地百姓不同,很显眼,有个风吹草动很容易引起注意。为找到一个理想的隐身之地,我往上海跑了五六次。经过仔细考察,我发现上海是个好地方,城市庞大,环境复杂,人口密集。躲在上海的里弄里,无异于藏在深山老林,难以发现。还有一点,人多而杂,便于谋生。
我很快作出决定,举家搬到上海。在苏州,我们仅仅住了一个多月。
在上海,我们隐名埋姓,过起了躲藏的生活。那段时间,我们不断地变换住所,我的内心充满了惊恐与不安。
解放前夕的上海,通货膨胀,金元券越来越不值钱。全家11口人的生活,靠我倒卖银元维持。1949年,解放军打到上海,我想,解放军内肯定有不少北方人,一旦被认出,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我再次更换户口、姓名、籍贯,与家人分居。开始,我跟两个老婆住在宝山路。上海刚解放时候,户籍管理部门登记户口很简单,先发给每户一登记表,由自己填写后上交,从此就算有了合法户口。我在宝山路户口登记表上只填了我的母亲、二弟媳、侄子、侄女等人。我本人的户口、住处却在其美路庆阳里,并乘机将我的化名吴金山改作虞金山,同时把两个老婆都改姓虞,把小老婆袁小灿改成我的妹妹,解放后拥有两个老婆也是不允许的。
为了更好地隐藏,我首先摸清了上海的街道,熟悉了社会各界的情况,特别是方言。为了避开原籍柳青县,我为全家编造了假历史:原籍徐州,从小离开徐州来上海做生意,还要求每个人把徐州的街道、风景、地理、人情乃至方言土语都搞清楚,让他们背熟,还经常对他们考试、演习,来应付户籍警的盘问。
我在庆阳里居住时,非常害怕遇到北方人。这里南方人多,干什么的都有,流动性也大,住了一年多没发生什么问题,我也就安了心。
我把一家人隐身于浩如烟海的商贩之中,我整个人从服装到说话,包括举止行动,俨然是一个“老上海”了。我和我的老婆沈君兰与小妾袁小灿住在一处,让母亲跟二弟、三弟等另住在一处。为了不被发现,我不让母亲和弟弟知道我的住址,还告诫他们,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与我发生联系。那时候,我自信地认为,这样做即使共产党能找到我的家人,也无法找到我本人。
我再次吟咏起唐朝诗人贾岛的那首《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按照诗的意境,我时常保持着高度的警觉,遇到一点风吹草动,就马上寻迁新居,而且千方百计地斩断新旧居之间的联系,把自己隐身于“云深不知处”。
生活中我坚决不与外人来往,给人的印象是个“商人”,却不做生意,更不敢出入大街小巷。后来,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窘迫,为了生计,我苦思冥想,最后找了个谋生之路:让两个老婆做一些布鞋试着到市场上卖。布鞋拿到市场上出人意外地抢手,价格也不菲,做多少都能卖掉。我这才松了一口气,一家人的生计算有了着落。
后来,因二弟吴民与母亲不合,被母亲骂出家门。吴民一家三口身无分文,跑到我家求援,住在我家里不走。这下子,我不与任何人发生纵横关系的局面被打破。我心里又开始不安起来。更糟糕的是,三弟吴栩去北京卖房子,在北京住了两个多月,房子非但没卖出去,又去参加解放军当了军医。我心急如焚,如坐针毡,生怕吴栩供出我的住址来。
1951年,全国人民大张旗鼓地宣传镇压反革命。可是,吴栩还没有回上海,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对二弟吴民说:老三这个蠢才,看样子是不回来了,人家解放军一定会抓住他,抓住他肯定会问咱娘的地址。一旦知道咱娘的住址,就不愁拽出咱们。怎么办?只有搬家,切断线索。
我与吴民密谋后,费了四天时间,在岳州路找到了一幢草房,房东过去是保甲长,是这一带的流氓。此处基本没有北方人,环境很利于藏身。我们决定迁到这里。随着时局的变化,上海对转户口比以前认真了些,要求有证明,但迁移证是迁出人自己填写,这又给了我钻空子的机会。我在迁出证上照原户籍填写,在迁入证上把岳州路改为局门路,两路相差几十里,这个地方我根本没有住过,也不会被人(包括我的家人)知道。
我在岳州路住下不久,就去派出所报户口。派出所的户籍警看过我的迁出证后,在“局门路”三字旁边划了一条线,改为岳州路,户籍警问我,你到底是迁岳州路还是迁局门路?我支支吾吾说,是南北口音不同写错了。户籍警对我说,回去叫原派出所盖个章吧。两天后,我又让袁小灿去派出所报户口,这天派出所刚巧换人办理手续,她很轻易地就把户口报上了。我的这一步妙棋,在后来的多次查户口中,都未能查出破绽。
这时候,我母亲仍住在宝山路那幢小木屋里,对我的搬家一点也不清楚。但我仍不放心,我母亲不搬,跟我自己没搬一样。于是,我又催促我母亲搬家。我母亲哭哭啼啼不舍得离开,我劝她,宁可把那小木屋白白扔掉,也不能再来看房子。为了不让邻居们知道我母亲的住所,搬家时对邻居说,我们搬回南京了。
我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万无一失了。
11
上海市的民主改革工作继续开展,工作队分片包干,异常地认真负责。在我居住的那个只有五百户人家的小里弄里,就进驻了一个工作队。这时,我感到了气氛的紧张。在一个晚上,我特别提醒我的女人,说,这一段可能会有人找我们谈话,不要害怕,一阵风过后就散了。千万记清楚,必须说成咱们老家是徐州,从小离开家,一直在外做小生意。我又反复地把徐州的风土人情讲给她们听,让她们牢记在心。
我还对跟随多年的老炊事员秦敬说,老秦伙计,这几天工作队如果找你谈话问情况,一定要记住我教你的话,从8岁起到现在干什么,千万别说脱口。
工作队进驻以后,经常召开群众大会,宣讲民主改革政策。秦敬吓得天天心神不宁。我为了安慰秦敬,常跟他一起逛马路,看电影,还给他买糖果吃。经过精心筹划,我终于又蒙混过关。
1955年,上海再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里弄里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被揪出来枪毙,我的心再次被吊起来,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因为经历了多次的周旋,我尽管内心不安,却能坦然面对共产党的追查。然而,也许是天意,也许是报应,最终,共产党还是通过我的三弟吴栩这条线索把我擒获,我最初的担心成为现实。这一天是1956年9月16日。
柳青县抓获我的专案小组通过老三吴栩这条线,确认我躲藏在上海,他们在上海找我,无异于大海捞针。但他们的决心太大了,整整侦察了五年。最后发现了炊事员秦敬,秘密抓捕了他。秦敬抵不住共产党的攻心,一下子全都吐了出来。
当我发觉秦敬失踪之后,不详的预感笼罩在我的心头。但是,我不能束手就擒,要做最后一赌。我开始筹措潜逃用款,到信用社谎称去安徽贩卖毛竹,要求贷款。这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已经进入了共产党的视野,他们对我的行动了如指掌。信用社也参与到抓捕我的行动中,先通知我已批准了贷款申请,还约定了办手续的时间。我去信用社办手续的时候,信用社的工作人员已经换成了柳青县专案小组和上海市公安局的人员。
有人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虞金山。
又问,哪里人?
我用十分流利的徐州口音从容地回答着,原籍徐州,从小就离家在外做生意……
这时,问话的人突然一拍桌子,厉声喝道,吴仁,你别再演戏了!
刹那,我怔住了。回过神来,我突然浑身发抖,瘫坐在地上,我在心里沮丧地说,我一直想躲过这一天,这一天还是来到了……
接下来,我的二弟吴民、小老婆袁小灿也随即被抓获。
这时候,我才知道,共产党各级领导对我的案件是史无前例的重视。早在1950年10月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候,曾在豫北地委担任过书记、后来成为高干的王武就会同国家公安部给河南省公安厅发出命令:一定要不惜人力、物力将吴仁抓获归案,并强调“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从那时候起,中央、省、地委及柳青县就组织了强有力的专案小组,展开了对我的追捕工作。
枪声一响,我就来到了这里,孟婆庄,向您陈述我的一生。我非常清楚,我是罪有应得,我欠下的血债,终于得以偿还。尽管我和我的弟弟,还有袁小灿的三条命,远远抵不过我犯下的罪孽,我的忏悔更是显得苍白无力,但我只能这样了。时光不能倒流,我的人生也不可能重新开始,过去的一切,都将被历史记载,永远都无法颠覆。
关于我的叛变,多数人认为我是因为女人,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我在追悔自己行为的同时,我不能不想起余谦、信西华这样的左倾主义者。试问,在我的叛变过程中,他们不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吗?
回顾自己罪恶的后半生,现在客观地分析我叛变的原因,我感觉,除了余谦与信西华的逼迫,关键的应该还有两点,一是自己对信仰的缺失,二是自己的自私与狭隘。而自己对共产党干部及其家属的残忍与疯狂,则是歇斯底里的报复与泄恨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是余谦与信西华辜负了我——而他们,代表的是共产党。我只能把仇恨,记在共产党头上。
孟婆奶奶,我知道,在您这里,登记完之后,我将喝下一碗迷魂汤,忘记前世的一切,走过奈何桥,转世托生。
尾声
孟婆听完吴仁的叙说,面无表情,好长时间都不说话。孟婆身边的三位美丽姑娘孟姜、孟庸、孟弋也沉默不语。她们为吴仁的罪恶而震惊。
良久,孟婆对吴仁说,你还想转世托生?你前世的罪孽如此深重,怕是阴间也照样容不下你这种恶魔,要对你严加惩处。
吴仁听后,惊恐地说,孟婆奶奶,我已经忏悔了,我忏悔还不行吗?
孟婆冷漠地说道,你犯下的罪恶,仅仅忏悔就够了吗?
孟婆又对三位美丽姑娘说,你们去把吴仁带到奈何桥下。
这奈何桥分三层,生时行善事的走上层,善恶兼半的走中层,行恶的就走下层。下边是忘川河,河水一片血红,里面全是不得投胎转世的恶鬼,虫蛇满布,腥风扑面,波涛翻滚。行恶的鬼魂从奈何桥下层走过的时候,就会被恶鬼拦住,拖入污浊的波涛之中,为铜蛇铁狗咬噬,受尽折磨不得解脱。
吴仁被三个美丽的姑娘押解着,来到奈何桥头。看着桥下蛇虫乱舞,厉鬼尖嚎,胆战心惊。
他不禁仰天惊呼:拿什么,可以救赎我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