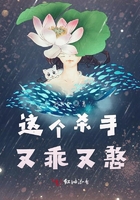“唔?”林飞羽难掩笑意,“你还懂风水哟?”
“不是说有把铁铲就能盗墓啊……”喇嘛唇角微颤,像是笑了一下,但旋即又恢复了之前的苦瓜脸,“这个墓没有任何的地面部分,只是一个很自然的小坡,上面也没有种树,就是杂草丛生的样子——”
以林飞羽的绘画水平,在描述这段景象的时候,也就只是象征性地画了一条代表“地平线”的黑条而已。
“入口被一整块巨石封死,从外面看就以为只是自然形成的岩块,根本不会想到里面别有洞天……”喇嘛的语速渐渐快了起来,“我们花了差不多两天的时间,才把石块敲碎移开。”
“两天?”林飞羽一愣。
“我们也没有想到会花那么久……但许霆不允许我们使用炸药,所以只好用一些原始的工具来做事。”
“你们就不怕被人发现?”
“怕,怎么不怕?”喇嘛顿了顿,“我们当时打算,如果被人发现,就给他一千块封口费——对当地人应该是足够了。”
“好,继续,你们凿开了石头之后?”
“巨石后面是一条甬道,有石砌的台阶,差不多45度左右的倾角,大概10米长……也许不到,但至少也有个七八米吧。”
“唔,45度的倾斜甬道……”林飞羽一边点着头,一边在屏幕上画着,“在中国的墓葬建筑中确实不常见。”
等等——他捏着手写笔的食指和拇指突然微微抽搐了一下,好像是为了要提醒什么似的,某个潜藏于记忆深处的声音在耳边轻声低吟了几句,但这种感觉转瞬即逝,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什么都回忆不起来了。
“等我们弄走巨石,差不多已经是第二天的黄昏了,由于不清楚里面的环境和空气状况,我们决定等到清晨的时候再进去。”
在职业盗墓人口中,这种等待的行为通常被称为“晾一会儿”——非常形象也很有意义。当然,对于扒开坟头就敢往里面冲的业余选手来说,这样做纯粹是浪费时间。
“甬道低矮,窄,做工也很糙,”喇嘛摇摇头,“就像是在土堆上直接挖了一个洞下去,这样的感觉……连台阶都是直接用泥土抠出来的。”
林飞羽一边“嗯嗯”地应着,一边在屏幕上画上草图:
“是夯土吗?”
“夯土……是什么?”
林飞羽顿了顿笔,决定还是不要和他纠结这种细节性的术语问题了:
“你继续,在甬道下面是什么?”
“甬道下面,底部,就在底部,竟然还有一块封石!大小刚好将路堵死,只留了一点点缝隙,连个指头也伸不过去。”说到这里,桑洛扎巴突然笑了,“……当时我们就互相责怪了起来,连那个许霆都生气了。”
“唔,我能理解,”林飞羽点点头,“等于是你们之前‘白晾’了一晚上。”
“对,墓穴等于还是没有开苞。我们争论了一会儿后,决定使用雷管来节约时间。”
“你们用了雷管来炸开石门?”
“不,不是‘石门’,只是一块‘石面’,打磨得很光滑,但我们当时根本就不知道它有多厚,也不知道那是不是什么门,说不准在它后面什么都没有呢。”
“还真没见过这样的设计,”林飞羽舔了舔嘴唇,“真遗憾你们不是考古学家,没留下记录就把它给炸了。”
“打爆孔的时候,我们发现石板很薄,大概只有一拃宽吧,”喇嘛伸手比画了一下,“所以最后并没有用上雷管,锹子和锤子就够了。”
“唔,设备倒还挺环保……”林飞羽揶揄道,“把那石板撬开又费了你们不少劲儿吧?”
“还行吧,我们也不是新手了……最困难的部分是把碎石和土渣运出甬道,这确实花了不少工夫。”桑洛扎巴像是在回忆似的停顿了片刻,“而且我记得……那时候许霆还要求我们把碎掉的石板在外面重新拼好给他过目,这也很麻烦,而且到最后也没拼出个完整的图案来。”
也许是职业的关系,林飞羽对那些在原有逻辑系统中突然冒出来的“新概念”总是特别敏感:
“图案?你刚才说……图案?”
“对,就是石板上的图案,怎么了?”
“描述一下——”林飞羽将手写笔绕着拇指转了几圈,然后一把捏住,点了点屏幕,“越详细越好。”
“这个……我还真记不得了,”喇嘛面露难色:“约莫是一米见方吧?反正挺大的,形状嘛……就是黑乎乎的一团,有点像太阳,反正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也许是墓主人画的符之类吧?”
“那许霆为什么会要你们把它重新拼起来?”
“谁知道他呢?”喇嘛有气无力地道,“反正从开墓起,他就一直呆在外面指手画脚,连甬道都没有进去过。”
林飞羽隐约觉得这里面有什么蹊跷,但一时又想不出来,于是点头示意对方继续。
“砸碎石板后,里面就是墓室了——”说到这里,桑洛扎巴忽然叹了一声,“哦!那可真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精美的墓室,地板、天花板和墙都是石壁砌成,一块一块的,刻满了各种我看不懂的符号和文字……”
“唔,精美的墓室,却有一个土得掉渣的甬道,”林飞羽若有所思地道,“听起来就非常不合理,莫非是修墓修到最后发现没钱了?”
“不,虽然不知道修墓的人是谁,但我肯定他非常有钱,你能相信吗?他在墓里还砌了石井。”
林飞羽眉角一扬:
“井?”
他抬起头,看了看后排的两人——一个正襟危坐,一个面无表情,似乎都对“墓里有井”这种咄咄怪事没有产生多大的好奇……或者说,困惑。
“‘井’?你确定你没搞错?”
“嗯?”喇嘛还有点被问住了的意思。
“井,”林飞羽咽了咽喉咙,“特指‘一种取用地下水的垂向汇水建筑’,你确定你没有搞错?”
“至少在我看的时候,四口井里都是有水的,水位离井口最多也就是两米左右吧……”
“你……你等等,”林飞羽笑道,“四口井?大师你没喝多吧?”
“出家人不打诳语,再说……我干嘛要骗你们?你们不是国家安全保卫局的吗?”
带着“反被摆了一道”的感觉,无话可说的林飞羽在屏幕上画了四个“圈子”:
“好的,姑且信你……四口井,怎么看这墓室的规模都得超过一个村子了,但你说入口距离河岸只有三十米?是三十米吗?”
“不,墓室没那么大,估计也就是……”喇嘛回忆了几秒,“五十平米吧,五十平米最多了。”
林飞羽低下头捏了捏眉框——他在脑海里对“五十平方米”这个概念进行了一番仔细的推敲,不禁更加觉得对方是在信口雌黄:
“五十平米的地方,还放了四口井?你这是在说自来水厂吗?”
“真的是墓室!棺材就在正中央——”喇嘛有点急了的样子,“还是雪花石的呢!光棺盖就有好几十公斤!”
林飞羽捂住脑门摇了摇头,又冲叶枫打了个响指:
“喂,你听说过这种事吗?在自己的墓里修四口井?”
“没有。”
叶枫的表态一如既往——像面瘫似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但是前辈,我认为这种行为具备存在的可能性。”
林飞羽无话可说,只得在平板电脑上的屏幕中间又画上了一个长方形——以此代表石棺。
“接下来呢?你们撬开了棺材板儿,发现了什么?”
“尸体啊,当然是尸体。”
“能看出是什么人的尸体吗?”
“已经全烂了……”说这句话的时候,喇叭双手合十,又碎碎念了几句,“……它仰面朝上,双手交叠在小腹,身上就剩了点破布,其他什么都没有。”
“陪葬品呢?”
“真的没有,空无一物,除了人,棺材里连块值钱的石头都没有找到。”
“那警察找到的赃物是什么?”林飞羽突然脸一横,“你是记忆力真不行了呢,还是故意在这里跟我耗时间?”
“赃物?”桑洛扎巴先是一愣,继而哭笑不得地道,“……你说那些破玩意儿啊,都是堆在墓的角落里,一看就知道不值什么钱。”
“就说那些破玩意儿,”林飞羽用笔尖弹了弹屏幕,“在墓里时是什么样的?”
“这个我真不知道,”喇嘛不紧不慢地摇摇头,“翻墓的时候,我人已经在外面了,在和许霆谈分赃的事情。”
林飞羽突然觉得,这或许才是问题的关键——
“分赃?这个不应该是一开始就谈好的吗?”
“对,按规矩,是应该先约好销赃后分钱的比例,一般是三七开……但他很特别,他说他不要钱,但要求所有挖出来的东西,必须先过他的目。”
“听起来对你们挺优惠。”
“听起来是,哈!”喇嘛干笑一声,“可我们实际上什么都没挖出来不是吗?所以我爹才会叫我和他再谈谈。”
“那你又谈了些什么?”
“真记不得了……总之,最后我们还是按他的要求去做了,把所有掏出来的东西在他面前一字排开,让他一件一件看过去。”桑洛扎巴顿了顿,“他看得很仔细,打开了每一个陶筒,取出里面的羊皮卷,摊在地上,用放大镜一个一个地看过去。”
“羊皮卷……放在陶筒里……”林飞羽不解地自语道,“这他妈是哪个朝代的规矩啊?”
“反正上面的字我一个也认不出来,当时只是觉得都是些不值钱的文书而已,所以他要什么就随便他拿了。”
“那他挑中了什么?”
“几张羊皮卷,大概是……三四张吧?他一把就塞进了包里,然后当场付给了我们剩下的二万五千元。”
“现金?”
“现金,然后人就走了,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
“唔……”林飞羽若有所悟地点点头,“也就是说许霆应该已经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可能吧,反正我们拿了钱,带上一些看起来比较完整的文物就走了。”喇嘛叹了口气,“啊……贪心啊……都是报应,我们应该把那些都还回去的……”
“‘报应’?”林飞羽一声哼笑,“遭了报应当然会这么说,盗墓的时候你们咋就没想到呢?”
“其实那次活儿,我一开始就是反对的,”桑洛扎巴有些懊恼地道,“但家里人说干完这票就收手,而且对方的开价真的很高,我们实在没有理由拒绝……现在想来,都是那妖人的诡计啊。”
“刚才是报应,现在又是妖术了……你说这些,警察恐怕完全不会相信吧?”
“哼——”喇嘛苦笑道,“警察审我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那时候脑子完全一团乱麻,没日没夜地看到一些……”
他咽了咽喉咙,像是有什么苦痛似的欲言又止。
“但是我信——”林飞羽轻轻摁住他的肩膀,掷地有声地道,“妖术也好,报应也好,不管警方是什么态度,我都愿意相信你的遭遇与经历,而只要你肯说出详情,我们就有办法来帮你摆脱它。”
林飞羽并不是为了安抚对方而说大话,第七特勤处创立的初衷之一,就是消灭所有“妖术报应降头诅咒”之类祸害百姓却又不可言说的糟糕物——而要消灭它们,首先就必须正视它们的存在,回避与讥讽并不是解决问题应有的态度。
更何况,现在的林飞羽,已经百分之百确信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错觉”,与赵信曾经面对的“妖术”如出一辙——说不定还就真是一人所为。
“详情?”桑洛扎巴避开林飞羽的视线,把头偏向车窗,“我皈依在这里,就是为了忘记那些事情……我没什么‘详情’好说的。”
“你的兄弟死了,你的父亲死了,只有你活了下来,”林飞羽冷冷地道,“你难道不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吗?你难道不想……”他本来想说“为他们报仇”,但考虑到对方出家人的身份,于是又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换了一句更温和的表述,“难道不想让许霆受到应有的惩罚?”
喇嘛不语,依旧是默默望着窗外的夜幕。
“好,就让我和你直说了吧……”林飞羽忽然加快了语速,“现在我的——我们的手头上有一个案子,关系到好几条人命,而凶手很可能就是当年雇佣你的许霆。我们现在对他的作案手法还不甚了解,对他的动机也是一无所知,既没有证人也找不到线索,现在解开谜题的唯一钥匙……”他有意顿了顿,“就是你了,桑洛扎巴。”
“唯有这件事,我帮不了你。”喇嘛合上眼睛道,“那时候的一切都太过混乱,我分不清哪些是现实,哪些是虚妄……既然我的话事关重大,那就更不能胡说八道,对不对?”
“是不是胡说八道,得由我们来判断,”林飞羽眉头一横,“你看到了什么样的幻觉,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破案的关键。”
“不是我故意隐瞒,但那段记忆真的很模糊,我不知道要从何说起。”
“比如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狗’……”林飞羽决定拿出杀手锏来,“在幻觉中,你曾经被一群‘不存在’的狗袭击过,有这回事儿吧?”
喇嘛沉默了几秒:
“……嗯,是在看守所里的时候,我大喊大叫,还被人揍了一……”他突然收住声,睁开了眼睛,扭过头来,一脸迷惑地看着林飞羽:
“等等,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件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为了掩饰心中隐隐的紧张感,林飞羽撩了一下额前微卷的刘海:
“并不是只有你被幻想中的德国牧羊犬袭击过,我说了,受害者还有其他人,他们也……”
“什么犬?”桑洛扎巴眼角一跳,“你……你刚才说什么国什么犬?”
被问住了似的,林飞羽愣了几秒:“德国牧羊犬啊……”考虑到对方的“见识”,他忙改口道,“一种大狼狗,通常是黑色的。”
喇嘛一边摇着头,一边连说了好几个“不”:“我看见的不是黑狗,是大黄狗,是土狗,土狗。”
虽然达不到“晴天霹雳”的程度,但林飞羽还是被和尚的这句话给彻底说呆了——他嘴角微启,眼神凝滞,僵在两人面前足足有十好几秒。
“土、土狗?”像是在求助一般,林飞羽将目光移向了叶枫,“土狗是、是什么玩意儿?”
“土狗,”叶枫点点头,一本正经地答道,“学名‘中华田园犬’,起源为东南亚狼。体型中等,耳朵下弯,尾巴粗且向上卷曲,中短毛,颜色多以黄、白、黑或混色为主,性格温顺,可以群居,地位域强,容易饲养,忠诚度高,不易生皮肤病,被广泛用于我国农村的看家护院及狩猎活动。”
“当我没问,谢谢。”林飞羽又转向桑洛扎巴,“那么醉汉呢?遇到过吗?还有穿运动服的怪人呢?都没见过?”
取代回答的,是一阵令人尴尬不已的沉默。
车厢内的三人面面相觑,其中两位的脸上还挂满了迷茫与困惑,而另一个……则像是一位事不关己的局外人,端端正正地板着扑克脸,一动不动。这滑稽的场面持续了整整一分钟之后,以林飞羽的一声哀叹收尾:
“……好吧,这儿有夜宵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