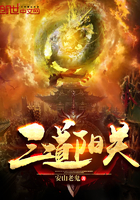(二)
大中八年(854)春平康里
“翠色连荒岸,烟姿入远楼。影铺春水面,花落钓人头。根老藏鱼窟,枝底系客舟。萧萧风雨夜,惊梦复添愁。”
大唐长安,一个暮春的江边,一位年仅十岁的少女看着眼前翠色连江的细柳,绣口一吐,一首意境迭出的五言律诗顿刻生成。她身旁,一位其貌不扬,但风度翩翩的白衣书生为其抚掌,连连称妙。少女羞赧一笑,一双美目眼波流转,偷瞄着身旁这位白衣书生,神色间充满爱慕。他只对她稍稍多望了一眼,少女的脸顿时羞成了桃花。她羞涩地低着头,只趁他目光游离至别处时才敢瞄上两眼。
眼前这个男人大耳、肉鼻、阔嘴、貌似钟馗,年长她三十余岁。她仰慕他的才情,超出了崇拜的范畴。他惊艳于她的天赋,更喜欢她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
那一日,她陪着他漫步江边,在诗情画意间谈论着诗情画意,整整一天,他们都沉醉在这暮春的美好光景中。
日暮时分,他送她回家,一树桃花落满了他们的归路。一路上,依旧风声谈笑,意犹未尽,俨然是一对忘年交了。快乐的时光终是短暂的,少女到家了——这是长安的平康里,烟柳巷,亦是她的家。而他,终是要离开的。少女要送他一程,他犹豫了一下,终还是同意了。
平康里的桃花树依旧落花如雨,铺满陌上,白衣书生牵着一匹枣红马,少女含泪的眼波尽是不舍,他望着眼前年轻的容颜,娇艳的美,白净的肌肤,飘扬的长发,以及泪珠滚动的双眸。他轻轻俯下身子,温柔地将泪珠拭去。用温和地口气安慰她:“幼微不许哭,小脸哭花了可就不漂亮了,不漂亮了老师就不喜欢了。”少女立即抽出手帕,将那点儿泪花抹干净了,乖巧地说:“幼微是高兴,因为见到老师了,所以..幼微不哭了,以后也不哭了!老师,您还会回来看我吗?”
“当然,老师答应你,等我们幼微长成大姑娘了,一个大美人,老师就回来,回来给我们幼微做个老书童,到时候你可不要看不起我这个老头子哦!”他尽量将话说得幽默、俏皮,为缓和一下这离别的愁绪。
少女终于露出笑脸,打趣道:“那我们谁都不许反悔,我负责长成大美人,老师负责给我做老书童,谁反悔谁小狗哈!”
他闻言大笑,捋着长须,应道:“好好好,我温长卿后半辈子就给我这如花似玉的女徒弟做书童啦!哈哈哈..”
不多时,路边现一长亭,不知不觉中已送出十里之地了。
温庭筠停住脚步,对幼微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我们就此别过吧!”说完翻身上马,示意幼微快快回家。
幼微假装转身离去,却躲在不远处的树丛中,目送他离开,直到他策马扬鞭的身影消失在桃花流水的尽头,方才返身离去。此时,已是黄昏,夕阳从远山落下,天际出现一道艳紫,那样冷凝的颜色,像千万年才成就的一块琥珀。温庭筠就像是鱼幼微心中的琥珀,滟影流光,完美无瑕。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一晃四年光景过去了。又是一年春暖花开,又是士子们春风得意,获取功名之时。一旦得中,大都“喜过还疑梦,狂来不似儒”,很少有人能够“还是平时旧滋味,漫垂鞭袖过西街”似的淡然。
而此时的温庭筠郁郁不得志,仅在河南方城任职方城尉,仕途的落魄让他心灰意冷,终日里出入于烟花巷陌,在花天酒地、纵情声色中麻醉自己。
这日,温庭筠从青楼出来,已然喝高了。正准备回客栈时当街被人叫住,他回身看时,已是醉眼朦胧,眼前一片模糊,所有的光影似乎都混搅在了一起,五颜六色,就是没有一处是看得清楚的。他使劲揉了揉惺忪的醉眼,定了定神,但见眼前一位小哥,二十岁上下,浓眉俊目,面如冠玉,衣冠楚楚,亦是名门望族的打扮。
来人道:“飞卿兄莫不是不认识小弟了,我是子安啊!”温庭筠这才想起来,此人名叫李亿,字子安,一位同乡故友,虽然两人之间年龄也相差了二十余岁,但在读书人的圈子里,大家还是兄弟相称。温庭筠不想竟然他乡遇故知,心中悲闷先散去一半,连连抱拳道:“哎呀!原来是子安贤弟,愚兄失礼啦!还请贤弟多多海涵啊!”两个同乡故友客套寒暄一番后,找了间小酒馆开始叙旧。
这不说不要紧,一说吓一跳,这李亿此时已是新科状元,温庭筠顿时惊得连筷子都没拿住,慌忙起身参拜,他万万没想到李亿状元及第,更没想到的是这状元郎竟然能屈尊与自己同桌对饮,一时无语,更无力掩饰自己的慌张与不安。
这李亿倒是平和,连连摆手,言道:“飞卿兄莫要拘谨,世人都将兄长与李义山(李商隐)相提并论,合称“温李”,如今兄长的大名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我李亿不过一介秀才,虽侥幸得中,不过名垂青史之人必是飞卿兄啊!”
温庭筠虽然酒喝得高了些,但深知此乃李亿故作谦和的一种说辞,断不能信,更不可顺杆爬,忙连连摇手道:“子安贤弟折杀愚兄啦!我哪里可与状元郎相提并论。贤弟金榜题名,日后必是国之栋梁,愚兄只可如那闲云野鹤一般,在吟诗作赋中了此残生罢了。”
李亿闻此抬举,心里自是舒畅,不过并不露喜色,仍旧抬高温庭筠道:“哪里哪里,飞卿兄的才情举目无双,只是暂不得志,但**************,一遇风云变化龙啊!”
温庭筠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昂首将一樽酒饮尽。之后二人推杯换盏,畅谈人生、理想、抱负,又兄弟相称,早没了官场的拘束和礼节。
菜过五味,酒过三巡,李亿突然话锋一转,道:“飞卿兄啊!其实今天请兄长喝酒实有一事相求啊!不知兄长可否成全?”只道是酒醉心明,温庭筠虽然喝得酒酣耳热,但早想到李亿以新科状元之姿请他喝酒,必有其目的,只不过实在想不出状元郎有什么事情会相求于他,又不好直说,只应和了几句文人之间相互吹捧的客套话,看来现在李亿是要直抒胸臆了。温庭筠心里好奇,但仍装出一副淡定模样,不紧不慢地说:“贤弟客气,你我兄弟有话自当直说,只要愚兄能帮上忙,是义不容辞啊!”
李亿忙起身给温庭筠满满斟上一樽酒,感谢道:“呵呵,有飞卿兄这句话就够了。实不相瞒,这事当真只有兄长能够帮上忙啊!”
温庭筠笑道:“贤弟不要再卖关子啦!如今贤弟状元及第,炙手可热,多少人想攀龙附凤都来不及呢!还有什么事情轮得到愚兄帮忙啊?”言罢又打趣道:“不会是看上长安城的哪个娘子了吧?”
李亿听罢大笑:“我说飞卿兄有佐世之才吧!你看,果如诸葛孔明一般神机妙算啊!”温庭筠本是打趣而已,不料竟然言中,很是诧异,心想:李亿状元及第,前程不可限量,况且生得俊朗,眉清目秀,可谓才貌双全,可能这赶着送上门的大姑娘、小娘子都挤破了头吧!他还会缺女人?
李亿说罢从内衣口袋内掏出一张纸,递给温庭筠,道:“飞卿兄,现世上诗词歌赋没有人比得上兄长啦!小弟这里抄录了一首诗,请兄长过目。”
温庭筠礼节性地谦虚了一下,缓缓将纸张展开,见里面抄了一首七言绝句——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温庭筠看罢,对李亿道:“愚兄若没有猜错,贤弟看上的姑娘,就是这首诗的作者吧?”
李亿微笑着点点头,不置可否。
温庭筠一边欣赏着,一边捋着须髯,赞道:“确实好文采,而且带着几分倔强不羁,你看这‘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就有几分自觉是女儿身,空有一腔才情抱负,不能金榜题名的愤懑啊!有点意思。”李亿不觉抚掌,道:“飞卿兄果然不是浪得虚名,子安佩服啊!”
温庭筠惭愧地笑了笑:“哪里,徒有虚名而已,还让贤弟见笑了。”随即好像又想起什么,问道:“可是不知此事我能帮什么忙呢?”
李亿神秘一笑,凑近温庭筠耳边,轻声说了一句:“作诗之人,飞卿兄认识。”
温庭筠一怔,不免又将诗稿再看了看,细细回味,不再言语,似乎心中已有了三分答案。李亿见温庭筠不语,心想他肯定已猜出诗的作者,但并不点破,继续说道:“这件事情还要从三日之前说起..”
李亿借着酒劲,向温庭筠诉说着三天前的那场奇遇。
此时,已是夜色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