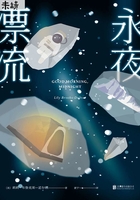白荷在自己的房中,最初的几天,以泪洗面。她思想了很多,很多。她不知道自己在新婚的第一天就怎么得罪了自己的天。在这一带地区,女人们称自己的丈夫为天。是自己长的丑吗?不入丈夫的眼,惹得白荷一天几次照镜子,自忖自己长相也不算丑陋,模样在她见过的女人中,也算说得过去,算个中上等的女人吧。随着后边涌来的日子,白荷麻木了。她也就不想那么多了。心里自己解劝自己,全当他去经商了。白荷为什么这么想呢?在家时,她姨妈家的一个叫梅表姐的丈夫,长年在外经商,很少回家。仅在年节时候,回来住到正月十五,就又起程了。后来,梅表姐有事到她家来小住几日。她俏俏地问梅表姐这事儿,她见梅表姐眼圈儿红了,落下两行泪来,又听她愤愤地说:“全当没有他, 我是守活寡。”白荷想起梅表姐说全当丈夫死了这句话儿,怎么,再怎么也不能出自白荷之口。不管怎么说,是康宁把她迎进他家。他们又是拜过天地,拜过父母高堂,是自己正儿八百的丈夫,是自己的天。自忖,她不能没有天,她不能欺天。她不相信,丈夫看不中自己。她认为是丈夫太年轻,不免耍小娃娃性子,小娃娃脾气。待他停上一段儿,火气消了,脾气下了,我们就会和好了。不是有一首俚曲,是这样说的:
天上下雨地下流,
小两口吵架不记仇。
白天吃的一锅饭,
天黑睡的一枕头。
想到这儿,白荷不觉噗哧一声自己笑了。她想到丈夫在新婚的头一天晚上都没有同自己睡在一架床上,更没有枕一个枕头,她不免又重重地叹了口气。她暗自叹自己命苦,上天让自己受这等磨难……不觉泪又双行地流下来。她抬头望着窗外,听着外边石榴树上那软软的枝条上,一只小鸟也孤寂地嘤嘤地叫着。
崔白荷夫人让赵老管家派人去她娘家取她的文房四宝,去把她过去在家修习的字帖也送来。赵老管家说:“我跟老爷说一声儿,去县城跟你买一套新的文房四宝来。再买几本新字帖。”
康少奶奶说:“你只管派人去取,就是了。”说罢,扭脸儿走了。
赵老管家为康宁在新婚当天出走的事儿,差点被康老爷辞退,若不是康夫人从中说合,赵老管家差点丢了饭碗。为这事儿,他没少受康少奶奶的脸色。下午,下人就从县城崔府取回来她所要的文房四宝和一些十分陈旧的法帖。赵老管家心里想,字写得咋样,法帖还不少呢!
白荷这个康少奶奶,自从拿来自己的文房四宝,她就把自己的屋子,收拾得跟书房一样雅致,洁净,每天都伏案书写,她用薛涛笺抄写《金钢经》,蝇头小楷个个写得颇具神采。有时候,高兴了她驻笔吟上一段儿。下面就是高兴时常念的一段儿:
“须菩提,于意云何?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宁为多不?””须菩提:“甚多!世薄,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多!”
“若夏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他人说,其福胜彼。何以故?须菩提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所谓佛手者,即非佛者。”
白荷夫人这时候心田一片静明,犹如一片皓月之光,如软软轻轻的圣洁的羽毛,撒陈在她的面前。
7、康宁知晓了,小野秋子染烈性传染病身亡,使他伤心不已。他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最大的伤痛。怎么也不能忘却小野秋子姑娘对他那种刻骨铭心的爱。康宁夜不能寐,当他一闭上眼,她就亭亭玉立的站在他的眼前。当他沉沉睡着,她就会出现在他的梦境里。
小野秋子和他坐在去东京湾那边的火车上。小野姑娘坐在靠窗子的座位上。康宁坐在她斜对面隔着过道的位置上,看出了她一副郁闷的心情。他知道她不高兴,是今天火车上人太多。他俩一齐上车,拥挤的人群把他们从中隔开,这才使得两只交颈的鸳鸯分开了。康宁看着小野秋子身后车窗玻璃上有朦朦水气,她从衣袋掏出一块柔软而洁白的纸帕,扭身把车窗上的水气,从外到里一圈儿一圈儿地拭去,就象外科护士对伤口消毒。最终,把一块玻璃拭得如一片湛蓝的湖面。她的头影,投视在湖面,远远看去,是那样的美丽。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像一个姣俏的少女在湖泊里游泳,水面平静如镜。
随着火车制动闸的缓缓刹住,火车身上的各个关节部位都发出吱吱嘎嘎的金属响声,声音有大有小。火车停靠在一个县界的小站上,从站台涌上来一群人。这群人中,有五六个人,抬着一个伤号。伤号不住的呻吟,好像伤的不轻。伤号的担架就放在车箱中间的通道上。列车开动了,朝前方行进。伤号忽然口中发出:“呀!呀!”的声音,那几个抬担架的男人见伤号发出声音,忙问:“怎么啦?怎么啦?”伤号只是呀呀的叫,急得那几个人什么似的,不知所措。这时候,康宁见小野秋子把自己保温杯子递给抬担架的人,让他们喂伤号水喝。那个人挥着手,意思说不要。她看着很着急的样子,她和邻座的旅客商量了一下,对换了一下座位,她就拿着杯子走到那个伤号的担架旁,把杯子对着伤号污血斑斑的嘴唇,杯子里的水,一点一滴的喂到伤号的嘴里。那伤号慢慢地恢复了安静,嘴里不再发出呀呀的声音,平静地安睡了。前边一个大站,几个抬担架的人,把伤号抬下了车箱,他们几人看着护送他们下车的她,伸出了大拇指。回到火车上,小野秋子脸色红彤彤的,在窗外远处高山的缺口处,涌泄过的夕辉中,她就像个圣洁的女神。
夕辉斜照在车窗玻璃上,就像一幅精美的版画,康宁心里想,这是他迄今为止,见过的一幅最最美丽的画,他这时候,真想抱着她,美美地亲她,吻她。他要向她说:“我要关爱你,呵护你一生一世!”
康宁坐在他和小野秋子生前常来的那座寺庙里。 这天,跟他们第一次来这座庙那天的气候差不多。他进来的时候,他也去佛前跪拜,上了三柱香。但他没有像她上次一样抽签,他不想抽签,没有了她,要签有什么用!签上的预言,会使他伤感,会使他伤情。他在那个水池边的大松树下坐下,陷入了深深的回忆里。康宁首先想到,和小野秋子第一次远离东京,到东京湾旅行的美好时光。就是那次,在火车上看见她一颗善良的心。她对那伤号之情,洋溢着她那一颗仁爱之心。从那以后,更加坚定了康宁爱小野秋子的信心。他相信,她是上苍赐给他的一件最美好的礼物。他要珍爱她,永不失去她!现在,康宁觉得这个世界使他沮丧,使他心灰意冷。他失去了小野秋子这个世界上他唯一最爱的姑娘。失去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亲人!他对这世界失去了一颗蓬勃向上的心。失去了她,而他认为他在这个世界上再继续下去的日子,是一种苟活,是一种犬儒的日子。虽生犹死,行尸走肉一般。自那次从杂货店老板那里知道小野秋子染病身亡的消息后,他就觉得自己的灵魂已经随她而去了。这里的康宁,是一个空壳子。他万念俱灰,他来这里仅只是一种身不由己的缅怀之旅。
康宁那一双无神的眼睛,无意识扫描着寺院进出的门。陡然,他眼前一亮,在门口出现她的身影,是那样俏肩束腰,穿着碎白花底的绿绸和服,和服下摆滚了一圈桔梗叶脉的花饰。腰间束着一条窄窄的紫色绸带。头上梳着高高的唐仕女的发髻,显着细腻凝脂长长的脖子。耳后发际处有长长细茸的毛发。他注目凝神,她进了辉煌的大雄宝殿。康宁趋步迎向她。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里遇到小野秋子,简直不敢想信自已的眼睛,死去的人能复活吗?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一个字:不。
他等在大殿门口,她出来了。就是她!
就是她,就是她!小野秋子迎着他的目光,向他快步走来。康宁迅速伸出了有力的手,一把拉住小野秋子,一齐走向寺院左首那片长着高大的樱树林,长长的动情的吻,在高大的樱树林下持续了好久好久。他们相拥坐在树下的石凳上,小野秋子姑娘向他述说着自已“死亡”的经过。
她和康宁热恋的爱情,被原在汉语训练班上那几个流氓学员知道了以后。他们天天去搔扰父亲的瓷器店,并扬言她如果跟那个中国学生订婚,一定杀死她,要放火烧了瓷器店。她父亲原来很支持他们的婚事。后来,在各方的压力下,彻底屈服了,不再支持女儿和康宁的婚事,立逼她不许和康宁来往。父亲劝女儿要为全家着想,不能毁了小野家族,并且为了全家人的安全,把她锁在了家中。后来,又让哥哥从北海道来到东京。哥哥听父亲说了她和一个中国留学生谈恋爱的事情,以及那群流氓搔扰的事。他本是胆小怕事的人,经过和父亲的一番商量,在当天夜里一块儿就离开了东京,坐上去北海道的火车。离开东京的时候,父亲又和她家对面杂货店老板栗原山子大叔商量了这件事。
她和父亲、哥哥一块回到北海道。父亲不让她出门,整天把她锁到屋里,让嫂嫂看管着。她对嫂嫂说了心里话,为了全家,她放弃了和康宁结婚的念头。但就是死,也要再见到康宁一次。小野秋子不得不以绝食相要挟,才使父亲让了步,让哥哥陪她来东京见上康宁一面。他们住在一家旅店,在这里等了三天了,哥哥催她走,她说今天康宁就要来了。果然,今天康宁就出现在她的面前。她事前给哥哥说:“康宁今天一定会来找她的!”仿佛是他们早有约定似的。说着,她指着站在他们不远处的一个人。康宁到了跟前,他定睛看了一会儿,是的,面前这小伙与秋子姑娘的父亲极其酷似,尤其那粗黑的眉毛、阔大的嘴巴,厚实的唇。
康宁和小野秋子姑娘这次在这里相见,是他们怎么也不会料到的,但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了这里。小野秋子姑娘在心里无数次地感谢上苍安排她和康宁最后一次相见。康宁在许多年后,每想起这件事,也是感谢上天的安排。康宁听了小野秋子姑娘如泣如诉的述说,他心情平静下来了。他真爱她,她是他唯一的爱。为了她,那怕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他不能为了和小野秋子的结合,而毁了她一家人,使她痛苦一生……决不做这样的事。
他们分手在洒着夕阳晚照余辉下的樱树林中。她把头深埋在康宁的怀里,抬起泪眼迷朦的眼睛,知道自己的泪水早已流尽了,流干了。她十分珍惜他们最后的时刻,能相聚一分是一分。她知道和他今生今世再也没有相聚的机会了。她真后悔自己,没有把自己的处女献给他,这是她终生的遗恨,抱恨终生呀!
康宁清醒而无奈地松开了小野秋子的腰际,他将永生铭记这难忘的一刻!她灼热的体温,快要把他烤枯了。从此以后,他们就要水天一方!将永远再也见不到他的小野秋子了。恐怕他们只有在梦中相见了!
小野秋子和她的哥哥消逝在远去的公共电车上。
康宁在三天三夜里,既没有吃,又没有喝,在床上睡过了这迷迷懵懵的七十二小时。那天,他是怎么回到学校的,自己也不知道。
懵懵懂懂,浑浑噩噩的康宁,在学校宿舍里度过了那个难捱的漫长冬天。小野秋子离他而去,却带走了他的灵魂,带去了他的全部心智,他只剩下了躯体和自己赖以存活的气息。那张床,是他的驽马,骑着它走向爱的苦海,茫茫无际的苦海……他看不见前边的光亮,四顾茫然,四面全是高高的峭壁,他在窄窄的缝隙里,没有灵魂的躯体,就如一具尸体,漂浮在死寂的海面。他呼唤着爱的归来,呼唤着青草的春天,呼唤着那宛如洛神的小野姑娘的归来。他怎么也舍却不下她对他的爱,那甘之如饴的情份,已经灌注进他的骨髓,他永生永世的难忘那刻骨铭心的爱!这年的冬天,一个留日的中国同学给他带来了一首歌,那同学对他唱道: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阳,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今霄别梦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康宁听完之后,已是泪流满面。他又让那同学为他连唱几遍。让那同学为他记下歌词,他颤抖着手,接住同学为他抄下的歌词,他呜呜咽咽,已是泣不成声。他问这歌词的作者是谁?那同学说是旅居日本的一位叫李叔同的中国诗人写的,他说:“这首词写的真好,我非常喜欢。”心想,这位诗人与他心灵相同,若不是这样,怎么能写出如此的美妙歌词。窗前,康宁在遐思那位引以为知己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