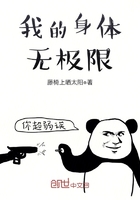无功剑正躺在伴生空间里,但黄裳还要用它唤醒余图南的失落人格,自然不能交给余家父子,因道:“很遗憾,令嫒佩剑遗失在战场上,了无踪影。”
余父盯着他:“不会是你私藏了吧?”
“爹!”余振北叫道。
余父道:“振北,图南那柄剑你也见过,削铁如泥,合该你用,为你姐姐报仇哇!”
余振北道:“顾北的虎形拳使的那么好,不会骗我们的!”
真是个耿直少年,黄裳汗颜,也有些惭愧,却无法说出实话,只道:“伯父不信我也无法。不过你们还是暂且搬出去避下风头的好。万一有事,尽管找我。”
黄裳留下地址,回到家中,却见夭夭正和刘茵对弈,凑前一看,执黑的夭夭已占了地和势,连成一气,又厚又实,将白子分割成几块,支离破碎,不成样子。刘茵长考未果,弃子认输,摇头笑道:“夭夭真厉害。这一步你是怎么想到下这里的?”
夭夭咬着指头,小脸上尽是茫然:“不知道唉。我只是觉得下在那里比较好。”
“跟着感觉走么?”刘茵叹息一声,感慨道:“天赋过人哪!小夭夭,想上学吗?”
黄裳暗暗摇头,夭夭下棋哪是什么跟着感觉走,二人灵魂纠缠,心灵互通,他会的技能夭夭也会。黄裳前世和姐姐黄离下了近十年围棋,在网络上亦是大杀四方的存在,夭夭和他水平一般无二,刘茵水准虽不错,却不是对手。
刘茵想拐夭夭入学,正合夭夭盘算,甜甜笑道:“想!”
顾西上前挑战,也被杀的丢盔弃甲,拉黄裳入局失败,渐渐夜深,诸人安歇。幸好这院子是顾父在时所置,为求个子息繁多的兆头,有几间空房。黄裳一夜未睡,胎息了两个时辰,便一直在琢磨如何引动生命盾和善恶矛中所潜藏的庞大能量。
他自在喜马拉雅山下晋升二阶后,十滴雷霆源血贯通一气,彼此共鸣,反哺肉身,时刻催化情绪生机,凝练进度大增,现下已有十三滴。黄裳暗忖这样才对,若一直像一阶时那样艰难,没人能凝练一万源血成为黄昏骑士,遑论全身化源的黄昏上位。
初冬时节,黑夜渐长而白日渐短,清晨时天仍是黑的,为安全计,兄妹让吴妈暂时回家,黄裳起床做了一桌早餐,粥香弥漫,引得一大一少一小三女起来,吃的不住叫好。
饭罢,刘茵和顾西自要去学校,夭夭要入学考,也坐上顾西自行车后座跟着去了。
黄裳也跨上自行车,骑出城外,向着一座山行去。
孙家道场不在城内,而是坐落城北一座山上。那山原来有名,自孙禄堂到后,山中常起雷音,渐渐百姓便管它叫“雷音山”。
黄裳此来,一是想向孙禄堂表示谢意,二是与孙存周商量余振北之事。
山上多松柏,黄裳停了车,沿路上山,这条路宽阔笔直,直通道场门前,通报名姓,孙存周很快迎入,一路上已有许多道场弟子在晨练,一拳一脚,一板一眼,颇见功力,甚是用功。
二人坐定,礼毕茶罢,黄裳送出昨夜顾西找出来的谢礼,顾父收藏的一方前朝古砚,雅致不落俗套,孙存周哈哈一笑收了,道:“大同报之事我已查明,那篇报道是杨怀修请人所作,照片也是他提供的。”
“杨怀修?”
“杨公露蝉之子,杨氏兄弟之父,袭爵靖远候。陕西那起袭击铁路事件我还没查清楚,但我托人查了候府一干干事的动向,其中一人前几日刚巧去了陕西,想来和他脱不干系。”
黄裳不解:“动机呢?这样一位大人物,总不是因为儿子输了一架就如此大动干弋?”
孙存周似有些不好意思,干咳一声道:“说起来这源头还在盛师兄身上。家父在和几位师兄谈话时说起要再收一名弟子,只是不要仙士。盛师兄无意透露出去,报纸理解成武徒,但‘不要仙士’这四个字传到靖远候那里,想必多出了你们三个骑士。”
“杨怀修从儿子那儿知道我的身手,担心两个儿子不是对手,便设法坏我名声,如此一来,天下第一手自然不能收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作弟子……”
黄裳颇有些难以置信,道:“因为这样的猜测就煽动一村村民袭击铁路,不顾那么多人的死活?”
孙存周淡淡道:“杨怀修承袭候位,权贵已久,非往日武人,为子孙计,只怕不会顾忌太多。”
黄裳摇摇头,心中涌起一丝怒火:“我欲状告杨府煽民闹事,污蔑旁人,如何?”
孙存周喟然道:“怕是不成,杨休修甚得圣宠,家父早年也曾受杨公指点一二,我也不好为顾北出头。”
黄裳沉吟片刻,又道:“大同报呢?”
孙存周瞧着他,似有些惭愧:“大同报背后是翁同龢,两代帝师,无疑以卵击石。”
两代帝师翁同龢,昨日听顾西长论京中人物时曾听过,乃同治、光绪两代皇帝之师,素有文名,德高望重,几谓文坛领袖。黄裳若状告大同报,只怕会先被一堆士子拿唾沫淹死,况且看孙存周模样,对于插手此事似有难言之隐,黄裳无权无人,取不到证据,如何状告?
京中权贵行事,竟至于此。
孙存周长叹一声道:“顾北勿怪,敝家如今处境微妙,不宜多涉朝中之事。我已请一位朋友捉笔写文,亲自作证,为你洗涮污名。”
“你竟然到了这一步,清帝不会放过你的!”
黄裳一怔,忆起蒙哥马利公爵的这句话,一时恍然,拱手谢过。杨家乃候府,又有杨露蝉留下的庞大人情,想要凭此扳倒杨家只是妄想,但他下定决心,决不会让对方算计得逞,因问道:“孙前辈打算如何选择弟子?”
孙存周道:“家父只提过一句,并未透露具体想法。但想来和以往差不多,各位故友推荐一些优良子弟,加上武徒自己报名,各人比过一场,视其人品、心性、武功、潜力,由家父自行决定,却不一定是最终的胜出者。大师兄庄吉当年比试只得了第五名,家父仍选了他。”
黄裳暗忖良久,提起余振北之事,有些人盯上了余图南的剑谱,孙存周皱眉道:“竟有这等事?那伏虎帮我也略知一二,是李景林在后面主持,难道是他?”
想了一会,他抬起头道:“我听说当年他也曾挑战过余图南,传闻是败了。李景林绰号武当一剑,于剑法极是自傲,想来不大甘心……”
黄裳问道:“李景林武功如何?”
孙存周慎重道:“我等五人并未直接交过手,依我估计,李景林当不在我之下。”
“不在存周之下么?”
黄裳长吁一口气,拱手道:“烦劳存周兄放出消息,就说顾北尽得余图南剑法真传。”
他本欲将此事揽到自己身上,岂料孙存周一听之下,面色大变霍然站起失声道:“此言当真?”
黄裳点头:“何以如此?”
“顾北稍待。”孙存周以从未有过的慎重语气交待一句,匆匆出屋。少倾返回,肃容道:“家父有请。”
黄裳起身随他出去,道:“怎么,余君剑法有什么要紧之处?”
孙存周道:“个中缘由我也不甚清楚,似乎关系到家父一件重大往事。”
从后门出了道场,二人沿着山路向上,黄裳本拟以孙禄堂天下第一的身份地位,无敌气魄,定然住在顶峰,一览众山小,然而在接近山顶时,出现一座茅屋,孙存周示意他进去,自己守在外面。
黄裳推门而进,屋内空空荡荡,别无它物,只一蒲团,跌坐一人,面目平和,睁眼瞧来,黄裳俯身下揖,恭恭敬敬道:“晚辈顾北,拜见前辈。”
孙禄堂仔细打量他,微微点头,拈须笑道:“不错,比之上次见面,小友又进一步。”
黄裳诚恳道:“还要多谢前辈传符并搭救之恩。”
孙禄堂道:“我亦有私心在此,小友可愿听一个故事?”
黄裳道:“晚辈洗耳恭听。”
孙禄堂抬首望天,目光悠然,似是穿透茅屋,望见外面广袤山河,无垠睛空,道:“有一个年轻人,自幼酷爱武功,多年苦练,加之一点天份机遇,侥幸成为仙士,又蒙多位前辈指点提携,终于练出一点还算说的过去的本领。忽忽多年,外敌入侵,这人立下些许功劳,江湖上朋友们抬爱,送了一个口气很大的浑号,年轻人此时已不再年轻,气却还是很盛,也膨涨的很,竟是收了,自此指点江山,以为天下无敌。有一天这人忽然心血来潮,外出游玩,遇到位老人在教一个女娃娃武功,这人看那女娃天资很好,偏偏那老人教的招式口气挺大,甚么‘冲盈抱虚’、‘色空双解’、‘三宝如意’、‘三三归元’、‘乾坤衰劫’、‘一线生机’,听起来唬人的很,使起来却全然不成样子,便要抢个弟子。三言两语不和,两个人动起手来,那人竟是一败涂地,于是心灰意冷,闭目等死。岂料那老人说:‘你这年轻人还有点看头,比这世上其他人强一些,也就差那么一两步,可惜,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