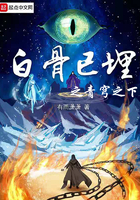天擦黑的时候,两人从张府侧门走出来。
张府侧门紧挨着茅厕。粪车从侧门进府,不必走太远就到目的地。无论是对粪车还是对张府的空气,都有好处。许是常年走粪车,又挨着茅厕的缘故,这地方常年有股骚臭,没人愿意来。
这两人,一人扛着锄头,是王三,一人扛着麻袋,是张大。麻袋里不知装着什么东西,看起来挺沉的。他们显然不是掏粪的,而是要去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在他们身后,还跟着一人,这人看起来瘦弱,抄着手,正跟两人嘀嘀咕咕的说些什么。抄着手的人,正是房管事的那个小厮。
小厮在房管事前是小厮,在他们面前那就是一尊大神。两人不敢怠慢,恭恭敬敬得听着吩咐。麻袋里的物事不能让人看见,必须去城北达摩岭连着麻袋带里面物事一起埋起来,一定要挖地三尺不能浅浅得埋了,事成之后赏他们纹银一百两,事无巨细一一记在心里。
突然听到赏银一百两,两人差点要当场欢呼。一百两可不是小数目,足够他们一年的奢侈生活了。即便是两个人一百两银子,五十两也足足够用。
他们拍胸脯保证,一定将事情办好,不辜负这一百两银子。
小厮满意点头,从袖子里掏出两块令牌来,递给两人一人一块,嘱咐事成之后便可以拿着令牌去账房支取银子了。
两人听了连忙接过,都道是行善积德才得了这么个好活,可怜他的几个兄弟,还说这私活危险,动不动就得丢掉性命。什么丢掉性命?不过是听别人瞎说,瞎说的话哪能算数?要是兄弟们知道能得一百两银子,肯定都争着来,毕竟谁会跟银子过不去?
两人兴奋的浑身冒汗,力气倍增,拎着麻袋扛着锄头出北城门一路往北,沿着官道走了大约一刻钟时间,抬头便能看到路旁多出一道山岭。这就是达摩岭。
山岭郁郁葱葱,却几乎没人会去爬,只除非一年中有限的几个日子。因这山岭是城中所有人的埋骨之地。埋骨之地大多是风水宝地,达摩岭也不例外。达摩岭中风水最好的几个地方,被张家占据,做为张家祖地。剩下的旮旯角落,才是其他家平分。
城中所有人家的祖宗都埋在这里,日积月累之下,达摩岭虽然依旧郁郁葱葱,却平添了几分阴冷。这分阴冷在白天还不明显,但在夜晚,林间吹起凉风,配合着摇曳的淡蓝色鬼火,足以吓破人胆。
两人背着麻袋,扛着锄头,手牵着手,不敢说一句话,不敢闭一下眼。生怕说话动静引起恶鬼注意,生怕闭一下眼,睁开后前面有颗带血的人头。
山风吹动树枝,发出的声音好像鬼哭,那一根根摇摆不定的树枝,好像背后有什么东西操纵。他觉得,每颗树后面好像都有东西,每团草丛里都有对瞪视的眼睛。
他们战战兢兢,浑身发冷,好像光着屁股在雪地上打滚。他们想着算啦,就把麻袋往地上一扔回去得了,反正这地方也没人会来。
两人对视一眼,都看出对方的想法和恐惧,立刻便下了决心,扔下麻袋,撒丫子往回跑。这鬼地方他们是再也不想来了。
但没等他们有所行动,张大的突然一声惨叫,手一松,麻袋掉地上。惨叫在夜晚的山岭里传出老远,惊醒了打盹的老狼。老狼抖擞精神,对天一声嚎叫。嚎叫,让这夜显得更诡秘了。
“怎么了!怎么了!你叫什么!”两人手牵着手,王三分明感觉那一刹那,张大的手一下子变得冰凉。
张大指着地上的麻袋,手哆嗦得像得了帕金森:“他……他在动。”
麻袋里装着死人,虽然上头没明说,但三更半夜得去达摩岭,加之麻袋的分量触感,猜也能猜到几分。
猜到了,但他们默契地不提,只当不知道。荒山野岭,遍地坟冢的地方,背着个死人已经够吓人的了,若是再去谈论,没病也得吓出病来。
以为不谈论就没事了,可那死人好像生怕别人忘了他似的,他竟然动了!黑森森的树林里,眼前一座座馒头似的坟冢若隐若现,间或还有些怪异的叫声,这情形简直是恐怖片必备。
这时候,身后的麻袋突然动了。若放在白天,那肯定是麻袋里的人还有气,必然要打开看看还能不能救。可现在,黑灯瞎火的坟地里,两人心里嘴里只有三个字在不停的回荡: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
张大胆小,一路背着麻袋,一路就犯低估。好不容易挨到达摩岭,眼看着挖坑埋了就好了,麻袋终于出事了。
一路上想着会不会出事,现在真出事了,他终于放松了,烂泥一般摊在地上,说什么也起不来。得亏出门时候放水了,一路走着出汗,才没有太丢人。
王三胆大,总算有些理智,可也没打开麻袋看看的想法。他要活着,待会自然会自己爬出来,麻袋又没封口。他若死的,现在是诈尸,打开要看,命可就丢了。
现在要做的就是离开这片是非之地,他一手拿着锄头,一手扛起腿软的张大,认准回去的路,撒丫子狂奔。跑起来,总觉得身后有个眼睛在看着,冷汗就下来了,脚下使劲,跑得更快了。
跑了不知多久停下来,两人心有余悸。虽然事做的不够完满,但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回去之后,便可以拿着令牌去领银子了。一百两啊,够一年不愁吃喝了。
手拿着令牌在眼前摸索着。令牌质地坚硬,摸起来是块铁。这可是值一百两银子的铁,最贵的铁了。一边摸索,他们便想着怎么花这一百两。该给地里买头牛,给娃买几件新衣裳。婆娘老嚷嚷着要做些小买卖,以前是没钱,总是拒绝。现在既然有钱了,就做。
这么想着,摸索的时间就有些长了。突然觉得手疼,低头一看,见令牌融化,正迅速地渗透进肉里。随着渗透,疼痛地感觉越来越明显。直到令牌全部融入进去,疼痛已让他们恨不得将手剁去才好。
怎么回事!他们大惊大叫,让静谧的山林显得更加恐怖了。他们想说话,想问问对方到底怎么了。但张口只能啊啊的乱叫,嗓子被封住了。他们想逃跑,只能逃出去几步,便觉得腿脚不灵活了。
惨叫持续了很久,从高亢渐渐的沙哑,渐渐的低到若不耳闻。
两人离开不久,树林中走出个人来,头戴月白色文生公子巾,身穿月白色文生公子服,正是张明远。
他看了眼狂奔得下人,心说幸好他来跟着,否则这俩下人非得坏了大事不可。他没打算上去追究。他们活不过明天早晨,追击死人的责任实在是多此一举。
麻袋突然又动了一下。张明远皱眉,这畜生果然是******种,生命力很是顽强。他从袖中拿出一把短剑。
短剑无鞘,剑身即便在黑夜里也有淡淡的光芒,显然是宝兵。张明远掂量了掂量,比划了比划,觉得还行,长度足够,分量也足够,便一手拿着短剑,一手去掀麻袋。
麻袋掀开,露出里面的张泓来。
黑暗中瞧不出张泓的面色,但隐隐地能看到他正忍受着痛苦。死人脸上的痛苦,和活人忍受的痛苦,表情是不一样的。张明远虽是书生打扮,可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死人也没少见。
只一眼他便确定,张泓还活着。
匕首划开张泓衣服,露出胸膛来。张明远拿手丈量了一下,圈定了一个点。从这个点往下半个巴掌的距离,就是张弘的心脏。
被打的皮开肉绽不死,他不信刺破心脏也不会死。传说心脏是灵魂居所。心脏破了,灵魂无依靠,自然死亡。自古修行再高深,除非达到魂入元阳的地步,否则都无法避免。
他不信,张弘就能活着。
选定了地方,张明远反手握短剑,一使劲捅了进去。平常杀人大多用术法,直接动兵器杀人不多,杀的怎么说也是自个儿子,张明远心中真有些微妙。
心脏破碎,血像喷泉一样出来。张明远待了一会儿,听心脏没了跳动,满意点点头,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