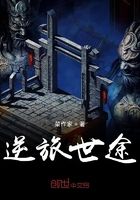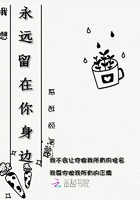这套小说文丛中展示了中国年轻作家的作品,异常尖锐地呈现了当下中国写作的可能和困难。它显示千禧时刻的中国文学仍然存在的敏感性和某种衰退的征兆。
“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已经是文学界谈论已久的话题。其实以出生的年代来界定文学潮流往往没有太大的意义,也未必具有概括力。但这里入选的“七十年代”作家的写作风格和内容的确往往非常一致。他们的写作接近于八十年代的刘索拉,九十年代初期的陈染、林白等人所建立的自我倾诉、强调个人感觉的“谱系”。他们似乎都有所谓“个人写作”的文脉。
这些作品几乎都聚焦于当下的全球化与市场化时代的城市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经验,往往表现出对于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非常有趣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这些小说都表现出对于丰裕生活的渴望,表现出对于“新经济”下的那种突如其来的成功的渴望。这些作品往往描写年轻知识女性遇到时髦的“新经济”的成功者,而且这些小说几乎丝毫不掩饰对于“成功”的欲望。另一方面,这些小说又表现了某种另类的反叛性,表现出对于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不满,这种不满非常接近当年的“垮掉的一代”对于社会的不满。小说里的人物往往希望过一种越轨的生活,希望超脱中产阶级的伦理,寻找某种超越的可能。这种矛盾的处境正好反映了中国当下的青年的中产阶级想像的极度的矛盾性。一方面渴望个人力争上游的成功,另一方面希望保持一种激进的想像,这种矛盾正是中国全球化与市场化的急剧发展的结果。他们往往要遗忘当下的现实中的另一面,也试图遗忘历史的记忆。但这里展现了一种困境,一种更为深入的矛盾。这里有一些看不见的人和空间与时间在默默地涌现。它们是最需要和最渴望被压抑和遗忘的东西,但又如此无情地时刻涌现在本文之中。“革命”和“底层”,如同幽灵,又如同电脑本文中的乱码从本文的断裂和缝隙之处“浮现”出来。使得这些好像仅仅有关身体和个人性的本文有了某种新的意义。
这种“幽灵”和“乱码”的经常出现,可以使我们发现新的启示。遗忘的不可能通过这种反遗忘的叙述“漏”了出来。“幽灵”的无处不在如同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所表现的一样,它们还有再出发的可能,只是必须找到在新的语境中的表达的点和连接的新的思路和新的面向。七十年代作家写作的矛盾性和能产性也似乎正在于此。而这种遗忘、反遗忘的纠葛和复杂矛盾也说明这种写作具有某种积极的作用和力量。这其实也说明刘索拉式的反叛风格与“七十年代出生”作家间的断裂。七十年代作家乃是这个全球化和市场化时代文化的最为戏剧化的表征,他们的写作投射了这个时代年轻人在困难中的可能和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