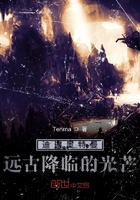“哦,你是担心这个啊!”叶保说,“那我不知道。我不去木阁楼就是了。”“你这样答应我,我就放心了。”谭蕾听叶保这么说,心头那个结就放松了,顾虑似乎也减轻了,脸上露出了欣喜的表情。她理了理原本被扎成一溜的头发——原本披开的波浪形卷发,因为今晚来时被套在风衣帽里,被她用一条绸丝带扎成一堆,聚拢到脑后。这样她整个白皙的脸容就呈现在他的眼前了。她的双颊红润,透出一种健康女性特有的红嫣血色。那戴在她玲珑剔透双耳上的一对坠吊的金耳环,在柔和的灯下熠熠生辉,那能勾人心魄的眼睛,双眼皮上下眨动着。叶保还发现她的双眼皮不是那种简单的缺乏内涵的双眼皮,在她的双眼皮上下之间还分布着一些细小的线条,形成那种深邃的、内涵幽深的细眼皮,是那种看了令人心颤的双眼皮中的多眼皮。那多眼皮是黛青色的,黑眼圈你仔细看实际上也是黛青色的,是任何一位高超的化妆师所无法描绘的黛青色,因为这是浑然天成的。叶保平生第一次见过这么美丽动人的多眼皮和这种自然天工的黛青色,在他的初恋情人也属于美女范畴的范艳彬那儿也没见过。昨天他第一眼看见她,也许就是被她这双勾人的眼睛所迷住。但那只是远距离地看,并没真正发现她的眼睛有这么美,而现在是这么近距离,让他细细地看,他才发现她这双独特的、与众不同的眼睛。她的多眼皮每眨动一下,都会使他心跳一下,他不由自主地对她赞美道:“你的眼睛长得如此的美妙动人。”她对他的赞美感到羞怯,她低下头轻声地说:“我已三十八了,都快是老太婆了,还能像你说的会美妙动人?”“女人的美不是用年龄来界定的。”叶保说,“十八岁年轻的女人也许是个丑八怪,而八十岁的老太婆也许还是个美女。美女是天生的,也是终生的,不因为美女的年岁的多与少,年轻或年老就失去她美女的天姿,美始终都伴随着美女的一生。”谭蕾认真地听着,并不感到叶保对她的赞美是在凭空敷衍她。其实,每一个漂亮的女人都清楚自己的美。她们从众多异性的目光的注视、追逐中读懂和感受到自己的美。她从经常被男人骚扰的经历中,确信自己是个美貌的女人。谭蕾懂得自己,也懂得男人,懂得男人在像她这样美貌的女人面前常常会出现的那种怪异的、令人匪夷所思的神经质的举止动作,以及他们的正人君子与好色之相融汇在一起的眼神和心跳。她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己还年轻的俊俏的男人,看着他因为自己的美貌而按捺不住自我而抖动着的嘴唇,她问:“叶保,你今年是多大?”
“三十六。”“那你可比我还小两岁。”谭蕾想缓和下他激动的神态,说,“这么说,我应该做你的姐姐了。”“不,我不要你做我的姐姐。”叶保伸手捂住谭蕾的口说,“我要你做我的情人。”“这合适吗?”谭蕾轻轻回避叶保的手说,“哪有女人比男人大的情人。”“这世上女人年龄比男人大的情人多的是。”叶保说,“俗话不是说,‘女大三,抱金砖’”,“但那毕竟是俗语,现实生活中,大都是男比女大。”“我现在就是要把这种习惯倒过来。”叶保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上前搂住躲闪着他的手的谭蕾,说,“我已无法控制住我对你的爱。”“不行。”她再次躲过叶保的手。“为什么?”“你有老婆、儿女。你这样做不觉得对不起他们。”谭蕾说。“我是有老婆儿女。但实不相瞒,我并不爱我的妻子。春节前我从桃阳报到回去,我的妻子继续跟我吵,说是我一意孤行想多生一个小孩,毁了她的后半生,要和我离婚,弄得我整个春节都生活在阴风惨雨里,所以,我连元宵都没过就回桃阳了。”“真的吗?”谭蕾不解地说。“其实,我和妻子的婚姻,本来就是我父亲一手撮合成的。我们虽说都受过中等文化教育,却不是自由恋爱,没有多少的感情基础。一遇到家庭重大的变故,根本就经受不住风雨的考验。这真应了那句‘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可以说,我和她的结合本就是一个错误。我和她结婚这么些年,我从没在她身上感受到爱与被爱,和家庭的幸福。也正因为这样,我才会像她说的一意孤行要她为我再生一个孩子。当然我这种做法,其实是变相地把她当成我的造人机器。”
“但你们毕竟有了两个小孩,你们又是结发夫妻。”谭蕾说,“你也许是太认真,太追求婚姻生活的完美。要知道,这世界有多少家庭、多少无爱的夫妇,都是这样撮合着过啊!”
“可我心有不甘。”叶保感慨地说,“我知道,这世间,爱对一个人的一生是多么的重要。一个人如果生活在无爱里,一生是多么的可怜和可悲。即使这个人活着也像行尸走肉跟死去已经没有什么两样。”
随之,叶保毫不忌讳地向谭蕾述说起自己在省财校与女教师范艳彬的初恋,和妻子结婚十二年无爱的婚姻生活,以及怎么在查税遭到打击报复,从一个县局股长下到桃阳的遭遇。谭蕾静静地听着,她虽然很感震惊和错愕,但一直没有插话,就像一位熟悉多年的老朋友在聆听着他的这些个人经历。人实在是很怪的生物,有的人相处几十年,或者一辈子,都不会向相伴者讲述那些绝对属于个人隐私的情感故事;而有的人却只在一面之交,或一次邂逅,或一段旅程,就能像老朋友那样敞开心扉,向对方倾述过去的情感经历和人生际遇。叶保此时的心境就是属于后者。他说完后对谭蕾说,“这些话,特别是与女教师的情感经历,我都没对我的妻子言语过。不是我想隐瞒什么,或者畏惧什么,而是因为俩人没有感情,我就没有向她叙说的欲望。而今天和你在一起,我有种向你倾吐的欲望。我似乎感到我要让你了解我的过去和现在。”
谭蕾为他的坦诚、率真而感动。她说,“今晚你约我来,我是有顾忌的。虽然我已在昨天从你的谈话中和你骑摩托受伤中,感到你是个心地善良的男人,但是,现在是花花世界,许多男人都会用假象,用花言巧语哄骗女人。于是,我有过怀疑,你会不会也是一个花花公子?刚才,你在我面前讲述了这些个人经历,我才打消了这种顾虑和怀疑。”
“你能这样相信我,我觉得很欣慰。”叶保说时,眼眸亮了一下,谭蕾从他的眸子里发现有晶莹的泪珠在闪动。那是真诚的泪珠,是被人理解感动后的泪珠。这真诚的泪珠敲击着她的脑神经和心灵,叫她无法拒绝。倏地,她伸出双手温情地抱过他的头,一串温热的泪水夺眶而出,淌落在他的脸颊,与他的泪珠儿融汇在一起。她用舌头舔了舔,分辨不出是他的还是自己的,但是酸楚的和咸涩的,又包含着有他雄性的气味。这时,叶保一个激灵,吻住了她的双唇。潭蕃震颤了一下身子,人便无力地依偎在他的怀里,驯服地接受着他那像雨点般的热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