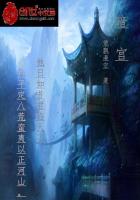兴平二年(公元一九五年),长安。
窗外的雪花纷纷飘落,屋子里虽然点着火炉,却仍然能感觉到寒气从门窗的缝隙中吹进来。
夕嫣将大氅披在了坐在身边拿着拨浪鼓的少年身上,满眼慈爱地看着他。少年虽然已经二十来岁,但表情举止看上去却与四五岁的孩童无异。
这是夕嫣和李傕的儿子,名叫李式。当年夕嫣怀他的时候,没有太过节制,仍每天配制毒药,结果影响到了胎儿。他一出生,便是个傻子。或许正因为这样,夕嫣才更加疼爱他。
一丝寒风吹进来,李式打了个冷颤,夕嫣赶忙将他搂进怀里,低头用手抚摸着他的额头。
李傕就站在屋外,透过门缝看着里面的母子。但他没有出声,也没有进来,因为每当看见夕嫣这样的时候,他都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恨之心。
为什么老天要这样对他,为什么偏偏自己的儿子是个傻子,女儿又远在他方。
李傕也不过才三十多岁,却已经银丝满鬓了。多年的操劳,让他也不堪重负,但是为了对夕嫣的承诺,他也只能坚持着。
……
那是十七年前,年少的李傕第一次遇到想要跳崖自杀的夕嫣。
“姑娘,为何轻生?”李傕的性格天生沉闷,他永远都不会做出冲上去救下夕嫣这样的事。
夕嫣那时也不过十六岁,一个十六岁的少女正站在崖边一边哭一边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忽然旁边有个人冰冷地和自己说话,任谁都会奇怪。
“与你何干!”夕嫣擦了擦泪水,嗔问道。
“哦,那在下先告辞了。”李傕说完便要转身离开。
“站住!你这人好生奇怪!问我轻生的理由,又这般冷漠,你到底想要如何?”夕嫣抄起一块石头砸了过来。
李傕并没有躲闪,任由石头砸在自己的头上。
鲜血顺着额头留下,但李傕并没有去擦,而是平静地问夕嫣:“你既然仍在乎他人的感受,又为何要寻短见。”
“我……我……我被负心之人抛弃了。”说着,夕嫣蹲在地上大哭起来。
而这,恰恰是当时李傕最致命的软肋。
年少的他,能面不改色地杀掉一个成年人,却害怕把女孩子弄哭。
“那……那个……你……”李傕一边手足无措地左顾右盼,一边结结巴巴地想去劝她。
“你什么你!不会哄人么?”夕嫣抬起头,用一双哭得通红的眼睛瞪着李傕,把他吓了一跳。
“那……那你跟着我吧,我不是负心人。”李傕心虚地说。
“啊?”夕嫣睁圆了眼睛看着他。
李傕尴尬地抓抓头,转身冲着别处,不再看他。
“噗哧”一声,夕嫣笑了出来,“就你?你能给我什么?”
“我……我……我将来一定会成为大将军,让你富贵终生!”李傕紧张地憋红了脸。
……
很多事就是这么奇妙,在那个特殊的时间点上,夕嫣遇到了真心对自己好的人。而李傕,为了兑现和夕嫣的诺言,这些年一直努力坚持着。
而仅仅过了一年时间,李式就出生了。当时还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不正常,而且,夕嫣那时正怀着凌鸳。
可是,在她分娩之后,便有个人找到了她。
原来,她的师傅已经与夜锋达成合作,命她和来人一同前去加入。而来找她的人,便是日后夜锋北方总堂五贤老座下夜帅,她的师姐——百里嫙。
在她的百般央求之下,才同意带着凌鸳同往,但必须对女儿的身份保密。
就这样,连与李傕道别的机会都没有,夕嫣便不情愿地成了夜锋的夜帅。
更让她无法忍受的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奇妙,当初抛弃自己的韩渊也在这。而当年韩渊移情别恋的对象——玉琉,竟然也是夜帅!
就这样,为了完成师傅的命令,也为了保护凌鸳长大,夕嫣在夜锋度过了尴尬而又孤独的十年。
直到那一天,她收到了李傕派人送来的信。
凌鸳已经长大,无须她多操心了。于是,她从安邑分堂离开了,留下中了“灼毒”的爱徒龙悒。
当李傕和夕嫣再见面时,两人都已人到中年了。那是唯一一次,李傕的部下看见他们的将军落泪了。
独自带着一个先天弱智的孩子,还要去四处征战,将李傕原本帅气的脸折磨地满是沧桑;而夕嫣,也因为这十年的操劳而变得冷血了。
但是当他们拥抱到一起时,似乎时间又回到了相遇的那天。
如今,李傕经过近二十年的时间,终于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让夕嫣贵不可言。
————————————————
幽州,渔阳郡,潞河北岸。
阎柔在鲜于辅、鲜于银、齐周的推举下成为了乌丸司马,阎柔招集鲜卑、乌丸等兵马,组成了数万人的汉、胡兵马。
此时,这些兵马全部冲了出去,对公孙瓒任命的渔阳太守邹丹兵马,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夹杂着胡人的兵马,战斗力总是很强悍。战争没有任何悬念地迅速结束了。
鲜于辅走到阎柔的身边,对他说道:“听说,他的人也快到了,是么?”
阎柔点了点头。
三日前,他已经收到了密信,袁绍的大将麴义已经奉命率军前来助战。所有人都明白,这不过是袁绍的小把戏,卖个人情得点好处。
阎柔忽然转头,严肃地看着鲜于辅,说道:“还得烦劳你去下。”
“去哪?”
“迎接刘虞之子刘和与麴义的兵马。”
“刘和?”鲜于辅诧异道。
“他在这里的声望极高,我们理应与其合作。”
“也罢。既如此,我便起行,你且在此扎营歇息,等待乌桓峭王的到来。”
二人正说话间,有士兵报说,已抓获邹丹。
不一会儿,邹丹便被带了上来。
“如今公孙瓒已变得生性残暴,阁下为何还要助他?”阎柔笑问。
“一日为主公,则永世为主公。速速杀我,邹丹绝不肯降。”邹丹朝阎柔大叫。
鲜于辅心中不忍,便对阎柔说:“如此忠义之人,实在不应杀害,不如暂且囚禁,待日后……”
“杀了吧。”阎柔没有等他说完,便对押着邹丹的士兵说道。
“你!”鲜于辅怒视着阎柔,心中满是惊讶,难道他也变得如公孙瓒般了么?
“正如你所说,他是忠义之人,难道我们不该成全他的美名么?难道你要后世史书上写他如何在牢狱中受凌辱,如何悲惨地死去才甘心么!”阎柔直视着鲜于辅质问道。
“唉!”鲜于辅长叹了一声。确实,一个忠义之人,如果不能死得其所,反倒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将邹丹斩首示众!传令众将士,邹丹的眷属一概无罪,供给如旧,有敢惊扰者,杀无赦!”阎柔红着眼圈看着面前的邹丹大声说道。
“多谢了。”邹丹冲他微微一笑,坦然受戮。
鲜血浸透了辕门外的土地,又一个重义之人离开了。
辕门内,以阎柔和鲜于辅为首的一众将士,全都拱手相送。
能得到敌人的尊敬,便是为将者最高的境界了吧……
……
将邹丹下葬之后,鲜于辅便点了五百人马,准备动身去接刘和。却不想袁绍的信使先到了,信中说:麴义和刘和已经在鲍丘附近扎下营寨,只等他们前去汇合。
阎柔和鲜于辅看完信后,临时决定由鲜于银和齐周留下部分人马等待乌桓峭王,而他们二人则率大军直接去与麴义汇合。
由于要带着大量的辎重,他们的速度并不快,第二天黄昏才到。
简单的寒暄之后,他们终于了解了此处的情况。
公孙瓒虽然如今已然残暴成性,但其军事才华却并没有消失。就在麴义他们刚刚进入幽州的时候,公孙瓒就已经开始部署了。
他将身边的全部兵力都放在了幽州与冀州交界处的要道,麴义不想中了他的埋伏,所以小心地从幽、冀边境偷偷绕了过来,成功避开了公孙瓒为他设下的层层伏击。
公孙瓒得知后,立刻收缩兵力追赶,终于在鲍丘与麴义遭遇了。
阎柔等人收到信时,他已经和公孙瓒这么僵持了半月了,只是谁都不想冒然进攻。
公孙瓒怕的是兵力收缩之后,袁绍会再偷偷派人马过来幽州。而麴义担心的是,辽西郡会有援兵过来。
最主要的是,双方都相信自己的粮草足以将对方耗走。
毕竟战争终究是要死人的,而保存实力,是在乱世中生存的第一课。
可是当阎柔和鲜于辅率军赶到时,公孙瓒便知道,只能战了。
于是,就在阎柔他们到达的同一天夜里,幽州最强轻骑兵,威震塞外的骑射霸主——白马义从,又一次出击了。
只是,他不曾料想,这支令他傲视群雄的神兵,却败得一塌糊涂。
面对着麴义的“先登死士”,白马义从速度上的优势完全被忽略了。就如同当年的界桥之战一样,这匹敏捷的“骏马”再一次输给了甲壳坚硬的“乌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