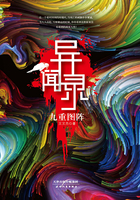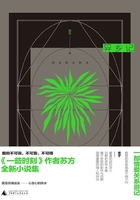现在,正当一切都似乎不会再有变化的时候,他终于要回到英国来统治他的人民了,斯图亚特察理从此不是亡国察理了。
十一年前,一小队极端派清教徒杀死了他的父亲,那由数千目击者发出来的悲恸之声立即震荡了整个欧陆。这一桩弥天大罪是会永远沉重地压在英国人心上的。那时国王弑王的长子流亡在法国,直到他的随从牧师跪下来称他“陛下”,这才知道他为营救父王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他转身,走进卧室去独自哀悼。他知道自己成了一个无国之王无民之主了。
于是在英国,科隆韦尔的暴力脚跟上了英国人民的颈脖。现在,做了贵族中的一员就是犯罪了,曾经效忠王室的通常要被没收土地和钱钞。那些跟随察理二世逃亡在外的,都宁可待在外国等着形势好转才回来。一种极端严肃的教规控制了全国,凡属英国人本质上所有的一切都被压制了,如诙谐的谈笑、游戏、宴会等等的狂欢,饮酒、跳舞、赌博、调情等等的享乐,一律都在禁止之列了。五月节跳舞的花柱都被砍伐了,戏院都被封闭了。谨慎的女人都收藏起她们那些绸缎丝绒、红红绿绿的漂亮衣裳,搁起她们的面罩、扇子、卷发和假发,遮盖了低开领子的颈脖,嘴唇上不敢再抹胭脂,面颊上不敢再点黑痣,就为避免嫌疑,被认为是王党的同情者,甚至日常用的家具也一天天变简朴了。
科隆韦尔统治英国十一年之久,但是英国最终发现他是一个难免一死的凡人。当他生病的消息开始传扬出来,就有一群急躁的士兵和市民聚集在宫门口。顷刻全国的人都陷入了恐怖之中,因为大家想起了内战时代的混乱,到处都有游兵的抢劫,农场家宅、猪狗牛羊,没有一样会幸免。大家不希望科隆韦尔活着,可是如今又都怕他要死了。
那天天色黑下来,就起了狂风暴雨,其势越来越猛,以至于房屋多被夷平,树木多被拔起,望楼尖塔纷纷倒塌地上。在人们看来,这样的狂风暴雨只能有一种意义:先王的鬼魂来向科隆韦尔索命了。科隆韦尔自己也在惊恐之中大喊道:“落入了活的上帝手中是可怕的呢!”
暴风雨扫荡过整个欧洲,过了一夜又持续到第二日,等到科隆韦尔下午三点钟逝世,它还是在英伦岛上继续作祟。他的遗体立刻被涂了香油,匆匆下葬了。可是他的党徒给他立了一个穿王袍的蜡像,放在莎默塞托宫,好像他是一个帝王。人民却仇恨他,把垃圾扔在他的墓碑上。
他死后没有人能接替他的位,此后大约两年都在一种半无政府的状态中。科隆韦尔本是指定他的儿子继承的,他儿子却没有老子的本领,一班跋扈的军人就把他去掉,倒使他得其所哉。从此就有许多小冲突陆续起来,骑兵和步兵之间,老兵和新兵之间,都起了矛盾,而军队和平民之间的内战也似乎势在必行了。绝望笼罩着全国。第一次内战既然是一无所获,现在难道又要再来一遍吗?于是大家唯一能指望的就是复辟。
孟克将军原本效忠察理一世,察理一世被杀之后才投靠科隆韦尔的,这时群龙无首,他就从苏格兰出兵占领了首都。孟克虽是个军人,他却坚信军权必须隶属于政权,他的希望是解救全国,以免它做军队的奴隶。他审时度势,以便测定全国心理的倾向,直到看明一切阶级拥戴王室的热情已是无可抗拒,他就宣告斯图亚特查理复辟了,立即召集一个自由国会,接着察理二世从布利台宣谕,谕允俯顺舆情,使英国复为君主国。
一时伦敦挤满了保王党人和他们的妻小,如果有人并不诚心渴望皇上回来,他就只得销声匿迹了。自从战事结束以后,人们逐渐恢复了欢笑,至此就突然加紧起来,一切束缚都被挣脱了。假如有人穿着朴素的衣裳,摆出虔敬的面孔,就会被人认为是同情清教徒的确凿标记,只要想表示自己忠于王室的人都要疏远他。世界翻了大大一个跟头了,只要从前被认为罪恶的,现在突然间都变成了美德。
一六六零年五月二十九日,是察理二世的三十诞辰,他就在这天骑马进伦敦。
在他流亡的十五年中,他在欧洲一国又一国地漂泊着,到处不受欢迎,因为各国的政治家们都跟谋杀他父亲的那人有来往,有他在那里是觉得别扭的。现在这种流浪生活总算结束了。在他流亡期间,他一直过着贫穷的日子,一直衣衫褴褛,常常因旅店主人不信任,得向他恳求来日的早餐。现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也算终结了。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他始终都在图谋复国,却一直没有成果,现在总算如愿以偿了。尤为重要的是,他这十五年来受到人家的种种侮辱和轻蔑,现在都可以告终了。总之,他这无民之主无国之王的身份至此竟然终止了。
那日天高气爽,风和日丽,人们都互相告语,国王回銮逢到这般好天气,实在是个吉兆。从伦敦桥直到白宫,凡属御驾必经之路,每一条街道、每一个阳台、窗口,乃至于屋顶,无不挤满了人;虽然人们知道皇车总要过午才到,街上却在清晨八点钟就已没有一英尺的空隙。国民义勇军在街上警备的人员达一万两千,当初他们攻打过察理一世,现在却又集合起来为他儿子回朝维持着秩序。
所有的招牌上面都用五月花做装璜,各条街道都竖着冬青大牌坊;多数建筑的门前都钉着绿色橡树枝。家家的窗口都荡着花环,用缎带和银瓢点缀着,那些银瓢都擦得雪亮地闪烁在日光中。喷泉里面荡漾着红酒,全城教堂的塔上都不断响着钟声。终于听见低沉重浊的炮声,宣布皇车已经到达伦敦桥了。
皇车的行列开始在那些狭窄的街道上缓缓游行起来,马蹄声有节奏地踏着,喇叭和号角吹得震天响,鼓声阵阵如同雷鸣,在周围的山间引起回响。整个行列闪耀光辉,炫目得令人惊疑。它成了一条长河,源源不断:一队队的御林军,有的穿红银二色的大氅,有的穿黑色天鹅绒而全身金碧辉煌,又有的是银绿二色的制服,都配着闪亮的长刀,举着飘扬的旗帜,座下的马鼓鼻腾骧,抬蹄傲然高举。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那行列却还未尽,以致观众们的眼睛昏花而发痛,他们的嗓子都喊哑了,耳朵都被不断的鼓乐震得嗡嗡作响了。
那数百护驾的骑士当初为察理一世打过仗,竟然卖了他们的财物和土地去资助他,后来就跟他的儿子到外国,现在又随驾回来,在行列中几乎做了殿后。他们统统穿着华丽的衣裳,骑着马,只是这套装饰都是向人家赊来的而已。他们的后面就是市长老爷,手里握着一柄出了鞘的刀,是他行使职权时用的。他的一边是孟克将军,一个强壮丑陋的矮子,骑在马上却非常威严,能够获得士兵和平民同样的尊敬。除了国王本人之外,他在当时的英国几乎要算是最得人心的一个人了。在市长老爷那一边骑着马的,是贝科哈的第二任公爵威佐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