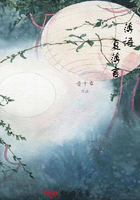京城,广渠门。
五更天了,再过一会儿,天也就快亮了。
京城东面的广渠门外聚集着众多百姓,熙熙攘攘地坐满一地,等待城楼上的晨钟响起。
鸣过晨钟后守军就会解禁放行,城外等待开城门的百姓中,多数为一些种菜的农户,他们早早地起床,在此等候只是为了早点入城找个做小生意的好位置。
卖柴的樵夫、卖碗碟的小商贩、磨菜刀手艺人……一些乱七八糟而又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在城门外堆得琳琅满目。
广渠门是北京城连接外界很重要的一扇城门,城外的百姓可以从这儿进入京城做小买卖,外乡人也可以从这儿进入京城走亲访友。
但是进去后只能在外城活动,内城是不能靠近的,内城被一条护城河围着,绝对禁止靠近,这里面就是紫禁城。
紫禁城代表着大明朝权力的巅峰,它更是大明的核心,好多进京来游玩的富贵或闲士都是远远地观望一下它,饱饱眼福,但这也足以成为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因为它太神奇,太壮观,太令人们神往,但是人们总是忘了里面也太危险。
虽然在紫禁城里面没有兵刃,也没有硝烟,但是相比沙场它会更加残酷,从里面败下阵来的人,要么死亡、甚至诛连到族人,要么充军,终身不得回乡,连落叶归根的权力也被剥夺,被判个“客死异乡"的宿命。
但若地在里边运气好,又精通为官之道的话,也许终有一天能一越冲天,不仅仅光宗耀祖,就连整个家族都摇身一变,成为名门旺族,甚至影响到下面几代人的命运。
正因为这些不确定因素,给紫禁城蒙上了一层层神秘而又诡异的面纱,给人无限遐想,令人向往。
……
王允抬起头,站在远处望着对面的广渠门,感觉自己站在城墙下就好似站在一个拱桥之下。
眼前的这座城门是用巨百砌筑的一个大圆拱,圆拱上面又是一丈多高的石墙兵营室,再上面又是座雨檐指战楼,左右都修有一整排回廊。
城门上方石营墙上密密麻麻开着两层方孔,方孔里面也是个大营室,这些密密麻麻的方孔就是辟箭窗,如遇外侵攻城的话,这儿马上就会关闭城门,每个辟箭窗都会有弓箭手守护御敌,广渠门马上会就变成一座保垒,一座让敌人头痛的保垒。
王允此时不会想到仅仅一年之后,也就在这广渠门下,皇太极调领十万铁骑,绕过自己以前的顶头上司袁崇焕把守的锦远防线,向新开的一门嫡亲蒙古借道,十万清军野战铁骑兵临这广渠门下。
当时身兼兵部尚书、御史、督师辽、津防务的袁祟焕将军,得到情报后,速调九千兵马,从辽东披星赶月地急行军,终于抢在清军的十万铁骑前一日赶到这座城门下,拼死悍卫京城。
可悲的是生性多疑又胆小的崇桢帝朱由检,毅然拒绝了袁崇焕将军先入城整顿军队和休息的请求,下令紧闭城门,让这些长途奔波,从辽东赶来的将士只能在广渠门外扎营休息。
第二日,清军赶到后,这些疲惫不堪的九千大明军士又得迎战十倍于自的清军。
幸得袁祟焕英勇非常、不畏敌众,身披银盔亲自上阵,总是冲在前面,骁勇无比。清军营中无一人能与之对阵,袁祟焕每日斩杀阵前敌将数人,搞得后来清军阵营里的人眼见自己的主将就要败下阵来时,就只能靠后面箭营如蝗的箭雨掩护,才可让前营的主将全身而退。
清军向袁祟焕射出的箭支不可计数,插在他盔甲的空隙处卡住而不掉落,总量之多,使人从远处看袁祟焕,他简直像只插满箭支的刺猬,所幸袁将军有盔甲护身,并无大伤,他咬牙苦苦支撑不让自己停下来,这样做只是为鼓舞士气,不然的话自己的九千人马,面对数量庞大的清军,这九千明军只需主帅渗入一点懦弱的表现,整支军队立刻就会土崩瓦解。
要是军队一旦溃散,对面的十万八旗军想攻破这道广渠门,也许还用不了一天的时间。
后金的神话努乐哈亦,以前就败给袁祟焕一次,之后他的儿子皇太极也败在袁祟焕后里好几回,袁祟焕可谓是金国铁骑的克星,清军本就对袁祟焕有所畏惧,现在又一次次目睹他的神威,无不畏惧。一时间,在实力悬殊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上演着一次次两军拉锯战的奇怪现像。
可是,每一天都是用血用命和清军苦苦硬撑的明军,他们身后的广渠门,却被祟桢帝从里面用大石封死,袁祟焕得不到任何增援与补给,军中无水无粮,若不是城门下有一条小水沟,这九千军士早就不可能有戏了。
城内的百姓不知外面的局势如何,但是城头的护城士兵却能含泪观战。紫禁城内,大明天下最强悍的御林军,还有护城军里三千营的人,哪个不能以一当十?现在却搁置在一旁,对皇上“贴身保护”。
袁祟焕在城门外奋战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在城内传扬开来。
第三天,城内百姓终于冲上城墙,他们不愿看到这大明国的最后一道防线被祟桢帝这样无情地践踏,若是败,大明的国都京城将会沦陷,这将会是每一个大明子民莫大耻辱,迁都?亡国?哪条路都让人无法接受。
汉人的江山是明太祖朱元璋从蒙古人那儿抢回来的,现在后金的清军又想效仿蒙古人统治汉人,像蒙古人一样开辟一个大元朝,这对汉人来说是决对不能容忍的。
清军的几次屠城史更是让百姓恐恐不可终日,但是百姓又有何能力去改变这金国八旗大军压境的局势呢?
短短的三天里袁祟焕的军队消耗了约四千人,死去的将士为国家卖了命,但临死时都空着腹,他们悍卫着这一墙之隔的京城,悍卫着祟桢的皇权,但祟桢却让这些为他拼命而损命的亡灵变成了饿死鬼。
在这关健的时刻,城内一个名叫万曲的富商之妻,领头做好饭菜,用荷叶包裹,再拿红绳捆绑,又在外面套上牛皮纸,最后又是红绳加固,人们称它叫“屈原荷包”。
墙内百姓只要有锅有灶的,都宁愿自己空着肚子,也要先在自己吃饭前做好“屈原荷包”把这救命的粮食带上城墙头,向下扔去,投送给正在下面保卫大明江山的袁祟焕的军队。
城头兵防之地,原本是不让百姓与女流进入的,但城头官兵这时早都不用这种愿坐视不理的态度了,不仅为百姓提供方便投送粮食到城脚下,更是加入其中做好饭菜包好后丢下去。
这种军民涌入城头共事的情景,在明太开祖开辟明朝后的两佰多年里实属少有。
从第三天开始,正当剩下的那些饥饿的明军,人心开始涣散之时,从身后城墙上抛下来的一个个小小的“屈原荷包”又把军队里将士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士气又得以大振。
袁祟焕的这支峥峥钢铁之师,终于可以开始不用饿着去和清军拼命了。
英雄总能创造奇迹,将士们的士气也因这些后方百姓的红线粮包,受到精神上的安抚,这种安抚远远比拿它裹腹更受其用。
“我们并不是孤军奋战,我们身后的百姓与我们同在,就像我们的父母,城墙虽厚,但阻不断百姓对我们的牵挂,大明的百姓们与我们都在保家卫国,清军若想入城,请从我的尸体上踏过,清军可以杀我,甚至可以鞭策我的尸体泄愤,但他别想捉到一个俘虏。”
第四天,明军只剩下一半的人数,近五千人,袁崇焕把队伍分开,形成两组,前面一组与清军对峙,后一组在后面靠着城墙休息,饿了就捡食地上的红线粮包。
这些天,每天都会迎接两三次清军的进攻,说不准下次就轮到自己,但没有人再害怕,士气相当高昂,两军交峰时,每个士卒都是浴血奋战,像为队友挡刀挨枪的壮举随处可见。
这支队伍以形成了一个整体,攻不破,战不降,闲下来的士卒给自己包扎伤口时都是吹着小曲,这儿不可能听得到受伤的兵士的**,就算伤口再疼痛,在这种气氛里谁愿意喊出声来?
这儿体现出的只有好男儿的峥峥傲骨,没有懦弱,甚至没有痛楚和恐惧,面对强大的敌人,表现出的淡然与不肖,给战友的勉励不难想象,在战争的最前沿、在生与死的分界线,笑声,甚至是歌声一片,这种场景太让人不可思议。
反而,对面强大的清军却是一片狼籍,后金的军队长居于北方严寒地代,可现在京城正值酷暑,清军们个个叫苦不堪,皇太极见状更是急于想破城,金国的国力本就弱于在明许多,皇太极这次花大代价挥军十万,他怎舍得失掉这口边的肥肉?但是对着顽固坚守的袁崇焕,就连努乐哈赤这位后金的神话,也只能一筹莫展,只能焦急万分。
第四天,皇太极不得不自披将军服上前营,发动着一次次猛烈的进攻,但都被一次又一次压下来。
皇太极心中不由得感叹:“袁不灭,明则不会倒。”最令清军气愤的是,明军在晚上还点上一堆堆煹火,军士围着煹火又唱又跳,城头上的百姓的喝彩声此起彼伏,这些快乐的声音传到敌方的清军军营里,久久回荡。
这是残酷的战争前沿吗?
是的,的确不可想像,关健是看你怎么去看待它。这些围着煹火又唱又跳的人其实是受袁祟焕之命而载歌载舞,他们没上过战场,没有战斗经验,他们都是擅自作主,从辽东偷跟而来的伙头军,被袁祟焕发现后对他们的惩罚就是让他们轮班不停的歌舞。
不时一个士卒捡起城头扔下来的一个粮包,解开红绳,回到煹火边,一边吃一边乐。
在这儿饿了就能开饭,百姓虽然不都是有钱人家,一个月只能吃一两顿荤腥很平常,可这地上随处可见的粮包,哪个不是装有鸡、鸭、鱼、肉?只是无酒,不过就算有那东西也没人敢去喝,因为…这儿有这儿的规定。
城墙下,煹火旁,一个正在吃饭的兵卒吃着吃着,只见嚼饭的嘴慢慢地停了下了来,双眼一红,悄悄地扭过头,一行热泪滚下脸庞,但他脸上却挂着笑容,
因为打开“屈原荷包”外的牛皮纸时,这张纸背后有一行字映入了他的眼帘。“将士们抛头颅、洒热血,书生无以犒劳,以内人陪嫁玉镯换取燕窝,再由夫人亲手烹饪,盼君品尝。”
陆陆续续更多短短的“信件”出现了,打开这“屈原荷包”时就能收到城内百姓的问候……
“将士们辛苦了……”
“盼望袁崇焕将军早日凯旋归来……”
“好男儿,理应精忠报国。有望将来犬子能效力于袁将军麾下……”
“这是我最喜欢的麻油炸鸡,若是将军觉得合口味,便向墙楼高喊几声麻油炸鸡,我就会让厨子多做几份,将以红布镶裹,便于区分……”
一个年若五旬的老兵,吃完饭拿着一张牛皮纸,四处望了望,散坐在广渠门前的都是四五个一拔,或十来人围坐一拔的,只有一个年轻兵卒,单个背靠在城墙上打瞌睡。
老兵笑嘻嘻地窃笑着向那兵卒走过去,也挨着年轻兵卒坐了下去,刚一坐定,老头就用肩怂了怂那年轻人,“喂,涿州来的小子,喂喂……。”
年轻人被叫醒后,惺惺地睁开双眼,又伸出手捂住嘴打了个哈欠,扭头望了望老兵,问道:“老魏伯,你能不能让我歇会儿,我守那一班四个时辰,开了两战,差点要了我这条小命儿。”
魏老头憨憨地笑笑,拿起他那粮包的牛皮纸,指着上面那几排字,问道:“我不识字,嘿嘿,你帮我念念,京城里的百姓给我写了啥?”
年轻的兵卒接过牛皮纸一看哈哈大笑,一下子睡意全无。
“你笑什么?”魏老头表情很迷惑。
年轻兵卒笑弯了腰,“你…你…老魏伯,你可真会挑,哈哈哈…”
年轻兵卒笑完后又道:“我说老魏伯,哈哈、你一个伙头军,只做做饭,又不能上战场,你是跑这儿来和我们抢哪门子风头啊?”
魏老头不悦道:“将军是没点名要我们过来,我们伙头班子也确是偷跟过来的,我还不是想着这大军远行不带伙头军咋行?你们这帮娃子难不成不吃饭?太不让人放心了。”
魏老头摇摇头,又叹了一口气说道:“将军以为到京后军中的膳食会由京城安排,没想到吃了个闭门羹,主子来个闭门不见。行军太急,我们这帮伙头军跟不上了,只有把粮食扔在半路,可这铁锅我们可舍不得扔了,只有空带了几十口大铁锅,前几日我们挨饿,看着这些锅就来气,我真想砸碎它,举起石头又不忍,唉…,不过我们伙头军也没白来,年轻一点的人都混到前面打清狗去了,甭要小瞧我们。”
“哈哈哈,不敢不敢,得罪天得罪地,我也不敢得罪你们,我怕以后你们做些半生不熟的饭,打发我这个不听话的毛小子,哈哈…”
“嘿嘿,知道就好。”魏老头又问道:“那……那你为什么说我抢了你们风头?”
年轻兵卒被他一提醒,又大笑不止,笑完后抖了抖手中的牛皮纸,让折皱的纸张平整了许多,对魏老头说道:“老魏伯,让我念给你听听,这上面是怎样写的,呵呵呵,不不不,应该是城里的百姓是对你说的什么。”
“嗯嗯……”年轻人清了清嗓子,念道:“今日在城头亲眼目睹众将士奋勇抗敌之英勇,心中澎湃之情久久不能平静,贵军之中个个好男儿,个个真英雄,老夫很是佩服,甚至仰慕,老夫家有一女,尚未出阁,虽无闭花羞月之貌但也算得上一个乖巧孝顺的大家闺秀,只要是城外军中之人,无论官职高低,无论是将是卒,若能瞧得起小女,老夫愿把小女配婚与尔。朝阳街尾,马氏。”
魏伯听完后大感窘迫,站起身来便道:“这一包不是我吃的,这一包不是我吃的。”飞也似的跑开。
“哈哈哈……”魏伯身后又传来年轻人一阵笑声。
……
“让开让开,快让开……”军中一阵骚动,四五个偏牙将抬着一人向后面跑来,抬到城门处时慢慢地放下来。后面一起跟来的几十个士兵议论纷纷。
“将军从马上摔了下来,昏了过去。”
“他太累了,我们可以轮班休息,将军很少下马,总是跑来跑去,生怕哪里出现什么闪失。”
一个身着偏牙将军服的人这时放下袁崇焕后,向城楼上大喊:“袁将军病倒了,请城防军中的大人们帮忙打开城门,让我们将军进城医治。”
城楼上没反应,偏牙将有些急了,又朝着广渠门上喊道:“请城防军中的大人帮忙打开城门,让我们将军进城医治,我们将军现在可不能有何闪失。”
……
还是没有人回答,偏牙将咬咬牙一个单膝跪地,嘶哑着嗓子喊道:“城楼上的大人们,请你们……”
“打开城门……打开城门……打开……”城墙头上的百姓忍不住了,一起高喊起来,声音越来越大,要求护城军打开城门。
这时城楼上的指战台上,走出一个人,恕气冲冲地对百姓吼道:“你们是不是想造反了?圣上有令,不准开城门,违令者……宰。”
城楼上回话的正是现在刚入内阁府的温体仁,明朝自从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后,各届君王朝野均无宰相一职,这样做可以避免权倾朝野的情况出现,使其不让官员的权力过余的大。
内阁府就相当于以前的宰相,不同的是它用内阁数个官员分担一个宰相的权力,内阁府的人,权利较之其它职位,还更很突出更优越的。
四个偏牙将听到城楼上指战台里温体仁的话后急了,一起齐刷刷地跪在城门下:“恳请大人求圣上开恩,先救一下我们将军。”
可是广渠门上的温体仁并不允许,只是对着城墙下边的对四个偏牙将怒道:“你想们还反了吗?现在清军就在对面,你们不把他们驱逐出境,守在这儿又有何用?我放任白姓投给你们粮食,已经是太纵容你们了,你们却不知好歹地要求越来越多,真是可恨之极。”
“温大人,看在你和袁大人都是同朝为官的面子上,你就求求皇上,先让将军进城吧。”
温体仁却冷冷地回道:“圣上让袁祟焕镇守辽东,抵御后金,可他倒好,现在金国都打到京城了,皇上现在很是震恕,他袁祟焕得先收拾好自己的烂滩子。”温体仁越说越来火,后面的话是又指又跳着说完的。
“温大人,清军是越过我们的防守,绕道蒙古过来的,蒙古那边并不是我们的防线,我们已经是用最快的速度赶来救援的,还温请大人明察。”
“我可管子不了那么多,只要来犯事儿的是金国人,你们就脱不了干系,袁祟焕在辽东都五年了吧?可他总是只守不攻,消极抗金,每年只会拿朝庭的银子修筑什么破工事,他只是贪图安逸,只求自保,而不深入进去剿杀满族夷蛮,今天的局面他袁祟焕得负全责。”
“大人,灭金之愿,本就不可能是朝夕之事,欲速则不达…”
温体仁不太耐烦了,挥挥手道:“行了行了,城门绝不会开,我猜到时我一打开城门,你们一涌而入,又要退守京城吧?”
“水…水…。”
“是将军,快,快拿水。”几个偏牙将听到袁祟焕的声音后,都反身向袁祟焕围了过来,扶坐好袁祟焕在担架上坐定后,用手托住他的背心,端起羊皮水袋,揭开木塞后送到他嘴边。
袁祟焕喝了几口水,双手用力支起身子坐好后,开口问道:“我昏倒多久了?”
“回将军,快有半刻时晨了。”
“呃,还好,扶我上马,让我到前面看看。”
“将军,再这样下去我们会全军覆没的,每天消耗一千兵勇,我们撑不了多久了,反顺都是死,不如我们向清军反攻过去,死也死个痛快,也让身后城楼上那些内阁府的人看看,我们并不是贪生怕死的人。”
袁祟焕狠狠地看了他一眼,虚弱地说道:“攻?我们全军覆灭事小,但我们都死了谁来守护这京城?”
袁祟焕说到这儿又放低了嗓音,说道:“唉………我知道我的军队里没有鼠辈,但是我们都死了的话谁来保护皇上?里面的御林军和护城军虽说厉害,但数量加起来还不到两万人,也不能确保万无一失,我们得坚守在这里多一天是一天,清军没机会攻城就成了,会有……会有我们的援军赶到的。”
一个偏牙将轻轻地叹了口气,对袁祟焕说道:“援军?这不太可能了,若是等圣上调南方的军队过来,也许得半个月后,现在各地农民义军蜂起,东边和西边乱成一团,各处的兵源都很吃紧,圣上根本就调不了多少人过来,况且……我们也没机会等那么久。”
袁祟焕点了点头,说道:“南边的军队我可不敢指望,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人,别忘了我们还有布满桂,他应该会来救我们。”
偏牙将吃惊地问道:“布左督统?若是……可若是他带人过来之后,我们在辽东花数年打造的防御,就没人守了,整个防线会成为几座空城,若敌人来犯,后果…后果将会是敌人不用大规模开战,一下就能夺得整个辽东,我们五年的心血不光会功亏一篑了?我们也都会是死罪。”
袁祟焕轻轻的摇摇头道:“敌人?辽东哪还有敌人,这次金国的军队差不多都倾巢而出了,再也抽不出多少人去攻打我们设在辽东的防线了,同样现在金国也差不多是个空壳子。”
袁祟焕强支起身子,坐了起来,又说道:“布满贵有勇有谋,他现在要么会去攻打金国,要么会援救京城,他如果现在去攻打金国这个空壳子定会十拿九稳,但这样一来就无法救援我们,也可能因此而失掉北京,呵呵……满贵不傻,他不会用京城做赌注去换取金国的一片冷土,所以,他一定会来,一定会。”
“这是要干嘛?喂……喂喂……你们想干什么?你们是在干什么?来人啦……来人啦……”城楼上又闹了起来。
原来这时有几个郎中从城墙头丢下几条绳子,几个京城的郎中得知袁祟焕病倒后,背起药箱相约而来,准备利用绳子从城防楼的墙头滑下去,再到城门下替袁崇焕医治伤病。
五条绳子都系牢后,郎中背起药箱,开始抓起绳子向城墙下滑去。
这时城楼顶上指战亭里的温体仁看见后,大怒道:“谁放的绳子?反了反了。”温体仁转过身又朝营室的兵卒大喊:“弓箭手准备,快给我杀了绳上的人,杀了放绳子的人。”
营室的弓箭手面面相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都不愿把手中的弓抬起来对付自己的百姓。
温体仁粗着脖子对身边的弓箭手吼道:“我叫你们放箭,射杀放绳子的人,如果清军攻过来,会顺着绳子爬上来攻城的,你们都不要命了?我叫你们快射箭,快射,违令者立宰。”
温体仁高喊的话语让城楼下面的袁祟焕的军队听闻后大惊,军中之人都抬起头,对着城楼上大呼:“别放箭,不要杀我们的百姓,温大人,看在百姓是想来救人的份上,你就放过他们吧!他们并无意冒犯军规。”
好多人几乎是用一种沙哑的声音在向温体仁乞求。温体仁身后的几个弓箭手拉满弓后手糠糠作抖,不想放箭出去。
“放箭,再不放箭我就杀了你们。”温体仁扭头面向弓箭手高喊。
“嗖嗖嗖嗖…"弓箭手们都是闭着双眼,把这一组箭射出了去。
箭支……全部都偏离目标甚远。
温体仁见状之后,一把揪起其中一个弓箭手的衣领,大怒道:“短短五十来步的距离都射不准?你们都是瞎子呀?再放箭,若是谁射不到,我要把他就地正法,立刻宰首。”
“嗖嗖嗖嗖…”
第二拔箭射了出去,七支箭,在这么短的距离不可能脱靶,七支箭全部命中,对面的三个郎中立即毙命,另两个郎中虽只是受了箭伤,但是他们都从广渠门的城墙上跌落了下去。
“嘟……嘟嘟……”几声闷响,这是人从高处跌落到地上的声间,每声闷响都如一把利刃插进人们的心窝。
“驱逐城墙上的白姓,如果谁再登上城来扰乱军队运作,杀无赦!”温体仁双眼布着血丝,高高在上的喊道。
城下的明军个个怒火中烧,咬得牙“咯咯”作响,袁祟焕用力合上双眼,他不忍再看,由于身体太虚弱,张嘴说的话都被淹没在一片叫嚷漫骂声中了。
此时,只见袁祟焕身旁一个偏牙将转过头,对身边的护卫说道:“到前面弓箭营取一弯弓箭来,不要让人看到。”
“是。”
不一会儿,两个护卫兵用战旗包着一柄强弓和数支箭羽交给偏牙将。
偏牙将又对身旁两个兵卫道:“现在你们并肩挡在我前面,挡住城楼上那些人的视线,不要让城楼上的人看到我的弓箭,你们两人中间再留一点空隙出来,要便于我放箭,我要……杀了温体仁。”
偏牙将最后的那几句话差不多是从他牙缝里挤出来的。
两个兵卫听闻后心里大惊,射杀内阁府的人,就等于去射杀天王老子,但是军令不敢违,二人只能依照着牙将的要求,挡在他面前,不让城楼上的人看到二人背后那个蹲在地上拉着弓,准备实施暗杀的偏牙将。
偏牙将蹲在地上,两个兵卫满脸通红地挡在了他前面,只见偏牙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再屏住呼吸,慢慢地拉满弓,朝着前面这两个兵卫中间的空隙中望去,看着令他咬牙切齿的温体仁。
偏牙将与温体仁仅仅只有七八十步之距,这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射杀距离,只见他对着城楼上的温体仁慢慢抬起箭头,瞄准……瞄准……
这时,偏牙将身旁的袁祟焕扭过头,刚好看到这一幕,他马上明白了偏牙将的意图,袁祟焕大惊,立刻对偏牙将高喊到“范尹虎,使不得。”
范尹虎听见将军的呼喊,扭头望了一眼袁祟焕,再回过头看看城脚下的那几具郎中的尸体,这几个从城楼上刚刚被温体仁下今射杀的郎中,让范尹虎再也无法忍受,此时唯一让他觉得可惜的是,自己不是战死于沙场,自己将会成为一个谋杀朝庭重臣的罪人。
想到此,年仅十九的范尹虎不禁红了眼睛,他本是军中的才俊,论文论武都出类拔萃,可现在,他选择了抗命,只见他扭过头,轻轻地对袁祟焕说道:“将军,尹虎从军以来从未违抗过军令,但这次我愿受军法处置。”话毕又扭过头,双眼一下子闪出了泪光。
“使不得,大局…大局为重。”袁祟焕体力不支,声音无法压过军营中向城楼上发出的那些混乱的叫骂声。
“嗖……”
利箭划破长空的声音,格外急脆。
紧接着,城楼上“啊……”地一声惨叫,温体仁中箭倒地。
袁祟焕闻声,眼前一黑,急得晕了过去。
范尹虎本是明军中数一数二的神箭手,但这次很可惜,他并没能击毙如此近距离的目标,他的箭只射中了温体仁的右腰,虽然箭支力度惊人,透腰而出,直没箭羽。
但是非常地可惜,百发百中的范尹虎,这一次并没有射中温体仁的要害位置。
范尹虎放箭之时,眼中有泪,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使得利箭失准。
也因为他的这次失误,让以九千兵力去面对十万清军铁骑,顽守京城九天最终迎来布满贵大军救援的袁祟焕,大功之时却得大难,含冤入狱……一年之后就被崇桢帝朱由检绞杀于狱中。
皇太极最大的克星,也就从此陨落,大明的最后一个能抗衡金国铁骑的英雄袁祟焕,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
不会有人知道,改变明、金两国命运的,竟是范尹虎的两滴眼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