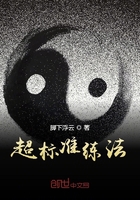翌日清晨,友康醒来,发现丑鬼韩潇子早没了人影,估计他是解决师门之事去了,友康也没记挂在心上。睡在身边的小家伙早醒了,歪着小脑袋眨动贼亮亮的黑眼睛好奇地瞧他,没吵没闹。友康简单地收拾一番,背上包袱和小家伙,空着肚子顺着街道,望着前方郁郁葱葱的古道行进。
莫忧雨道是一片望不到头的绿色森林。因为树高林茂,人在地面根本见不到太阳,一旦进去根本辨不清东南西北,像一只瞎眼的鸡到处乱撞。又有无数藏匿暗中的猛兽毒蛇出没其中。相比其他猎物,身重胆大的吊睛白额大猛虎更喜欢挑那些身形蠢笨的两只脚的人类为食,形单影只、势单力薄的落单商旅自然成了这种大虫不费力的口粮。对于经验老练熟悉这条古道的跑路子来说这都不算什么,猛虎可怕只要不落单成群结伙二三十人抱团一起过,这种独居的大家伙不会轻易招惹一大帮子人,最可怕的是另一种凶兽:银背火云豺。
金黄色的光线映衬友康黑色的发尖发亮,透明的汗珠顺着湿漉漉的下巴滴下脚底的泥土,黄土夯实的道路平整得寸草不生,与路边的杂草显明得如同两个世界,友康望着莫忧雨道幽深望不到尽头的浩远,心里发起毛。自己一个人还好,现在又拖着个孱弱的孩子不知能否安全穿越这茫茫无边的荒林险道。前方一阵如同夜晚的夜猫子一样渗人长嚎的不知名鸟啼挑动心窝不自觉的惊颤,但一切都已注定,他必须走,即使这片深林雨道是刀山火海他也必须闯,自己的命早在几天前就不属于自己,当他在那份10年雇佣兵契约纸上按下自己鲜红的指印时,他已经无路可走。
狭长的道路只容下两辆马车并行,闷热的空气搅得好像世界末日,头顶的阳光只洒下手巴掌大的光亮,没走多时,友康就听到熟悉的风铃脆响,昨日不可一世被唤作‘清童’的男人依旧骑着他的高头大马从友康身边驰过,全身热汗的友康听到清童不爽的咕囔声‘世界咋那么小’。气得友康想顶出一句:路是你家开的。
后面紧随而来的三辆精致马车也缓缓从友康身边驶过,不知什么原因,居然慢慢地停了下来,接着还是那一身婢子打扮、身材苗条的女子从车上下来,优雅地迈着深有礼教的步子冲着友康悠悠走来,在友康身前做了一个漂亮又不做作的万福金安,“夫人命我请小公子进膳”说着,女子恭敬地接过友康身后的小家伙,小心地踩稳马凳,倩影一闪消失在马车内。
树顶繁密的绿色割裂了浩瀚的天空,像一道无边的长形天窗漫伸到视线的尽头,火凤看着风师弟压得底底的黑色斗笠,默默地不做声,心里心事重重,摇摆不定的念头一次次让她挣扎不已,终于她停下脚步。
一直在前头的风旋感受到她的犹豫,自卑地没有转头,“你丢不下那个男人”
火凤摇摇头,“不是。”
“那就好,和我一起走,师姐。到深山老林,到万里异域,到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世界,什么师门?什么仇恨?什么闻道求仙?我全不在乎,我只想和你神仙眷侣般逍遥自在,抛弃这羁绊脚步的名和利,抛弃这折磨心智的世俗一切,只有你和我才是真的。”
火凤噙含着滚烫的热泪,心摇神驰地看着师弟无法抑制的颤抖背影,“我丢不下——我的儿。”
风旋被火凤带着哭音的声音击打得止住了颤抖,身体也好像被这打击压垮掉半截,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问:“谁?”
“我和他生了一个儿子。”火凤无奈地倾出郁结在内心许久的痛点,她不敢去问师弟是否能接受这个孩子,不是他的种的孩子。如果他的心真有那么大,容得下这个孩子,每天强颜欢笑去应付自己,好让自己感到他与孩子之间心无芥蒂,但强饰出的幸福就是他真想要的幸福吗?孩子是摆在她和师弟之间的一根根本无法磨除的刺。她看着师弟失魂落泊的样子,转过身,向来时的路,和师弟越行越远。
“莫忧雨道”斗笠下风旋的脸扭曲成难看的三角形,裂疤疤的脸上肌肉缩成硬邦邦的一团,“谁给你起的这么文雅寒心的名字。”他只想抛弃世上所有缠紧身心的世俗框框,但无情的现实却把他顶可怜的一点小小愿望揉碎得拼不出丝毫模样。
小家伙翘紧的嘴巴回味着甜甜的笑意,嘚瑟得打着漂亮的饱嗝,醉咪咪的小眼一开一合,漂亮婢子打扮的女子小心地将小家伙抱在怀中,小家伙好像很享受地冲她一笑,好像很不情愿地再被送到友康怀里,友康没好气地捏着小家伙柔软的红脸蛋,骂道:“没良心的小色鬼。”女子温柔地笑了笑,没有说话。马车又缓缓起行,叮叮悦耳的风铃声在碧绿色的林海中轻轻摇响,仿若一场虚晃柔情的美梦使人贪醉地不愿醒来,那清颜的笑靥,含蓄凝情的眼波,扣动在心灵深处,像荡涤灵魂余思的鸣颤。天空里突然的一声鸟鸣戛然住友康怅然若失的一声轻叹。
小家伙吃饱舒心地在友康背后熟睡,友康又只剩下一个人孤独地踏着细沙似的尘土继续自己危险的旅程,这时,不知他为什么想到了一个早已消失在脑海中的一个人,他莫名地急切渴望知道她还好吗?她在哪里?——羽惜。
马鞍上狼头韩武挺直腰背,鹰鹫般冷若寒霜的眼睛扫视着苍狼组每一个人,全身漆黑的每一个队员都以同样寒厉威武的姿态回应队长一丝不苟的检视,胯下和人一样漆黑的战马也感到气氛的凝重,腰胯的肌肉收缩拉紧,黑色的马蹄铁踩得青石板叮当做响。看到这一切,韩武面无表情地转过头,踢着马肚,一骑领先飞出。全身赤黑的二十骑如同二十股急速的黑旋风,诡异得如同黑夜下的白色幽灵,绝尘于赤裸裸的金色日光下,一路凝练着杀人的深意。
脑后急速的马蹄声一下下震动脚底的大地,似千军万马齐速奔腾,友康被这突如其来的压顶气势惊得开不了口,急忙侧在路边,看他们劲头的狠劲根本没把他这个道上的大活人丢在眼里,就算自己被他们踏为肉泥,这群人也不会勒一下马头减速,二十骑像二十团浓墨的黑云看也没看他一眼风驰电掣地飞过他身旁,‘疯子’友康一口气骂出心头的不爽也为了减轻一种不被当人看的羞辱感。‘这样不惜马力地狂跑会把马累坏的’他想,然而一转念又为自己刚才不公的对待愤慨,“去他妈的,谁管那么多呢,又不是我家的马。”再说他家也买不起马,即使一匹干粗重活的驽马。
燥闷的空气有了一丝风,马背上纯红色鬓毛微微被裹起,散乱得像风中女人的长发,清童轻轻抚平马背上的红色鬓毛,心理想着愉快的念头:出了这林高树密的莫忧雨道,前边就是一马平川,距离上都近在咫尺,这一趟行程也就放下8分的心,他想:只要自己把小公子和安姑娘平安送到主人手上,主人这匹被称为火焰神使的红色北原马,自己一定能求动主人把它舍爱赐给自己,正如花心的男人都爱漂亮的女人,贫寒小家的漂亮小姐都爱坏坏的公子哥,他清童只爱马,当然要极品纯种的良驹,但他的美梦还没享受完,身后步调一致的马蹄轰鸣声击碎了他的幻想,刚刚幸福的脸色一下苍白得没有了血色。
眼尖的韩武早早就看见视线尽头那三辆豪华马车,冷峻的瞳孔收缩成点睛般精亮的一点,他狠踢一下马肚,胯下的黑马猛劲地向前一窜,狠狠地提高了奔速,身后的漆黑色十九骑也如同十九具白色幽灵尽随头领身后,所有队员冷静得如同十九个哑巴不吭一声,集中精力的十九双眼睛像十九把雪亮的刺刀全聚焦狼头韩武的手上。韩武沉静如同一具死人般的雕像,马和人像连同一体的怪物,他左手把住缰绳,右手直直抬起,四指收紧,食指竖起指刺天空,摆成‘1’的手势,身后的19骑开始微微放慢马速,呈扇面形散开,第一排4骑全部两手放开缰绳,抽出身后破甲弩,瞄也没瞄,只听到一声‘砰’的弦响,四只黑色飞箭抛进空中,跟同一声弦响的是韩武石块般的手指飞变成‘2’,第一队整齐划一地滑向两边,第二队5骑没有滞泄得完美地前冲、利落地衔接跟上,又是一声‘砰’的弦响。
清童还没反应出怎么回事,一转头的瞬间,他看到第3辆马车后的护卫哼也没哼一声,成批的倒下,他清楚地见到一支箭穿破一个护卫的头盔,从那可怜护卫脑门正中又穿出,凶猛的箭势丝毫不止,又扎进前面一护卫的脖颈,鲜红的血一下染满护卫的前襟胸甲,死亡的痛苦恐惧让那被死神抓住脑袋的护卫惊愕得扩开奇大的嘴巴,却不能说出一句人话,‘咳咳’的丝丝热气从他吼尖不断地吱吱喷出,扎在脖上的长长箭尾震颤不定,好像开怀地嘲弄他不堪一击的脆弱。清童看到这短短的一切,下意识地不是去吼叫‘避开’,乱哄哄的脑袋只冒出一句话:完了。
韩武看出眼前的护卫也是一流之士,慌而不乱,有组织地分散阵型,有的护卫甚至开始反击,韩武冷冷地看着他们,右手已变成了‘4’,一直沉默不语的他终于开口吼道:“第二辆马车”,第四队微微竖起箭弩摆好角度,6支飞箭刷得一下全飞了出去。
清童听到‘第二辆’,他的脸已经白得不能再白,第二辆马车里有小公子和安姑娘,“挡住”,他对手下的护卫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吼道,护卫在第二辆马车的护卫们全部握紧盾牌,围在第二辆马车前后左右,3支箭射死3个护卫,另外3支箭2支射在马车顶部,没能穿透马车内部的玄铁护甲,最后一支箭却从车后射穿了进去,清童只听到一声非常凄厉的女人嘶叫,接着极快地没了。‘完了’他嘴巴上重复这个词,现实再清楚不过,这箭头不是一般的破甲箭,是孤竹国皇室才能拿到的战略武器,“零度子午箭”,这个号称破尽天下万甲的万箭皇镞。他想问:到底怎么了?为什么皇室会和他江南第一家郑家过不去。
马背上的韩武岿然不动,放下的右手抽出寒光闪闪的马刀,一马当先冲了出去,身后的19骑也刷得一下全抽出马刀跟着狼头飞奔战阵。飞奔的马带着速度的优势,一眨眼冲到距他最近的护卫前,一个照面手起刀落,那个护卫身子一软,马拖着死去跌落的尸体擦肩而过,被斜削飞的半个脑袋“啪”的一下砸在地上,踩成一滩稀泥。韩武面不改色地继续猛冲,轻巧地避过第二个护卫刺来的长矛,又是顺利的一刀,连人带甲劈为两半,喷出的鲜红热血湿透了韩武半个身子和胯下的马肚,他的脸依旧冷若冰铁,没有被热血融化半分。
清童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群来人不要命的凶戾,他拨转马头,冲到第二辆马车,用刀拨开车帘,一道热血碰到他的脸上,“夫人”他大叫,夫人胭脂擦红的脸已经白成了纸,如注的血从她的嘴里汩汩冒出,尖利的箭头一箭穿心,睁大的眼睛死不瞑目,死白的眼珠没有生气地死死地盯住清童的脸,清童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得一哆嗦,脑子断线般停顿一秒。接着,他看见安姑娘紧紧搂着小公子惊恐得望着他,求生本能的渴望支配她眼巴巴地企望着他的力量,旁边的奶妈吓成了个傻子,呆若木鸡。“快上来”,他伸出手,示意安姑娘递出小公子,安姑娘立马回过神,送出怀中的孩子,自己跳上清童的马,清童狠劲地抽打马,吃痛的红色‘火焰神使’踏蹄飞出。
狼头韩武在乱阵的拼杀中,早瞧见清童的一举一动,他用眼神示意身旁手下,对着清童的奔逃方向,冷静地说了一句:“凸眼,射马”。脸蒙着黑布的‘凸眼’端弩搭箭,稳平身子,一箭飞出。清童本能地感到凉飕飕地刺骨之寒,夹紧马肚一提缰绳,‘火焰神使’凌空窜起,飞来的箭矢从马肚下险险插过。韩武阴沉的脸没有多说一句,一把夺过‘弩机’,飞快地搭箭,箭头直指清童的后心,‘砰’的一声,箭身飞出,清童抱住安小姐,拼着自信的骑术前附身体侧歪,箭头没有把清童射个透心凉,却穿过上臂,削掉‘火焰神使’的左耳,突然吃痛‘火焰神使’发起脾气,突然撂蹄前翻一把撅飞背上之人。清童和安姑娘被重重得甩在地上,安姑娘为了护着怀中的孩子,头被磕破了血。暴怒的火焰神使掉头飞驰,疯一般撞飞一个护卫向后奔去。清童绝望地看着这一切,无能为力。
韩武一击得手,把弩箭扔回凸眼,策马向前,手起刀落,如入无人之境。马背上一个鹞子翻身,右手黑色匕首的刀身划着白色气流华丽地割断安姑娘的秀颈,左手探囊取物抓住安姑娘怀中的小公子。安姑娘凭着意识感到双手空空,心中一急,忘却脖子上的疼痛,气血上涌,‘噗’的,血像一卷展开的红画铺在空中,“孩子”,热血攻心的身子如残破的风筝倒在地上,僵在空中的血又像被人重重一拉有灵似的全跌进泥土中。
韩武抓住手中的孩子看着苍狼组干净利落消灭了垂死挣扎的护卫们。清童不顾出血的手臂爬到安姑娘的身边,摇着她没有半点反应的身体,安姑娘的血染满他的手。韩武冷冷地看着他,抓住小公子,打马飞去,身后的19骑也随着头领驰去,只留下孤零零的清童和遍地的血色与尸体。
清童抬头望着灰色的天空,不知什么时候太阳已近不见了。他想他完了,安姑娘死了,小公子也丢了,主人交给他的任务他失败了,他颤巍巍的掏出腰间的匕首,抽出刀鞘,“我对不起你,主人。”他喃喃自语,猛地扎进自己的心窝,死死的不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