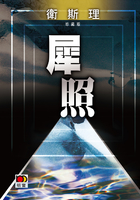周四平又去拜见齐长安。周四平选择了晚上时间,行前特地通过某个可靠途径了解齐惠的行踪,确认她当晚没有回父母家,他不想在那里意外撞见她。周四平在动身前给齐长安打了个电话,问岳父晚上有没有要事,他想去看看他。齐长安平静道:“你来吧。”这个答复在周四平预料之中。
周四平有很长时间没到岳父家去了,他和齐惠关系一直处于僵局,这种情况下出入齐长安家门让他十分尴尬。这天晚上他考虑再三,觉得就他要谈的事而言,上门拜见比较合宜,因此也就不管其他了。
齐长安在他那宽敞的大客厅里对周四平说:“我也正要找你。”
他请女婿喝茶。他闭口不谈齐惠的事,几天前他打过一个紧急电话要周四平到水上乐园为齐惠解围,此刻他只字未提,好像它从来没有发生过。可是周四平知道那件事的影子就罩在他们之间,岳父对他挺感激,他能从齐长安的言谈和语调里感觉出来。
齐长安对周四平说起本市对外经济交流协会的宋会长,这位会长跟齐长安是老熟人,两人关系一直不错。前些时候在一次晚宴上,齐长安跟这位宋会长坐在相邻的两张椅子上,宋跟他提到周四平,说:“你这个女婿有点忘乎所以了。”
“你什么时候得罪她?”齐长安问周四平。
周四平跟他说起前些时候洪承宗那家公司开业座谈会的事情,齐长安点了点头,说:“你可能太冲了一点。这个宋是个大夫人,你知道的。”
周四平苦笑道:“她帮着洪承宗逼我,没法子。”
周四平对齐长安提到了他的计划。
“我听说了。”齐长安说,“你的念头挺奇怪,不过我想你肯定有你的理由。听说进展还顺利?”
“目前不错。”
周四平把他所做的努力大略说了说,齐长安道:“你要注意,你的麻烦会在后头。比较而言,你跟洪承宗的事情只能算小事情,发展下去,可能出现的是你跟一些权力部门,包括能制约你的那些部门之间的问题,你考虑到这种情况了没有?”
“洪承宗有一个特殊身份,经历也特别。”齐长安说,“广告铺天盖地,推销术别出心裁,还有一场大雨中的演唱会,从这些现象看这个人确实很有能量。你现在以那块地的占有者身份还能跟他相持,但是你们相持的结果,必然就会有某个权威部门出来干预解决。我看不出到时候你会有哪些地方比他更有利。”
齐长安提到了洪承宗出席某一个城市规划研究小组例会的情况,这个小组的成员都有些来头,不是太容易对付,洪承宗却成功地得到了其中不少人的认同,让他们认定他正在为本城办一件极好的事情。这情形反过来必将成为周四平要承受的压力。
“我已经感觉到了。”周四平说,“有一些相关部门例如外经外事部门正在对这件事提出看法。他们认为应当鼓励外商投资,应当支持外资进行开发,本地企业不应相争。还有不少人认为我提出的那个建议接近于荒谬,能够把一块地拿去卖大钱,干嘛要在上边贴大钱?我知道这些议论肯定会越来越多。压力会越来越大。”
“这样的情况你还要继续干?”
“是,我是这样打算的。”
周四平对齐长安说,他认为在考虑钱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其他东西,为人做事只从钱或者利益的方面去考虑绝对是一种偏颇。他说最近他比较多地思考过这个问题。
齐长安很注意地看了他一眼。
“您知道近来我有些事不太顺。”周四平黯然笑笑,“这种情况下总是多思。”
齐长安非常简洁地评论道:“这好。”
周四平说他相信事在人为。有问题不怕,一个一个去解决就是,一个方向不行,就从另一个方向去寻找突破,总能找到办法。
“今天来是想向您请教,我正在找一些可以利用的融资渠道。”
齐长安没有表现出一点意外,他非常精明,不会猜不出周四平找他的主要原因。
周四平跟齐长安提到了他们解决建设资金的办法,包括几个合伙单位的投入,从社会及海外募集资金的具体思路。周四平向齐长安询问为他的这个计划从银行某个特定项目里争取到一些低息贷款的可能,探讨从省里,从其他地方其他银行,甚至从北京有关机构融资的可能。齐长安沉吟良久,说:“小周,你是真的?你绝对不放弃这个计划?”
周四平道:“您知道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时不时心血来潮的人。”
齐长安低下头,轻轻朝茶杯吹一口气,把浮在茶水上边的一片茶叶吹到一边去。
“你看看我,”他放下茶杯,笑着转开话题,对周四平说,“我老是想起那一年的冬天,我让她妈妈拿一点钱,托你给……小惠送去……”
周四平垂下眼睑。
他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在他和齐长安之间有一条维系的纽带,这就是齐长安无比钟爱的齐惠。事实上这条纽带已经丝丝缕缕只剩一点一根指头就能扯断的关联,如果这一点关联真给扯断的话,他和齐长安就完全形同路人了。反之,如果他能维持住这条纽带,他就能够继续得到齐长安的有力支持。齐长安是一个银行行长,他的身份非常重要,可以办成许多别人无法办成的非常困难的事情。
周四平为自己公司的员工安排了一次周末活动,他们的周末活动总是别出心裁。
那一回他们去打靶。周四平组织这一活动的灵感跟俞怀颖有些关系,那一天俞怀颖在城北高地小楼下对周四平说即将率人民代表前来视察的马主任有行伍之风,周四平灵机一动把小楼的招牌换成“作战部”,把自己弄得有如草头司令,居然让主任大悦,取得小胜,那以后周四平真有点走火入魔,魏国强问他周末活动搞什么,他情不自禁就提出打靶,好像他已经率公司众多员工应召入伍了似的。
魏国强去做了联系。魏国强办事能力很强,跟一些军方人士有关系,知道这类活动该怎么操作。两天后他就报告事情办成了,本市某驻军部队欢迎本公司员工去他们的靶场组织打靶活动,这一活动经批准已纳入某国防教育和民兵训练科目,所需经费双方已协商安排妥当,届时该部队将派员指导,协助开展活动。靶场地点在城郊三塘村附近某山间,是一个时有训练活动开展的军用露天简易靶场。
于是星期六上午周四平便率众员工前往靶场。三塘村靶场离三塘村还有相当长一段距离,位于山沟沟里,地点相当隐蔽,想来是因为军事需要。靶场大如足球场,三面环山,正面土山下部劈开一面坡,作为靶标区,地面挖有壕沟以供报靶。靶场比较简易,只是地面略做平整,铲掉杂草蓬蒿,保证射击安全。靶场附近有一个部队军械库,有一些军人驻守于此。
对年轻人而言,打靶活动挺新鲜,那天一到靶场,大家都兴奋不已,配合活动的部队教官扛来了五支冲锋枪,让大家列队,讲解射击要领,然后把枪放在五个射击位上,每位有一位教官指导,人们一组五人,开始卧地打靶。
周四平没有下场。进入靶场之后他就在外围走来走去,耐心等待。
他在等待两个人:马悦主任和俞怀颖。
在确定周末活动内容之后,周四平便给马悦主任打了电话。周四平是在那次人大代表的视察活动之后跟这位马主任打上交道的。那一回马悦带队到高地视察前,曾请俞怀颖介绍情况,并因此认定俞怀颖有道理,含远楼遗址应当保护,他要通过代表视察活动来加以促成。可是一到周四平的“作战部”,看到周四平往两张“战略态势图”前一站,马主任对他的印象竟然相当好,听了周四平一番解说,马主任的立场开始动摇,觉得周四平也不无道理。此后周四平又专程找他介绍情况,做了不少工作,末了马主任和他率领的代表团成员讨论了半天,决定进一步了解情况,暂不对含远楼问题提出最后意见。周四平对这一结果感到满意,他知道俞怀颖肯定是另一种心情。
因此周四平要请马主任打靶,周四平在电话里说他知道马主任在部队里是神枪手,他们公司的年轻人都很想亲眼见识一下。
“你要不来我们可会让人笑话,”周四平说,“我那些人里没几个摸过枪,他们只会浪费子弹。”
马悦便答应下来,说:“好啊,还真有点手痒。”
周四平提了个要求,请马悦叫上俞怀颖:“我不敢去叫她,她对我有误会。”
周四平说他希望借此机会消除误会。那一天出于无奈,他对俞怀颖多有打击,把她得罪了,俞怀颖至今对他耿耿于怀。周四平说其实他对俞怀颖十分看重,在这个世界上他最不愿意伤害的就是她,如果马主任能够帮他们消除误会,他会感激不尽。
“她对您很尊敬,她的工作也需要您支持。”周四平说,“您请她,她会来的。”
马悦答应了。周四平特别交代说,千万别跟俞怀颖提到他,否则她肯定不会来。
“您知道她的脾气怪得很。”周四平说。
那天上午,当靶场上“砰砰砰”响彻枪声的时候,果然有一辆“桑塔纳”轿车从三塘村方向开来,驶进靶场边的停车场。周四平迎上前去,他注意到那车对他十分敏感:车门不开,没有谁走出车来。
这情形在周四平的预料之中,他一点也不在意,径直走到轿车旁,一躬身子,打开了右后侧车门。
马悦和俞怀颖都在车里。
“你看看,小周。”马悦笑道,“小俞挺意外。她不高兴呢。”
“是我的不是。俞专家别在意。”周四平说,“马主任是好意。”
他请马悦和俞怀颖下车打靶,说:“既然上了贼船,就下来试当一回贼好了。”
俞怀颖冷冷道:“谁跟你当贼。”
她拒绝下车,说:“马主任您去吧,我对打靶没兴趣,我宁愿呆在空调车里。”
周四平也不强求,拉起马悦和轿车司机就走。
“别担心,让她休息休息。”周四平对马悦说,“一会儿我再去请她。”
周四平把两位客人带到射击区。马悦果然尚武,一听枪声就兴奋不已,按捺不住。
“给我那支枪!”他说。
周四平请教官立刻做出安排,让自己的职员撤出阵地,站在马主任身后,看这位老兵是怎么玩法。马主任也不谦让,接过一支冲锋枪,噼里啪啦拉动枪机,东看西看一番,装上弹匣,站直身子,端枪就打,一眨眼功夫打掉了十发,又快又急的振耳枪声迫使后边的一些观众用手捂住耳朵,环绕靶场的山谷嗡嗡嗡传响着急射的回声。
不一会儿报靶的就用步话机从靶区报告说,十发子弹全部命中,打了个八十九环。
“没打好,”马悦还不满意,骂道,“妈的。”
人们一起鼓掌,请马主任再露一手。
这时周四平已经离开射击区,坐到一旁的轿车里。
“我知道你在盘算是不是下车走开,”他对俞怀颖说,“我要劝你忍一下,这条路挺远,没法走。由于安全的缘故,靶场通常远离人口密集区。”
“我想办法把你请来,是想跟你说几句话,我当然得说完再走。”
周四平对俞怀颖说,他是想对她提一点建议。他认为俞怀颖非常能干,特别地执着,在她卓有成效的努力下,关于含远楼遗址保护的动议已经形成声势。周四平认为俞怀颖下一个动作应当做得更大一些,除了通过新闻媒介、学术团体和社会组织继续扩大影响外,应当考虑让更多的人关心和注意这个问题,眼睛即要向下,又要向上,下即面对百姓,上即影响更高层次的人物来关心支持。最好能采用一种影响面大,又比较有新意能让人产生深刻印象的活动,办这种事可能要有所投入,要花钱,这一方面,如果俞怀颖需要,周四平愿意尽量给予帮助。
俞怀颖显得相当惊讶。
“你这是什么意思?”她说,“这就是你的比较有新意的做法?”
“我这人有时自命不凡,忍不住就好为人师。”周四平自嘲道,“我总想教人怎么动手打架,独独没想到接下来该是自己鼻青脸肿。”
“也许不光鼻青脸肿。”俞怀颖说。
“难道你还非要我把命赔上?”周四平说,“我总认为咱们俩不应当是对头,咱们为的不是同一座楼吗?应当一起对付那个洪承宗才对。”
“那你为什么不退出去?”俞怀颖说,“你不要去折腾什么重建,你这种仓促应战的重建能搞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你应当把那块地交给我们,哪怕你开个价。”
“我要是图钱早把自己卖给洪承宗了。”周四平说,“我有我自己的道理。”
周四平说他曾经非常盼望出人头地,现在他发现有些事比出人头地更有意思,例如在某废墟上重修一座古楼。一个人一辈子里能够参与的有意思的大事充其量一两件而已,他这一辈子做的最有意思的事可能莫过于此,他怎么能放弃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反过来劝俞怀颖放手。他说他总觉得不可理解,如果俞怀颖真对那座古楼感兴趣,她应当希望有人把它恢复起来,而不是希望那里依然是一堆破烂。
“为什么非要把它抓在自己手里,跟逛传街娘们紧紧抓着自己的小钱包似的?”
俞怀颖冷冷道:“跟你一样,我有我自己的道理。”
周四平不觉叹气,说:“看来你就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