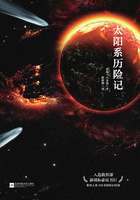好啦,我承认我卑鄙好不好?你说。我苟活,我没有良心,我活得像只猪。其实我本来就是畜牲,不是吗?你看,我会嚎(你重新表演你嚎叫的样子)。我像畜牲一样光着身子,我全身溃烂,你看,你看。我在人群中畜牲一样活着。既然畜牲都能做了,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你不也是野兽吗?
是的,我是。她说。所以我要你把她杀了!
你一惊。
我要你把她杀了!她又说。
她?你一惊。“她”不就是她自己吗?
有她没我,有我没她!她说。
这到底怎么了?她是在说梦话?可是她手里确实地拿着你们家的器皿。也许她并不是网上的那个“她”?你瞧她那令人憎恶的样子,哪点像网上那个她?
嵇康:我老婆让我杀了你。
毒药:好啊。
我是说,我老婆要杀了你。你重复一遍。
那就杀吧。她说。说得那么平静。
我也想谁把我杀了呢。她又说。有时候都想自己把自己杀了。
她蓦然说。
我不要。你说。
为什么?
我不舍得你。
谢谢!她说。
怎么会说“谢谢”呢?你想。我们好好过!你说。
在这里?
你无语了。自从你们走上了虚拟,就没有真实起来的可能了。自从走上了虚拟,你最好的梦就只能在虚拟中。
她笑了。何况这里是假的。她说。
是啊。这假的。虚拟是假的。假的又有什么关系呢?哪怕是演示一千次的死。
来吧。她说。你把我杀死了,你就可以跟你老婆好好过下去了。她几乎是在诱惑。
也许需要这么一种仪式。你想。用什么杀?你问。
用枪。她说。举了举她边上的枪。你瞧见了那把北京买的玩具枪。她居然真带回来了。
好吧。你说。现在来吧。
现在?她居然问。
还要等什么时候?你反问。
当然不。她说。她把枪伸向镜头。
那枪就跟真的一样,那么有实感。你只看见过一次真枪,不是在学校军训的时候,军训的时候,你装病逃脱了。你是在长安街上看到的。当时你往一辆军车上送水,在一个战士推辞你的时候,你悄悄摸了那杆真枪。那感觉至今不忘。你感觉到自己羸弱,你猛然萌生出小时候才有的念头:我要一把枪!
你迟疑了。
怎么了?她问。
挨枪仔是很痛的。
那是爽。她说。嵇康!她忽然叫。
你一愣。
你不是叫嵇康吗?
对了,你把自己的名字给忘了。是的。什么事呢?
你说,嵇康为什么非死不可?
你愣了。他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了呀,他非死不可了。
可是他几乎逃过了呀。你看哦,三千太学士为他求情。听说司马昭已经点头允许了,说只要他辩解跟吕安案没有关系,就赦免他。可是他就是不说。三千太学士求他:你就开个口吧!只要开开口就行。刽子手也说,只要你开个口,我就当做听见了你在申辩了。他说:拿琴来。
你:琴?
她:演奏《广陵散》呀!
你:噢。
那是因为痒。她说。太痒了。辛苦荼毒。药已经失去了作用。老子说,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他身上已经长满了虱子。
你也有吗?
是的。满是虱子。啃着我的肉。她亮出了她的阴处。我好痒!
似乎真的满是虱子。
快!快拿出你的枪来!她叫道。
我的枪?
你不是有枪吗?
你明白了。
对准了。
你感觉自己把枪瞄准了她。
把这块肉整个打烂,打焦!她说。
你忽然心头一紧。你摇摇晃晃了起来。你瞄不准那聚满虱子的洞。你害怕瞄准了。
你笑了起来:唉,这不是假的吗?她不是在玩吗?那边的她拿着那玩具手枪。那算什么?过家家?真正的枪在我这。
你想自己太紧张了。你想喘口气。要打也可以。反正是假的。要不是假的,还下不了这么大的决心呢!为了痒把自己射杀。
蓦地,她开枪了。
你听到了声音。似乎并不是从MIC上传过来的,而是从门外。或者说,你最初只是看到枪口冒了一下烟,没有出现子弹弹回来挂在枪口上的情形。也没有声音。一会儿,声音从门口缓缓传了进来。
你愣了。
她没有倒下去。也许是我听错了。你想。
是的,我弄错了。那根本是一支玩具枪,不会这么响的。没有威力的。可是,我怎么能肯定她不会偷梁换柱呢?
但是至少我还是弄错的,至少在床上。那不是我妻子。你瞧她动作那么轻柔。她从来没有这么轻柔。她一直是个女强人。她是另一个女人。不,她不是我的妻子。她是别人。那个毒药!我们在这里玩。你笑了。
你的笑猛然停住了。好像被当头一击。好像没有准备死的陪绑者,猝然被宣布执行了。很多念头顷刻间被一笔勾销了。
可是你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准备的。你于是又有点终于到来了,圆满了的感觉。你感觉自己的心在变硬。
我爱上你了。你说。
居然!居然感觉爱了吗?你感觉自己好像在追赶着什么。追赶在她生命完结之前。
奇怪,当你们时间很多的时候,你没有这感觉。你只觉得时间太多。
她问:你真的爱我吗?
是。你答。
那你就再给我一枪!她说。
好!你说。你又进入了她。射。
还很痒。你再给我一枪,好吗?她说。
她的手已经提不起枪了。
好。你说。
你射了。
再给我一枪,好吗?她又说。
她哀求着你,那声音像风,要刹那间被拉断了似的。
好。你进入了她。射击。
好像有虱子往深里跑了!她叫,看到了吗?
看到了。你说。你又开了一枪。
又往更深里去了!
你又更深入进去。你把我串起来了!她说。就像小孩的棒棒糖一样。像拨郎鼓。我感觉要飞起来了呢!她说。我要飞起来喽!我很轻很轻……我要再高一点。
再高?
再上一层楼。
你笑了。好。
我要进洞房。她说。
你一愣。进洞房?
我要告诉你呀,她说,你还欠着我呢,你还没有把我抱进洞房。
你想起来了,八年前,结婚那晚上,大家走后,她曾要求你把她抱进洞房。你说,我好累。
有时候形式是决定性的,一个问候,一个吻,一朵花,一个搂抱……女人是喜欢被抱的动物。可那时你却想:我累了,你又不是没有脚?你也应该懂事了。人其实不能太懂事,就像阴道不能太涩。
其实那时候你已经没有兴致了。所以结婚,只不过是了却一件事,或者还有给她一个交代。几乎所有男人都这样,所以婚后总是竭尽全力能敷衍就敷衍。也许也是从那时起,她就看透了你。她就开始折腾,开始打造幸福。
现在你后悔了。你感觉自己是欠她了。我抱你进去。你说。
你要补偿。虽然你很累。现在是真的累了。
我好幸福呢!她说,我的脚没有了,我感觉不到我的脚了。以前我的脚真可怜,一直负载着身体的重量。
你瞧见她的脚,晃晃荡荡,像截瘫了似的。还挂着鞋子。
她的手攀着你的脖子,软绵绵的,像不中用的牵牛花藤。好像很放心地把自己交给了你。假如你这时候撒手,她一定会摔得很惨的,你想。但是你没有。也不可能。因为她其实是被你的枪串着的,像棒棒糖。而不是你的手。
你完全可以停止,退下。可是你不能自已。你又开了枪。
你喘息着。你的气呼得我好痒。她说。
是吗?你更重地吐气。
我已经无能为力了。你做吧。你欺负我吧!你的心可真狠,力气可真大。我感觉又升上去了。上二楼了吗?
是的。你说。
我们的洞房就在二楼吗?
是的。你觉得不够吗?
那虱子又往里上面跑了。跑到全身了,酥麻酥麻的。她说。在抓我呢!我听到《广陵散》了。
《广陵散》?
她简直是女鬼,诱惑着你。
你没有听到吗?它是最好的药。比我赢多了。听到了?嵇康。
嵇康:听到了。它在上面。
你已经不是自己了。
毒药:上去?
嵇康:上去。到三楼了。
毒药:再上去。
嵇康:四层。
再……
五……
再……
六……
十,十五,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太高了……
嵇康:你害怕了吗?
毒药:不害怕。
嵇康:我也不。
你感觉已经没有退路了。你太累了。要是在平时,你早就一头倒下了。可是今天,你能坚持。
这是最后的斗争。把一生的积蓄都支出来用了,包括透支。
毒药:到了吗?
嵇康:到了!你看到了一片白色。白色的床。你看到了吗?
毒药:看到了。那是琴。
嵇康:琴?
毒药:你的琴呀!
嵇康:噢。
毒药:可以躺下来了!你把我的鞋子脱下来。
她的鞋子在她脚尖一翘一翘地。
嵇康:晕!
女人毕生就喜欢鞋子,穿鞋子,脱鞋子。你欠着身子去替她脱鞋子。
毒药:脱了,就要躺下去,琴弦就断了。就无可挽回了。你可要想好了,你要跟我结婚吗?
你笑了。当然。你说。你忽然又不甘心起来。为什么要躺下去?为什么要琴弦断?我们为什么不能好好相爱?为什么不能永远弹下去?
毒药:不可能。
为什么?我知道我错了。
你没有错。
你也错了。
我也没有错。是时间太长了。什么样的弦都要撑散的。
鞋子磕的一声掉了下去。
又磕的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