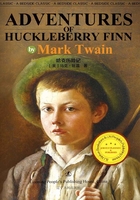阿强失魂落魄地往家里走着,他没有想到老太太会连夜从乡下跑回来!
她一定又有什么鬼主意了!这个老太太已经疯了,弄不好,势必把公安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小楼里的秘密就再也藏不住了。
女人啊,女人,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她们往往在关键时刻坏了男人的大事!
已经快要走到家门口,阿强突然气急败坏地站住了。他愣了一下,猛一跺脚,又掉头往回走。
今晚必须把藏在朱家的东西统统转移出来,然后,放一把火,让一切都化为灰烬。不论是何水水还是老太太,留着她们都是祸根!
阿强匆匆忙忙地跑到古董店里,翻出一桶备用的汽油,又找到一只装古董的空纸箱。
他料定那个发了疯的老太太肯定会对何水水下手,她那拙劣的手段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灭口的绝好机会,就让公安认为是老太太杀人后,又与被害者同归于尽了吧。
形势急转直下,发展到这种地步,是阿强没有料到的,他真不甘心就这样把从前已经习惯了的日子全盘毁掉,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性命要紧,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反正朱超民也不打算回来了,朱家的灾难都是他一手导演的,却要我阿强来收拾残局!丢他老母!
阿强忙完了准备工作,头上的汗水已经流了下来。透过隔壁墙,他听到朱家小楼里一片死寂,整个水东街也是一片死寂。
老太太的计划进行得怎么样了?可以动手了吧?
阿强觉得时机已到,他提起那堆东西,出了古董店的门。
他走出了几步,又返回去仔细锁好门,这才大步绕过小楼,朝朱家大门走去。
黑暗中,他试着推了推门,虚掩着的大门马上轻轻地开了。
阿强站在门口犹豫不决,他对里面的情况心中没底。
小楼的争斗到底谁占了上风?是阿清还是何水水?而这个打开门走出小楼的又是谁呢?
不论是谁,都不能影响自己的计划。
阿强闭了一会儿眼睛,适应一下室内的黑暗,很快就摸进了储藏室。
他并不开灯,而是将一只微型手电筒放在一旁,照着墙角的一个小洞。然后,轻轻拉动一个隐在墙角的小小机关,将手里的一只大塑料纸袋对准了那个地方。
满头大汗的阿强从储藏室里出来的时候,手里搬着两只沉甸甸的大纸箱。
他把纸箱放在大门口,才一点点地往楼梯口挪过去。要让火势从楼梯口迅速往楼上蔓延,每个窗户都安有防盗网,即使那两个女人察觉了火情,也无法逃离小楼。
阿民,对不起你了,这不是我的错!你不该这样对我,我对你一向忠心耿耿……阿强一边往楼梯上倒汽油,一边在内心嘀嘀咕咕地为自己开脱。
整整一桶汽油完全洒在了楼梯上,他慢慢退到大门口,几乎毫不犹豫地打着了打火机。
在微弱的光线里,只见一个人影儿站在二楼走廊上,正在看着他,白色的脸忽隐忽现……好像是老太太,又像是何水水,更像死去的阿素。
阿强打了个寒战,他抬起手正要将燃着的打火机扔到汽油上去,一声“别动!”在他的耳边响起,拿打火机的手腕被一只铁钳般的大手从后面死死扭住,他拼命想把那一星火苗扔到楼梯口去,没有成功。
客厅里顿时被几只手电照得通明,他听到一阵混乱的脚步声,等他明白过来,两只手已经被凉冰冰地铐得结结实实。
市公安局缉私科成员已经在水东街度过了第十个蹲守的日夜。
阿蓉虽然不是天天跟班,可是也已经熬了三天三夜,她正坐在距离朱家不到五十米的东新桥头一辆面包车里打盹。
“看!有人出来了……”坐在面包车里昏昏欲睡的阿蓉,突然被耳机里传来的报告声惊醒,她马上坐直了身体。
“是刚才进去的老太太么?”
“不是,是一个男的!”
“一定是阿强!先不要碰他,跟上……”
“明白。”
阿强匆匆忙忙从朱家逃出来,立即引起了阿蓉的警觉。她派了一个人跟上了阿强,自己带人上去敲朱家的大门。
楼里虽然只剩下两个女人,但是据她掌握的情况,老太太具有相当大的威胁。
虽然何水水一直不肯将朱家的情况如实反映给她,可是阿蓉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基本掌握了何水水进入朱家前后的情况。
月初从云南进入本市的一批重达几十公斤的海洛因,现在就藏在朱家。朱家老太太和何水水都可能是知情人,而这个阿强,就是这批货的中转人。
朱家大门关得死死的,里面似乎传出微弱的声音,阿蓉耐着性子敲门,如果里面没有特殊情况,一定会有人来开门的。如果万一有什么意外,就要撞门进去。
几分钟过去了,楼内突然传出一阵激烈的搏斗声和猫的叫声,接着,“砰”地一声巨响,便静了下来。
“不好,撞门!”阿蓉果断地下了命令。
何水水被疯狂窜上来的老太太死死抱住,她本能地想抵挡住这股突如其来的冲击,无奈两人的体力差距悬殊,瘦弱的何水水很快便支撑不住,她身不由已地往走廊的边缘靠近,眼看就要从栏杆上翻倒出去。
一瞬间,阿素坠楼的情景仿佛重现。她无法知道当初的阿素与老太太之间是否也有一场力量悬殊的恶斗,但她却知道自己此刻想干什么,她有一种强烈的挣扎的欲望。
恍惚中,一楼大厅暗红色的大理石地面隐隐地在她眼前摇晃着。
她不甘心,难道自己注定要变成第二个阿素,也要在朱家小楼里不明不白地死于非命么?
不!谁也别想再来摆布我了!我已经受够了……
可是,紧箍在她身上的阿清,沉重得好似一头大像,她再也没办法与这个邪恶的老太太拼力气了。
何水水细细的脖子突然猛地弯了下去,像一只小小的长胫鹿低头啄咬停在胸前的蚊虫那样。几乎在她闻到一股令人作呕的浓烈汗臭的同时,就听到老太太发出一声绝望的低吼。
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在危急时刻,牙齿竟成了最好的自卫武器……
老太太毒蛇一样纠缠在何水水身上的肉滚滚的胳膊,突然被狠狠地咬了一口,遭到重创,脚下顿时失去重心。
她似乎早已做好了准备,在倒下去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往楼下大厅方向倾斜过去。
何水水被一股力量裹挟着,也不由自主地朝栏杆滑倒。
她听到“砰!”地一声巨响,里面似乎掺杂着肢体断裂的声音。奇怪的是,自己的脑子仍然是清楚的,她这时才注意到自己被吊在走廊的栏杆上,两只手几乎失去了知觉,却仍然死死地抓着栏杆上的横木……
这情形和她踩翻了楼梯板那次是多么相似啊,可这一次情况远远比那次严重得多,只要她手上的力气耗尽,等待她的只能是和阿素一样的命运。
“救命!”她不由得发出一声嘶鸣,那陌生的声音太微弱了,刚一出口就被阴森森、黑洞洞的老宅吞没。
又是两声“嘭!嘭”的闷响,她听到身后的大门“哗啦”一下打开,有脚步声匆匆地跑进了客厅,阿蓉的声音传来:
“快救人……”
何水水就像一个极度困倦的跋涉者突然被放在了软绵绵的席梦思上,立刻陷入了香甜的梦境。她只觉得脑子晕晕的,一片朦胧,就失去了知觉……
二楼走廊距离大厅地面三米多高,体积庞大的老太太落地后当场毙命。
阿蓉看着小楼里的惨烈场面,突然感到深深的自责。如果掉下去的是何水水,那将给她留下终生的遗憾。何水水的安危,不仅是一个朋友的安危,说不定还是这个案子的关键。为什么不早一点儿向她公开身份,取得她的配合呢?
经过这一段的观察,她深信这个纯朴的四川女人是不会介入这桩犯罪活动的,只是因为虚荣和盲目信任,才陷入如此被动的局面的。
刚刚手忙脚乱地把何水水救下,阿蓉就接到了跟踪阿强的警员报告,称阿强又回到了古董店。几个人立即将老太太的尸体抬走,清理现场,就地埋伏在小楼内,等待阿强的再次上门。
果然不出阿蓉所料,阿强又窜进了朱家,暗中埋伏人员将他的全部举动尽收眼底,人赃俱获。
家中连续两天没有人接电话了,朱超民内心不禁慌乱起来。
现在他就在广州,离家只有咫尺之遥,可是却没有办法联系到家人,这就是干这一行的悲哀。
她们都跑到哪里去了?怎么连一个看家的人都没有留下?
一种不祥之感涌上了心头。
出于安全考虑,他离开云南的时候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多年来,他已经习惯这样,出动前从来不同下面的人打招呼,甚至不同自己的助手打招呼。往往到了深夜,他们会接到他从某个港口或某座城市打来的电话,通知说他已经到了某个地方了。
至于什么地方,谁也不问,问也没用,这是不成文的规矩。
这一次他到广州是为了谈一笔大生意,对方是来自内地一个制药集团公司的人,跟他谈一批兴奋剂的原料供应问题。
接到这个情报,朱超民感慨不已:看看人家!住在内地的大城市,坐在摩天大厦的写字楼里,老婆孩子一家人团团圆圆,却可以打着国营制药厂的旗号制毒贩毒!日子过得多潇洒!
他强烈地为自己这种东躲西藏、人不人鬼不鬼的“地下党”生活感到自卑自怜。冲动之下,真想回一次家,见一见何水水呀!可是这念头一出,他立即把自己臭骂了一通:
你不要命了!在H市,还是越少露面越好,不要感情用事!
到了广州的第二天晚上,见过制药企业的接头人,谈好了条件,刚回到住处,朱超民就躲在房间里用手机跟云南方面联系。
与云南的话刚讲到一半,手机上就显示又有一个电话进来了。是那家制药集团的人又来电话,请他到郊区一家有名的酒楼去吃夜茶:
“听说那里的田鼠肉味道不错,在内地找不到这种东西,能不能赏光陪我去尝尝啊?”
“对不起,我现在还有些别的事情,实在脱不开身……”朱超民狡猾地回绝道,他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轻易到处乱跑的。
“啊……您真的不能来?”对方好像很失望。
收了电话,朱超民忧心忡忡地反复把玩着那只小巧的手机,打不定主意是否该再给家里打个电话,正犹豫间,响起了有节奏的敲门声。
“谁?”朱超民飞快地把枪抓在手上,挂着保险链打开了一条门缝。门外站着一个漂亮的服务小姐,她手中的托盘上放着一封信:
“先生,您的信。”
“哪里来的?”他警觉道。
“是总台送来的。您自己看吧。”
他伸出一只手把那封信拿到手,立即关上了房门。
打开用胶纸小心封得严严实实的信封,里面掉出来的只是一个用潦草的字迹写成的纸条,上面有一行字让朱超民看了触目惊心:
快走!有人已经在注意你。
朱超民以闪电一样的速度把那纸条揉成一团,眨着惊慌的眼睛,边穿衣服边整理随身携带的手提箱。
不管这纸条是谁写的,此事是不是子虚乌有,他都不能再在这家酒店过夜!赶快换地方!
他给自己下了死命令,听了听门外的动静,然后悄悄打开了门。
还好,夜已渐深,走廊里没有客人。
两部电梯,一部在楼上,一部在一楼,他将两部电梯都叫了,以便哪部先到就坐哪一部。
一部电梯很快就从最底层上来了,他听到“叮咚”一声停止的示意铃,一颗心才算放了下来,只要进了电梯,很快就可以出大门,一切就又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了。
可是电梯是往上去的,而且里面还有两个客人。稍一犹豫,他就决定了:不管他,只要进了电梯就安全多了!想着,他一步迈进了电梯,回过头面对走廊,还好,没有异常情况。
电梯一层一层地往上升,朱超民突然感觉到双臂一阵麻木,身后那两个人已经死死地压在他的身上,他想掏出衣袋里的枪,已经不可能。
他本能地要抬起脚来挣扎一下,只觉得脑袋“嗡”地一声,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所谓内地制药企业的人,其实就是广东警方的缉毒人员,狡猾的朱超民终于在最后关头百密一疏,把自己送上绞刑架。
朱超民在广州落网的消息传到H市公安部门的时候,何水水还在病床上挣扎。伤势稍有好转,她就会沉浸在对他的思念之中,可是他的电话却无论如何也打不通。
对于她来说,他就像一个幻影一样,在这个世界上闪现了一下,便永远地消失了,可是他这不负责任的短暂出现,却给无辜的何水水一生蒙上了永难磨灭的阴影。
躺在医院病床上,吊着药水瓶的何水水,看到阿蓉眼里怜悯的神色,就六神无主,不知又会有什么灾难临头。
“我是不是要被判刑?”
“那要看你都做了些什么,你要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否则,就像从前一样,我还是帮不了你。”阿蓉的话没什么感情色彩,可是她不自主地躲避着何水水的眼神儿,让何水水感到阵阵绝望。
“他们……朱家的人,真的做了违法的事情了么?”何水水想着这一切,如同梦中。
“我已经跟踪了阿强几个月了,还有你。”
“你一直在跟踪我?你并不是阿兰的朋友,你在骗我们?你和朱家的人一样,也在骗我?”何水水的脸色很白,一丝血色也没有。
“我和他们不一样,他们在害人,也在害你;我是为了保护你,保护那些因为吸毒而丧失了一切的人们。”
“可是你早就应该告诉我……”
“那时候还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害怕告诉了你,会给你招来杀人之祸……”阿蓉掉过头来,直直地看着何水水的眼睛,“我们这一行的工作太难做了,常常遇到像你这样,天真善良却专门帮倒忙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么?”
何水水的眼珠突然涩滞不动了,阿蓉这句话让她费了好一会儿功夫才弄明白。她叹了一口气,心想,自己认识了这个阿蓉,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呢?
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与朱家的这场婚姻,给她留下的只是一场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