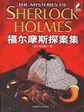火炕烧得很热,炕上铺着父母生前用过的被褥。他看着这一切,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他躺在炕上,双手枕在脑后,闭上眼睛,父母的音容笑貌一齐浮现在脑海里……就在这个土炕上母亲生下他。
转眼到了春节。队伍发了饷,破例放假十天。陕籍官兵都纷纷回家去过年,跟家人团聚。墩子无家可归,颇觉无聊。雪艳也说在队伍上过年实在乏味。要他一同去青庙镇看望看望姑姑,顺便在姑姑家过个年。墩子一想也好,便答应了。腊月二十八他俩去了青庙镇。
雪艳姑家待墩子如贵客,礼貌周全,毕恭毕敬。墩子反而觉得别别扭扭,浑身不自在。毕竟人地生疏,他有一种寄人篱下之感。破五儿一过,他婉言谢绝雪艳姑家的一再挽留,执意要回岐凤。
回到岐凤,队伍里上上下下纷纷传言,元宵节一过,队伍就要开拔河南。墩子半信半疑,去找张副官打探消息。张副官和太太回家过年还未返回。他闷闷不乐,回到住处喝闷酒。如果队伍真的要开拔河南,他考虑还要不要在队伍上干下去。
队伍开拔的消息属实,春节前命令就到了师部。孙蔚如的三十八军调驻陕西,孙蔚如兼任省府主席。新二师调防河南,归汤恩伯部管辖。接到命令后李信义十分不快。西安事变后,西北军成了蒋委员长的眼中钉肉中刺,此次调防实际上是瓦解西北军,可军令不得不服从。汪松鹤自然明了他的心思,多次劝慰他:“师座,大势所趋,你也不必为此愁眉不展。到了河南咱再图今后之计。”
李信义摇头叹气:“咱们本来就是杂牌子,又出了个西安事变,往后哪还有个出头之日。”
“这也难说,事在人为嘛。”
“唉,你我都不是黄埔学生,老头子不会重用咱们的。”
“师座说得极是。我也一把年纪了,想归隐山林。”
“松鹤兄,咱俩想到一搭去了。官场上的事我已经很烦了,不想再争啥高低了,想过一过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日子。”李信义哈哈笑了起来。汪松鹤也笑了。
李信义忽然问道:“西秦永平镇徐云卿一家被害一案查明凶手了么?”
汪松鹤说:“从情报处搜索到的情报来看,不是土匪干的。”
“那是啥人干的?”
“那天晚上下大雪,凶手没留下什么痕迹。但从火力装备来推测,可以肯定是罗玉璋的保安团干的。小股土匪是炸不掉徐家的炮楼的。”
“又是罗玉璋!”李信义在桌上砸了一拳,“前几日我去省城见到赵要员。他再三叮嘱,要我尽快破获此案,对凶手严惩不贷!他的女婿死于非命,老头子的火气大得很。”
“尽快破获此案谈何容易。现在我们只是推测,还抓不住罗玉璋的任何把柄。”
李信义愤然道:“罗玉璋在西秦为非作歹,为所欲为,实乃十恶不赦!不除掉此人,我这个师长就白当了,也愧对家乡的父老乡亲,更对不住对我耿耿忠心的陈楞子。”少顷又说:“姓罗的官居保安团长,也算是地方父母官,如此胡作非为,与土匪何异!长此以往,老百姓怎能安居乐业?”
汪松鹤说道:“用此种如狼似虎的人治理地方,只怕越治越乱,民不聊生。如今政府和军队里此类人比比皆是,这是党国的悲哀啊!唉,你我位卑,不管也罢。至于地方上的事让地方去管吧。我们即将开拔,无暇顾及此事。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罗玉璋多行不义必遭天谴。”
李信义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松鹤兄说的也是。只是赵要员那里咋交代?”
“实话实说吧。此案一时半时难以查明,部队奉命开拔在即,无暇查明此案,请他移交地方处置吧。”
“唉,也只能如此。”少顷,李信义说道,“离陕之前我想回家乡一趟。”
汪松鹤知道李信义双亲都已亡故,家眷子女都在省城,随口问道:“不知师座老家还有什么亲人?”
“还有一个叔父,两个堂弟,其余都是子侄辈。驻防岐凤以来总想回家看看,却戎马倥偬,抽不出空来。此次离开陕西,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
“师座早就该回家乡看看。李老大人恐怕已到古稀之年了?”
“叔父七十有五,是我父亲唯一的弟弟。小时候他十分疼爱我。”说到这里,李信义有点动情了。
“那就更应该回家看看。师座,松鹤也想去府上看看,不知尊意如何?”
“欢迎!欢迎!”
“咱们几时动身?”
李信义略一沉吟:“明天吧。”
“那我去通知张副官,作作准备。”
“不用了。回自己的家扎的啥势,耍的啥威风。”
……
翌日清晨,岐凤通往西秦的官道上有一队马队,约十余骑人。走在最前边的两匹马一白一红,白的似雪,红的如火炭。白马背上是李信义,红马背上是汪松鹤。两马并辔而行,马背上的人都着便装。李信义头戴红狐皮帽,穿一令貂皮大氅,颇似富商。汪松鹤头戴高筒皮帽,穿一领宁夏羔羊皮袍,似教书先生。紧随其后的骑者是张副官,墩子和十几个贴身侍卫,一律都着便装。
虽然节气已过立春,严冬的余威还在逞能。小北风呼呼地刮着,把天上的浮云挂得无影无踪,扬起的尘土把青蓝的天涂抹得灰蒙蒙的。刚出东山的太阳似一个没上火色的烧饼,一团惨白,不冒一丝热气。路两旁稀疏的几棵白杨古槐当风抖着,树枝随风呼啸。北风肆虐了一个冬天,虽然带来过一场大雪,却不等积雪消融就把它风化干了。高塬被折磨得千孔百疮,贫瘠的土地满目疮痍,狰狞丑陋,不见一点绿色,苍凉寂寥。田野上寒霜一片白茫茫,缺少水分的麦苗失去了应有的绿色,蔫巴巴地缩在地缝里。李信义目睹这一切,在马背上长叹一声:“去秋以来一直少雨雪,倘若今春再无雪雨,秦地又是一个灾荒年啊。”
汪松鹤也道:“战乱不止,灾荒连年,最苦的还是老百姓。”
“松鹤兄说的极是,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两人信马由缰,指点江山,感慨不已……
太阳渐渐升起,朔风稍歇,天气暖和起来,田野上出现农人劳作,有了生气。李信义心情开朗起来,用马鞭遥指起伏的山山峁峁,说到:“松鹤兄,北国风光不及你们江南水乡好吧。”
汪松鹤是何等精明之人,见师长心情好了起来,自然不能扫他的兴,笑道:“江南水乡虽说秀丽,却不及北国风光雄浑苍莽,有大丈夫的气概。”
李信义哈哈笑道:“松鹤兄果然高见。这里是古周原地,是尧舜时期后稷教民稼穑之区。《诗经》云:”周原?,堇荼如饴。说的就是这地方。这一带曾是古战场,商、周、秦、汉、隋、唐各朝各代都在这地方交过兵。周从这里兴起有八百年天下,秦、汉、隋、唐以此地为根基拥有关中而统一全国。你看,这里东有漆水水断崖,西有千河相护,南有滔滔渭水,北有乔山为屏,抵御外族实为能攻能守之地。“
汪松鹤连连点头,恭听李信义夸家乡的佳处。
李信义用马鞭遥指远水近山:“这里前挹太白之秀,后负周原之美,东控平原,西带长川,襟渭带,三水环绕,是块风水宝地啊。”
汪松鹤环目四顾,满目黄土,苍凉寂寥,看不出有什么优点,可嘴里还是说道:“好地方,果然是好地方。”
李信义言犹未尽:“松鹤兄,康海你可知道?”
“可是明代写《中山狼》的状元公康对山?”
“正是此人。松鹤兄知道他是哪里人吗?”
汪松鹤摇头。
李信义笑道:“康海就是这地方人。说近乎点,和我是乡党。有句俚语:”公公刘瑾把权专,陕西连中二状元。其实这是以讹传讹,冤屈了康海。康海天资聪颖,敏而好学。相传朝廷派出巡按到了这里,县衙老爷为巡按接风洗尘,宴席设在一豪绅的花园里。巡按见一花盆养的佛手壮实可爱,随口吟道:“佛手伸手要甚。这是一句联句,因为是触景生情,质朴中藏有奇巧,一时无人答对得上。当时康海和几个同学在河里耍水,有同学慌慌忙忙跑来,说是巡按大人发下题来,先生叫大家快去答对。康海他们回到学堂,见先生和几个同学正在抓耳挠腮苦思冥想,便问巡按出的啥题目。先生说,叫对对联,佛手伸手要甚。康海说这有何难,咱对他个花椒睁眼望谁。”
汪松鹤赞叹一句:“对得妙!”
李信义笑道:“还有更妙的呢。巡按听到康海的对句大为惊奇,忙把康海传到县衙。康海见到巡按不惊不惧,上前施礼问安。巡按见他小小年纪,一身秀气,喜欢得不得了,当即又给康海出了一个联句”是三更打五更更鼓不同。这是个笑话,西秦上阁寺有口大钟,由一位老道看管,举报时辰。每夜一更,钟敲一响,二更钟敲二响,其他更次以此类推。偏偏巡按到来的这天晚上,老道不慎将三更敲了四响。等他清醒过来寻思道:“我刚才多敲了一响,不如再敲一响,算是把刚才多敲的那一响撞消了。结果弄巧成拙,三更被敲成了五更,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笑话。巡按大人以这个笑料藏典,编成联句,新奇高雅。要对得像个样子,实在很不容易。在场的不担干系的人听了乐得直笑,一些舞文弄墨的人听了直瞪眼,暗暗替康海捏把汗。康海略一思索,昂头高声诵道”南六斗北七斗斗星各异。在场的人齐声喝彩,巡按也高兴得捻着胡须直点头,连声夸赞:“才子,真才子!松鹤兄,你以为这个对句如何?”
汪松鹤赞道:“果然对得奇妙。”
李信义又道:“他写过一首过河诗,更是清新有趣。”
汪松鹤笑问道:“师座,这恐怕又有什么典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