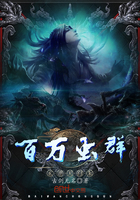洪武八年。
夜。
初春四月,更深露重,冥莫万寂。
星夜微光透过御书房的雕栏红木窗徐徐洒落,金陵城外的紫金山匍匐在一片灯火如豆的繁华辉煌之后,显得愈发静谧深沉。
朱元璋负手木立窗前,凭栏眺望。月色,星光,灯烟火气映在他棱角分明,有如刀刻斧凿般的脸上,仿佛失去了应有的光华,皆化作一抹浓雾散不开,寒光照不透的沉冷苍白。
月稍冷,夜渐沉。
这位天下新贵,不世帝王的心非月非夜,此刻却犹胜月冷,较夜更沉。
今夜,他要下一个决定,做一件事。这个决定就像是千万牛毛针芒刺在心头,令他不得不揪起心,咬碎牙,忍受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惋惜和势在必行,顿足颔首。同时,他也明白这件事情一经开始,再无回头悔路。无论之后影响狭广,牵扯巨细,臣论民议,终将和今夜一起成为永远的秘密。
——即使提及也无法道破。
“重八,你当真非杀刘伯温不可?”
说话的一个女人,生气的女人。
有人说女人生气时别有一番韵美,可这个女人生气的时候非但不美,且横眉怒目,额现青筋,更胜男子。一张圆盘大脸鼓胀潮红,当真有几分义愤填膺的模样。要是有人现在去招惹她,黄缎凤袍下,那双逃过荒,从过军,踏遍万里江山的大脚保准会在那人脸上留下一个黑漆漆,惨兮兮的脚印。
这女人姓马,年轻时多被人唤作马姑娘。自从嫁人成家后,他家男人手下的兄弟、义子、义侄叫她作嫂子、义母、婶子。不过,现在所有人都称她为皇后——马皇后!
“重八,你可曾记得这大明江山是如何得来的?”马皇后道:“如果你忘了,我现在就提醒你。大明江山和你的帝位就是这些老兄弟和义子、义侄用血汗和泪换来的!”
她说:“洪武二年,‘鄂国公’常遇春死于柳川河,太医院对外的说法是突然暴毙。可朝野上下哪个不知道你早已对他心生间隙忌惮?一时间,流言四起,人人自危。如今,李善长、宋濂、吕昶等老臣均已年迈。蓝玉、杨宪、胡惟庸之流又陷党派斗争,不思报国,实在难成气候。刘伯温的才干你比我更清楚,正是朝廷不可或缺的治国良才。他若一死,你身边又还有何人可用?”
朱元璋不可置否,月光映在他疲惫的眼眸中,显得冰冷、肃杀。
“刘基的才干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朱元璋道:“所以他非死不可!”
他说:“一个这么样有才干之人如果生出反心,必将成为一个最可怖的隐患和敌人!”
马皇后因愤怒而涨红的脸忽然变得苍白如纸,声音颤抖道:“刘伯温......要反?”
朱元璋眼中疲倦顿扫,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刀锋般坚定冷峻的寒芒:“这个人即使对我再有用,也已决计留不得!”
圆月隐在乌云背后,沉入远处的紫金山。朱元璋的决定就像日升月落这般亘古不变的道理,一经下达,便是死令。马皇后知道这件事情已没有任何回旋商量的余地。
死令之下必有人死,这一次便落到了刘伯温的头上。
马皇后轻叹一声,道:“看起来刘伯温已见不到明日的太阳。”
朱元璋的声音冷的像一把出鞘寒锋:“或许,他连三更天的更鼓声都已听不到了。”
“梆、梆、绑”
——更鼓响过三声,夜至三更。
御书房的大门应声而开,一道短小迅捷的人影急行而入,行至朱元璋身前七尺开外,伏袍而跪,额首施礼。
“微臣参见皇上。”
来人又对马皇后叩头:“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御书房内并未掌灯,朱元璋已提前撤走了所有侍卫、小婢,好像就是在等此人到来。来人正跪在横梁和圆柱交织倒映下来的一抹漆黑阴影中,似乎已完全和黑暗融为一体。看上去,这个人仿佛就是从黑暗和阴霾里孕育而生的邪恶精灵。
如果他没有说话,任何人都难察觉此人的存在。
马皇后一向不喜欢此人,甚至厌恶。尽管此人每次见到她时皆是满脸堆笑,礼数有加。可是,这样的笑意有如一个怨毒的诅咒,邪恶的魔法。让她觉得脊背发凉,胸闷气堵,好像有千万根尖锐银针正从她每一寸皮肤,每一个毛孔中扎进血肉里。
朱元璋没有回应,转首向马皇后使了个眼色。
马皇后和朱元璋乱世而结,盛世而伴。在二十几年的风雨患难里早已形成了一种快速有效的默契。这种默契有时只是一个不经意的眼色,一个细微的动作,甚至可以是一声稍重些的呼吸。马皇后立时会意,退出了御书房。再三确认过窗户是否关的严实,大门是否已闩牢之后,才一步三回首的缓缓离去。
——她知道接下来的谈话决计不能让第三个人听到。
黑暗中的人影一动未动。他下跪的姿势并没有什么特别,任何人下跪的时候好像都是这样子的,却给人一种异常顺从、唯诺的感觉。这个人仿佛生下来的时候就已跪着,生来就是给别人下跪的,好像只有下跪的时候才能将他生命的价值,生活的意义体现出来。
——朱元璋需要的岂非就是这样的人?
“你来做什么?”
黑暗中的人影跪的更低,身体几乎已贴住地面:“复命。”
“复谁的命?”
“自然是皇上的命。”
“我何时给你下过命令?”朱元璋道:“下的又是什么样的命令?”
“两个时辰前,皇上命微臣赐毒‘诚意伯’刘伯温。微臣深感圣恩,不辱使命。如今,刘公已毒发身亡,微臣自然要回到这里,向皇上复命。”
“什么?”朱元璋忽然拍案而起,眼中布满腥红血丝:“大胆胡惟庸!”
他说:“诚意伯告病在家,我实在担心,这才命你连夜赐下灵药。你却为何自作主张,将‘灵药’换成‘毒药’?你竟敢毒害朝廷重臣,到底是何居心!”
胡惟庸闻言已骇的失色,连连将头磕的掷地有声,回荡四壁:“皇上明鉴,微臣冤枉啊......”
他本来还有一大堆自辩之词要说,却忽然停住,硬生生咽回了肚里。因为他已明白朱元璋的意思。
“冤枉?”朱元璋冷冷道:“这件事难不成是我让你去做的?”
胡惟庸此时恨不得磕碎御前青砖,把头埋进地下:“微臣实在不该妄自揣测圣意,毒害刘公......”
朱元璋不等他把话说完,抢道:“这么说,你已承认这件事是你所为?”
“微臣有罪!”胡惟庸几乎要哭出来:“微臣罪该万死啊!”
朱元璋脸上掠过一抹难以觉察的笑意。与其说是笑意,其实不过是嘴角的肌肉快速抽动一下而已。这样的笑意本来就不是笑给别人看的,而是笑给他自己看的。
可是只要不是戴着面具,出现在脸上的表情就会被别人看见。他是不是知道胡惟庸一定已看见了这一抹笑?他是不是故意笑给胡惟庸看的?他是不是要让胡惟庸觉得自己对他这一次的行动很满意?
“胡惟庸啊胡惟庸!”朱元璋叹了口气,好像当真无比沉痛又惋惜不已:“你说我该如何治你的罪?”
“死罪死罪,微臣纵百死也难谢其罪啊!”
“你纵然死上千遍万遍,诚意伯也无法死而复生。”朱元璋重新坐回那张红木雕龙椅,说道:“你这条贱命难道抵得上诚意伯的命?”
胡惟庸连连摇头,又连连磕头:“抵不上,自然是抵不上的。非但抵不上,简直相差千万里。微臣这等庸才又如何敢于刘公比肩。”
“既然如此,我要你的命来又有何用?”朱元璋道:“前几日,你的老师李善长欲告辞还乡。推荐你出任中书省丞相一职,我并没有否决。你觉得这样的‘处罚’行不行?”
胡惟庸闻言,直将额头磕出‘咚’一声巨响,待得再抬起来时,额前已是腥红一片:“微臣惶恐,微臣何德何能,怎敢任此要职?还请皇上收回成命,另谋他选。”
朱元璋眯起眼,青冷的目光有如一支雕翎利箭:“你当真不想做?”
胡惟庸又将头重重的磕下去,却不敢再抬起来:“微臣万死不敢!”
“既然如此......”朱元璋淡淡道:“那就以后再说吧。”
“没有以后!”胡惟庸正色道:“微臣只愿做一名马前卒,殿前仕,为皇上效死,便已知足。拜相之事还请皇上切莫再提。”
朱元璋终于满意的点了点头。他知道这件事胡惟庸已准备一力承担下来,无论今后过去多久,就算有人用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他也一定不会把这件事的起因、经过、细节,包括今夜此地的谈话告诉给第二个人知道。
当一个人拥有了绝对的权利,尚无法断定下属对自己是否绝对忠心时,不妨恩威并施,先施“威”予以震慑,再施“恩”以安抚。当所施之“威”慑心寒胆,所予之“恩”又大于“威”时,那么他的下属一定会对他绝对忠心,纵然效死于他,也无怨无悔。
——这个道理朱元璋还未成为皇帝之前就已明白。
朱元璋在笑,冷笑。
朱元璋的笑有时候就连和他最亲近的马皇后也看不懂。
他好像真的在笑时,眼中却无半点笑意。他冷笑时,神情反而比任何时候都轻松、愉快。
——所以说,要看一个人是喜是悲,是怒是怨,一定不能看他的笑。笑,有时候也是人类武装自己,迷惑别人的一种有效手段。
“既然你不愿接受这么样的‘处罚’......”朱元璋顿了顿,继续道:“那便退下吧。”
他说:“刘基之事未结束以前,我不想再见到你。但是,如果你的家丁和仆从、小婢只要有一日未曾见到你,我就有一千种法子把你的头颅从脖子上取下来。我说的话,你最好牢牢记住!”
胡惟庸回答的时候已站起身来,躬着脊背,额首向后退去:“微臣遵旨。”
他转身行出御书房大门的时候,衣衫早已被汗水浸湿,掌心和额前因为恐惧、后怕,依旧在不停的渗出冷汗。胡惟庸长叹一声,惊魂未定,就像在黄泉路上,鬼门关前走了一遭一样,方才只要有一句话说错,此刻他或许早已是个死人。
现在,他虽然还活着,却已成了替罪羔羊。并且,在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日子一定不会好过。这件事情还未发生之前,朱元璋已在他的府邸中安插了内线。对于他的这位主子,这位帝王的手段,胡惟庸一向知道的紧。
胡惟庸行过一段洒满月光的青石长廊,又走入了一片不见尽头,漆黑空洞的黑暗之中。初春四月,御书房前的院子里桃花开的正好。据说这是马皇后专门差人从江南的某个地方转栽过来的品种,其他地方是看不着的。
胡惟庸却觉得,今年的桃花妖红异常,有如刘伯温死前吐出的那一串腥红血珠。
雕窗又开,窗外有月,圆月无光。
望着胡惟庸渐渐消失在黑暗中的背影,朱元璋终于看到了满院的桃花。
他曾经很喜欢桃花,他也知道,这些桃花是马皇后从江南一个叫青田的地方转栽过来的。
——青田就是刘伯温的家乡。
桃花依旧笑春风,他的眼中却为何会有泪花?
——这一切不正是他想要的结果?
桃花的红,有如朱元璋心头的血。他攥了攥手中一本已有些破旧的黄封小册,对月长叹:“伯温哪......我的挚友......”
——这位不世帝王,终于在这个月冷花开的夜晚,落下了一滴永远不会有人知道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