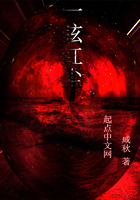横戈儿的血将流干,意识已逐渐模糊。可是,他要让通通儿活,他只有一次机会。
这一刀绝不容出现任何错误和偏差,他已毫无保留的豁尽了最后一丝力气。
只听得“呛”一声龙吟,刀出鞘,刀光暗红,有如久已风干的血迹。
四周立刻陷入一种深沉的寂静,风止于空中,雪停在檐前。沧海桑田,日月星辰,浩渺时间,仿佛已永远停顿在这一刻。
你一定没有见过失去了天地、日月、时间的世界,所以你想象不出它的样子。
世间万物仿佛堕入了一种深沉的长眠。长眠,下坠,却不知要坠向哪里,只知道那一抹暗红色的刀光好像已切断了人与世界的所有联系。
没有人能够形容这一刀的速度,仿佛只是回眸时的一望,转身时的诀别。
眼神和诀别又怎能用速度来形容?
这一刀徐如春风,静如山岳,就像是情人的纤手,仿佛还带着一种淡淡的花香。
开相护只觉这双温润软香的情人手拂过他的额头,正从他的脸颊一直抚摸到脖子。
他忽然微笑,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诡秘。他只觉心里愉快极了,就像是刚喝下了朋友的心头血。
然后他就看见了自己的脚。
每个人低下头,都能看见自己的脚。他却是从脚开始看上去的,先是腰,接着是肩,最后是脖子。
脖子上已无头。
他想不出他的头去哪了。
就在这时,他看见自己的身体倒下去,倒在血泊中。
这一刀来的徐,落下时却快如眨眼。所以,开相护的头颅落地时还没有完全死去。
假如你眨了眨眼,头就不见了,你想不想得通?
开相护脸上的微笑已凝固,最后一丝生命的气息已随风雪飘向远方。
多么温柔的一刀,多么可怕的一刀!
人呢?
刀光逝,刀入鞘。
风动,雪落。
天地、日月、时间仿佛又回到了世间,横戈儿的胸膛又在流血。
他还没有倒下去,他还活着。
他望向通通儿,通通儿当然没有走,此时也正在望着他。
二人相望、流血、大笑。
他们都还活着,活着可真不容易。
这件事终于结束了。
日落,月升。
有时候,结束即开始。
这件事结束了,另一件事却已悄然开始。
街口卖红薯的少年依旧在笑,身后却站着个穿斗篷,戴雪笠的瘦高个。街心摆面摊的寡妇似乎很高兴,她的摊位前终于来了个吃面的紫面大汉。街角屋檐下的乞丐几乎要哭,因为,一位白衣翩翩的女子刚刚把一锭银子放进他的破碗里。街尾捏泥人的小老头正在和一位书生打扮的公子攀谈,那书生手中正把玩着一个泥娃娃。
谁都没有注意过这一切是何时发生变化的,但是请你一定要记住这四个人。
因为,下一刻,这四人无论在做什么,已同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向着横戈儿急掠而至。
就算横戈儿还有力气发出第二刀,也一定反应不过来。他流了太多血,思维和身体的机能已处在崩溃边缘。
他实在伤的太重!
所以,四人,四指,以一种意想不到的角度,用一种巧妙精绝的吐劲方法,点住了他身上四处要穴。
横戈儿只觉一阵晕眩,便已昏死过去。
四人得手,沾地即起,掠至通通儿身前,拱手下跪,齐声道:“使者安。”
通通儿“嗯”了一声,眼中又泛起了那种忧愁:“你们来了。”
那书生打扮的公子道:“使者的伤要不要紧?”
通通儿点了点头,道:“嗯,很好,看得出来你很关心我。”
那书生居然脸色一红,微笑道:“使者的安危自然马虎不得。”
通通儿忽然冷哼一声,道:“既然你想知道我的伤是否要紧,为何不在自己的胸前也刺一刀?”
书生脸色一变,立时跪了个五体投地,声音已有些颤抖:“属下......属下惶恐......”
通通儿道:“一个人还知道惶恐,总算是不错的。”
他忽然用一种阴冷的目光盯住书生,冷冷道:“你既自觉惶恐,为何还不把小七和那姓横的救回去?”
末了,他淡淡的加了一句:“姓横的要是死了,方才恐怕是你这辈子最后一次惶恐。”
书生哪里还敢多言,急掠而出,一手背起雷时七,一手夹住横戈儿,渐渐消失在雪雾中。
他看起来弱不经风,简直像个书呆子。力气却不小,雷时七和横戈儿加在一起少说有三百斤,他依旧健步如飞,雪地上只留下一排浅浅的脚印。
此时,那白衣女子忽然取出一个印着梅花的瓷瓶,倒出黄色粉末,敷在通通儿胸前伤口上。
她算不上绝美,却也标致动人。娇容云鬓,秀鼻小口,一双乌亮亮的大眼睛,有如两颗璀璨夺目的黑珍珠。
“还是你好。”通通儿望着书生远去的背影,淡淡道:“我最讨厌那种光说不做的人。”
白衣女子轻轻的“嗯”了一声,低下头去。
通通儿伸手去摸她脑后的发髻,一头有如瀑布般乌黑柔软的青丝已披落下来。
白衣女子“哎呀”一声,把头埋的更低,好像已不敢抬头去看通通儿:“使者......你......”
通通儿笑了笑,道:“这样才好看。”
他说:“你的头发很美,为什么要将它盘起来?你一定要记住,女人的美是属于男人的,你生得这么美就是要让全天下的男人为你侧目,为你疯狂的。”
白衣女子双颊一片绯红,又轻轻的“嗯”了一声,手中忽然一抖,指尖已触及到了通通儿的伤口。
通通儿脸色一变,一字一字冷冷道:“还有一件事你也要记住。”
方才还是阳春三月的眼中已变成了隆冬腊月,他的声音就像隆冬的冰锥:“男人都喜欢女人,却不喜欢笨女人,更不喜欢做错事的女人。”
末了,他又用那种有如冰锥般的声音去刺白衣女人的心:“在我这里,没有人能错第二次,就算是女人也一样!”
白衣女子的手在颤抖,额前已沁出冷汗。
通通儿继续道:“听见了不回答也算是一种过错。”
“明白了!”白衣女子似乎怕得要命,几乎在尖叫:“属下明白了!”
通通儿满意的点了点头。
此时,那紫面大汉忽然站起来,他似乎早已有话要说。
“使者。”谁都听得出他声音里强压着的怒火:“为了那姓横的,七哥几乎丧命,值得吗?”
通通儿淡淡道:“你知道的,这是‘时那日亚’的意思。”
紫面大汉握了握拳,脸色已变成了一种盛怒的紫黑色,大喝一声:“首领糊涂啊!”
白衣女子和那一直没说话的瘦高个立时跪了下去,这四个字仿佛带着一种诡秘可怖的魔法。
通通儿眼中闪过一丝怨毒的阴鹜之色,叹了口气,道:“你知道我不会武功的,我的声音也一定响不过你。”
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出现,使者的位子早已落在你头上。我知道,从那时起你就怨上了我,怨上了时那日亚。”
紫面大汉似乎想反驳,通通儿已接着道:“你怨我,瞧不起我,想怎么样对付我都成。但是,你实在不该说时那日亚半句坏话。”
这句话说完的时候,紫面汉子已倒下去,喉头插着一柄短小雪白的小刀,连一滴血也没有流出来。
这一刀实在太快,刀入皮肉,血将并涌时,刀身已全部没入,将原本要流出来的血封了回去。
这柄刀原本刺在通通儿胸膛上。
那张已开始发白的紫面上凝固着一种惊惧之色,他至死也想不到,眼前这个不会武功的少年居然有这么快的出手。
通通儿叹了口气,道:“我知道你与小七素来交好,我实在不忍心杀你的。”
他忽然去问跪在地上的二人:“你们说我做的对不对?”
二人点头。
他们都知道摇头的后果是什么。
通通儿淡淡道:“你们认同我的做法,就表示你们对时那日亚尚算忠心。”
他对二人说:“这是他的福气,也是你们的福气。”
他转头对那黑斗篷,戴雪笠的瘦高个道:“我知道你一向不喜欢说话。”
瘦高个点头。
通通儿道:“‘多说多错’这个道理并不是每个人都明白的。这一点,你做的很好。”
瘦高个沉默。
通通儿继续道:“所以,时那日亚才会这么样看重你,才会要你去做那件事。”
他问瘦高个:“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
瘦高个终于说话了,只说了两个字:“明天。”
通通儿点了点头,仰面望天。
下雪天的傍晚是看不到夕阳的。
他忽然长叹一声,道:“看起来,今天就要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