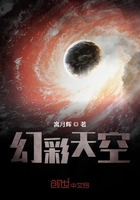如今,于尔根已经放弃了他的左派政治观点,坚决拥护帝国达成的一切——国家又运转起来了——无人失业、食物充足、全民康泰,民族自尊得到彰显。新的岗位、新的道路、新的工厂、新的希望——他说,除了帝国,还有什么能够带来这样的成就呢?然而得到这一切的代价,是要接受一个仿真的新宗教和一个狂暴的假弥赛亚。“什么事都是有代价的。”于尔根说。这次代价似乎未免太高昂。(厄苏拉时常好奇他们究竟如何做到了这一切。必定是抓住了恐惧心理,借助了剧场技巧。但这么多钱和工作岗位又是哪儿来的?也许仅仅来自旗帜和制服的需要就基本拯救了国家经济?“本来德国的经济就在复苏,”帕米拉说,“纳粹只是幸运地揽上了这个功绩。”)是的,他说,的确,不能忽视存在暴力,但这只是一瞬的痉挛和浪潮,是纳粹冲锋党前进路上不可避免的牺牲。现在所有人、所有事都已趋向理智。
四月,两人去柏林参加了为元首五十岁生日贺寿的大型阅兵式。于尔根在嘉宾大看台上获得了几个座位。“一种赏赐,我想。”他说。可他做了什么事,元首要“赏赐”他?她不明白。(他为此高兴吗?有时不容易看出来。)1936年他没能弄到奥运会的票,然而现在,他们却与帝国的VIP们比肩而坐。这几天他总是很忙。“律师从来不睡觉。”他说。(然而在厄苏拉看来,律师们都在为能一睡千年、高枕无忧而努力。)
阅兵式长得仿佛一辈子,堪称戈培尔策划的最成功的表演。军乐不断后,纳粹德国空军分中队保持阵形沿东西向飞越勃兰登堡门,献上震耳欲聋的序曲。更多的喧嚣与狂暴。“那是亨克尔和梅塞施米特。”于尔根说。他怎么知道?哪个男孩不了解飞机?他反问。
接着是无尽的兵团高踢正步沿路经过。厄苏拉看着他们,想到了撩起大腿跳舞的女子舞团。“Stechschritt。”(德语:正步走)厄苏拉说,“这走法究竟是谁发明的?”
“当然是普鲁士人。”于尔根笑道,“还能有谁?”
她拿出一板巧克力,掰下一块给于尔根。他皱着眉摇了摇头,仿佛她的行为表现出了对面前军事集团力量的不恭。她又吃了一块。这是她小小的抗议。
他凑近来让她听见——人群正爆发恼人的骚动——“不看别的,至少这整齐划一值得你钦佩。”他说。她钦佩。她的确钦佩。兵士的动作异常精准。每个兵团都走得一模一样,仿佛机器人一般完美,仿佛出自同一条生产线,失去了人的感觉。然而,充满人的感觉,本就不是军人的任务。(“一切都那么雄赳赳。”她向帕米拉汇报说。)英国军队能把这样庞大的一个集体训练得如此机械性地一致吗?苏联政权也许行,但英国人从来都不那么善于服从。
庆典才刚刚开始,她膝头的弗里妲已经睡着。整场阅兵希特勒都在行礼,手臂高举身前(从他们坐的位置上,她有时向他的手臂瞥一眼,它仿佛一把火钳)。权力显然能给人一种异于常人的耐力。假设过五十岁生日的是我,厄苏拉想,只要在泰晤士,在布雷、亨利或附近任何一处河岸办一个野餐,一个非常英式的野餐——热茶、热狗酥皮卷、鸡蛋西芹三明治、蛋糕和松饼。画面中家人都在,但于尔根是否也属于那片闲适的欢乐?他应该会融入得很好,穿法兰绒划船裤,斜靠草坪与休聊着板球。两人曾见过面,相处很融洽。1935年,他们曾去英国,回了一次狐狸角。“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休说,虽然听说她入了德国国籍,显得不很高兴。她现在明白,入籍这一步走错了。“事后洞悉力真伟大,”克拉拉说,“如果我们在事前就都有它,便无须写什么历史了。”
她便会留在英国。会留在狐狸角。留在草地、树林,留在小溪潺潺、铃兰花开的地方。
战争机器的队列轰隆隆滚来了。“那是坦克。”第一辆由几部拖着驮在背上的panzer(德语:坦克)映入眼帘时,于尔根用英语说。他在牛津念过一年书,英语很好(也因此懂得板球)。后续panzer(坦克)陆续驶来,跟着是带跨斗的三轮摩托,装甲车,骑兵英姿飒爽地挟行两侧(马队最受观众欢迎——厄苏拉唤醒弗里妲,叫她看马),接着是炮兵连,有轻型步枪、重型地对空迫击炮以及巨大的加农炮。
“那是K-3。”于尔根语气里有欣赏,仿佛觉得她能够听明白。
整场阅兵显出对秩序和几何图形的偏爱,这令厄苏拉难以理解。阅兵在这方面与过去其他的阅兵式和集会——充满舞台效果的表演——没有区别,但这次的备战气氛较往常浓烈得多。那么多武器——国家除了牙齿什么地方都武装到了!厄苏拉不知道他们竟有这么多武器,难怪每个人都有工作干。“莫里斯说,要想拯救国家经济,不打仗是不行的。”帕米拉写道。造这些武器必然是为了战争,不然它们有什么用呢?
“重整军事力量,是拯救全民身体素质的手段。”于尔根说,“它帮助我们重新获得国家荣誉感。1918年大帅投降时……”厄苏拉不再往下听,这席话她已经听过许多次。“上次战争是他们发起的,”她怒气冲冲地写信给帕米拉,“战后却弄得仿佛只有他们受了苦,只有他们忍受贫穷饥饿,只有他们遭遇家破人亡。”弗里妲再次醒来,心情很糟糕。厄苏拉喂她巧克力。厄苏拉的心情也不好。两人你一口我一口,把一板巧克力吃光了。
阅兵式的尾声居然很感人。各兵团将士身着各色军服,在希特勒的看台前组成好几排整齐的色块——横平竖直,队伍的边缘仿佛被刀片裁过。整体躬身向他致敬。人群激动得发了狂。
“你觉得怎么样?”他们拖着脚步往外蹭时,于尔根问。弗里妲坐在他的肩头。
“雄壮。”厄苏拉说,“非常雄壮。”同时感到太阳穴处,一次头疼正在缓缓酝酿起来。
弗里妲的病是几周前早晨的一次发烧引起的。“我不舒服。”弗里妲说。厄苏拉贴了贴她的额头后发觉汗津津的,于是说:“你不用去幼儿园了,今天跟我待在家里吧。”
“热伤风。”于尔根回家后判断。弗里妲的肺一直不好(“得了我母亲的真传。”希尔维阴沉沉地说),因此两人已经习惯了感冒流涕喉咙痛等症状。但这一次,感冒恶化得十分迅速,很快弗里妲的体温起来了,整个人疲弱下去。她的皮肤贴上去仿佛就要起火。“帮她降温。”医生说,厄苏拉就在她的额上敷冷毛巾,给她讲故事,然而弗里妲无论怎么努力,都提不起听的兴致来。紧接着,她陷入了错乱状态,大夫听了她的胸音,说:“这是支气管炎,等一等就退了。”
那天晚些时候,弗里妲突然恶化,两人将几乎纹丝不动的小身体用毯子裹住,乘出租车送往最近的一个天主教医院。对方诊断为肺炎。“小姑娘怎么病得这么重。”大夫说,仿佛责怪他们不尽心。
厄苏拉两天两夜不离弗里妲床侧,为了将她留在人世,一直握着她的小手。“如果我能替她得病就好了。”于尔根越过弗里妲身上浆得笔挺的雪白床单轻声说。修女们穿着兜头大氅,仿佛西班牙大帆船一般,鼓着风在病房里来回忙碌。厄苏拉走了片刻神时,顾自想到这些人每天早上不知要花多久才能穿起这套行头。厄苏拉自己肯定无法顺利穿戴那种东西,只会弄得一团糟。行头过于复杂,这本身似乎就是一项不当修女的好理由。
他们祈祷让弗里妲活下来。结果梦想成真。意志的胜利(原文此处为德语:Triumph des Willens)。危机过去了,弗里妲踏上复原的漫漫长途。由于虚弱、苍白,弗里妲亟待疗养,一天晚上厄苏拉从医院回到家,在门前发现一个不知由谁亲自放到门前来的信封。
“伊娃寄。”她等于尔根下班回来,给他看信封。
“伊娃是谁?”他说。
“微笑!”咔嚓、咔嚓、咔嚓。她想也许伊娃生来乐于助人。进山并不添她麻烦。伊娃好意相邀,不过是为了让弗里妲吸到山中的优质空气,吃到模范农场格兹霍夫生产的新鲜蔬菜、鸡蛋和牛奶。
“这不是圣旨吗?”于尔根问,“你能拒绝吗?你想拒绝吗?我希望你不想,而且留在山里对你的头疼病也有好处。”近来,随着他在部门里升迁,她发觉两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单边化。他判断,提问,自我回答,紧接着便盖棺论定,整个过程没有她插嘴的份儿。(也许这是律师行业的做法。)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这样有什么不妥。
“老山羊到底还是有女人了,不是吗?谁想得到?你以前知道吗?不,不可能,如果你知道你会告诉我。你竟认识她了,想想看!这对我们只有好处,不是吗?离王座近在咫尺。对我的工作有好处,也就是对我们有好处。亲爱的(原文此处为德语:Liebling)。”他例行公事般补上最后一句。
厄苏拉却觉得王座附近是一个相当危险的地方。“我对伊娃谈不上认识。”厄苏拉说,“我没见过她,是伯伦纳太太认识她的母亲博劳恩太太。克拉拉曾在霍夫曼的摄影工作室与伊娃一起工作过。她们以前进的是同一所幼儿园。”
“厉害。”于尔根说,“三步就从咖啡馆(原文此处为德语:Kaffeeklatsch)轻松跃到了权力中心。伊娃小姐知道她幼儿园的老友克拉拉嫁给了一个犹大吗?”她惊讶于他表达“犹太人”的方式。犹大。她从没有听他这样狰狞而轻蔑地说过这个词。她感到心里插进了一根钉子。“我不知道,”她说,“我不属于你所说的咖啡馆。”
元首占据了伊娃大部分的生活,他不在时,她便仿佛一个被抽空了的器皿。恋人不在时,伊娃每天晚上保持电话畅通,且像小狗一样,忧心地竖着一只耳朵,等待电话铃送来主人的声音。
山中无事可做。不多久,林中漫步和畅泳(彻骨寒冷的)国王湖变得叫人低迷,不再有焕发精力的效果。野花没有一直采下去的道理,在露台上的卧榻里晒日光浴,也总有快要发疯的时候。此处保姆奶妈成群结队,争相照顾弗里妲,厄苏拉发觉自己变得同伊娃一样,手中大把花不完的时间。她失策地只带来了一本书,幸亏书还算厚,是托马斯·曼的《魔山》。她不知道它是一本禁书。一个国防军军官见她在读这本书,说:“您胆子真大,您应该知道这是他们的禁书吧。”她心想,既然他说“他们的”,那他自己也许就不在他们之列。他们能怎么办?最多是从她手里把书拿走,扔进厨房灶炉里吧?
这国防军军官,为人相当和善。他说自己祖母是苏格兰人,说自己在“高地”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日子。
Im grunde hat es eine merkwürdige Bewandtnis mit diesem Sicheinleben an fremdem orte,dieser -sei es auch -mühseligen Anpassung und Umgew?hnung,她念着,吃力而拙劣地翻译着——“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它要求你去适应、去熟悉,这其中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说得多么真实,她想。曼的作品太深刻了。她多希望自己带了一箱布丽奇特的哥特浪漫小说。她知道它们一定不会被verboten(德语:禁止)的。
山中的空气(以及托马斯·曼的作品)对她的头疼病丝毫没有起到改善作用。她头疼得更厉害了。Kopfschmerzen(德语:头疼)_一词本身就叫她头疼。“我查不出您有什么问题。”医院大夫这样告诉她,“多半是心理作祟。”他给她开了一剂佛罗拿(佛罗拿(Veronal)是第一个商品化的巴比妥类药物。1903年至20世纪50年代中叶,巴比妥被用作催眠药)。
伊娃则没有任何文化消遣。不过,伯格本也不是一个云集知识分子的地方。唯一勉强有些思想的人只有斯佩尔。但这并不是说伊娃度日不用脑子,厄苏拉觉得情况远远不是如此。你能感觉到她生活热情的表象下,那种消沉和神经质,然而焦虑并不是一个男人希望在自己的情妇身上看到的东西。
厄苏拉想,为了做一名成功的情妇(虽然她自己没有做过情妇,无论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一个女人必须令人舒心、叫人忘却烦恼,恰似一个好枕头可以让疲倦的头颅得到安枕。Gemütlichkeit(德语:温馨)。伊娃友好,总是聊些无关紧要的事,从来不努力显得自己善思善辩。有权势的男人需要他们的女人毫无攻击性,家庭绝不能是思辨的竞技场。“我自己的丈夫也这么说,所以这一定是真的了!”她写信给帕米拉。虽然这番意思,他不是以自己为例表达的——因为他还没有权势。“至少目前如此。”他笑道。
政治世界对伊娃来说不过是一个将她的至爱夺走的东西。她被粗暴地隔绝于公众目光之外,不要说合法名分,甚至随便什么名分都没有,虽然她像狗一样忠诚,但狗得到的认可却比她要多。布朗帝的地位就比伊娃更高。她最大的遗憾,伊娃说,就是温莎王朝造访伯格霍夫时,她没有获准觐见公爵夫人。
厄苏拉听了皱起眉头。“但你知道她是个纳粹呀!”她脱口而出。(“我想我说话应该更小心些才是!”她写信给帕米拉。)伊娃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是呀,她当然是”,就再也不追究这个问题,仿佛英国一朝之君的妻眷是个纳粹党并没什么好奇怪的。
元首必须追随高贵、孤独的贞洁之路,他不能有婚姻,因为他已经与德国结合。他将自己献身给了国家的命运——至少概括说来如此。厄苏拉感到自己此时已经偷偷睡着了。(这是他晚饭后一次冗长的独白。)真像我们的伊丽莎白一世,她想,但没有这么说,因为觉得元首一定不希望与一个女人相提并论,即便这女人是个有着国王的心胸和胃口的英国贵族。上学时,厄苏拉曾师从一个很喜欢援引伊丽莎白一世的历史老师。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切勿将秘密告诉你没有试炼过其信仰、亦不知其能否守口如瓶的人。
伊娃如果留在慕尼黑,守着元首送给她的资产阶级小住宅,还能正常社交,一定更为快乐。身处山中这个镀金的牢笼,她只好自我娱乐,翻翻杂志,聊聊时兴发型、明星韵事(仿佛以为厄苏拉对这个话题也有了解),像表演快速换装魔术般一套套换衣服。厄苏拉去过几次伊娃的卧室,那是一个漂亮的闺房,与伯格霍夫其他地方的沉闷风格大相径庭,美中不足的是它的显要位置挂了一幅元首像。那是她的英雄。元首自己的房间里却没有相应地挂上他情妇的相片,在他墙上挂着的,不是伊娃的笑脸,而是他自己的英雄弗里德里希一世。伟大的弗里德里希(德语:Friedrich der Grosse)。
“我总是都把grosse听成grocer(英语:食品商贩)。”她写信给帕米拉说。当然,一般来说,好战而去征服世界的人,通常都不是卖吃食起家。元首获得伟大成就前师从何处?伊娃耸耸肩,她不知道。“他一直都搞政治,出生时就是政治家。”不会,厄苏拉想,他出生时不过是婴儿,一如所有人。现在的他是他选择的结果。
元首的卧室毗邻伊娃的浴室,别人无法进入。但厄苏拉见过元首睡觉,不是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卧室,而是在伯格霍夫午餐后的露台上,在阳光普照中。伟大武士的嘴皮玩忽职守,没有牵住,使嘴张开了,犯下了大不敬(原文此处为法语:lèse-majesté)之罪。武士暴露出弱点,可惜此地没有杀手,但有的是枪,随便一把鲁格,就能击穿他的心脏或头颅。可她自己怎么办?更重要的是,弗里妲又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