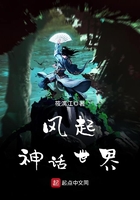在这边的那所院子里,王婉容的一夜未归当然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一大早,两眼红肿的徽宗便欲带领着郑太后、韦贤后、玉福及诸多嫔妃、皇子、帝姬们,去找斡离补要人;可恰在这时,那副将正好来到,大家便七嘴八舌地对着副将大吵大闹起来:
“王贵妃是你给叫走的,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你们把王贵妃弄到哪里去了?快快把她交给我们!”
徽宗以手势制止了义愤填膺的大伙儿七嘴八舌地呼叫,尽量压住自己胸中的火气,耐心地说道:“副将,昨天晚上是你把王贵妃给亲自带走的,现在到这般时辰了,还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们、你们到底还讲不讲一点儿人性啊?”
众嫔妃又禁不住一股脑儿地吵起来:
“你们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反正也活不成,就干脆集体自杀好了!”
“我们统统地集体撞头自杀了,看你们怎么给你们的主子交待?”
副将烦躁地挥挥手:“好了好了!你们要是坚决要人,那就给你们好了!不过,咱们首先说清楚了,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别吓掉魂儿了哇!”
众嫔妃闻言大惊:“啊,怎么,王贵妃真的惨死了吗?”
“那还有假!”副将直言不讳地应承着:“嗨,别看这细皮嫩肉的王贵妃娇娇娜娜的,发起疯来还真是厉害哪!居然拎起一把椅子想一下子砸死大元帅呢!可俺们的大元帅是何等地机灵啊,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哇,所以便转身来把她给一刀劈死了!呃,为了你们夜里不发呓症,我看,就别把尸体弄过来了,干脆在那边挖个坑埋了算了!”
“不行,我们一定要为她送行!”徽宗固执己见地说。
“对,她身为贵妃,我们要为她送葬!”郑太后和几个嫔妃齐声大呼着。
“那好,你们就稍待片刻吧!”副将这么答应着,即命令一旁的几个金兵:“去,把王婉容的尸体抬过来!”
几个金兵应声而去。少顷,他们用担架将王贵妃的尸体抬了过来。众人近前一看,立马被吓得尖叫起来!
啊,那是一个一劈两半的尸体!
众人皆伏在屍体上,呼天抢地地嚎啕大哭起来。
看着自己心爱的王婉容贵妃就这样地惨死了,心如刀绞、泪流满面、愤怒之极的徽宗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啊,婉容,你、你死得太惨了哇!你死得太亏了哇!我、我愧对了你呀!我、我愧不如死啊!”这么哭了一阵子,又回头看了看副将,怒不可遏地大吼道“哼,你们这些灭绝人性的东西,居然把人给一劈两半!俺、俺给您拼了!”这么叫着,便像一头发疯的公牛,蓦地一头向副将狠狠地撞去。
手疾眼快的副将急忙一躲,徽宗的头一下子“嘭”地一声撞在担架上,头皮立刻被撞得鲜血直流了。
郑太后立马命令吓呆了的玉福:“玉福,还楞着干什么?快快给你父皇包扎哇!”玉福缓过神来,立刻慌忙找来了纱布等物,同韦贤后一起给徽宗手忙脚乱地包扎起来。
泪流满面的郑太后又命令嫔妃们说:“大家都别害怕了,也别光顾着伤心难过了,反正人是惨死了!作为姐妹一场,咱们不能忌恨她生前的飞扬跋扈了,还要让她当个全尸之鬼,以求来世能托生一个完整的人啊!快,咱们贡献些衣物,把尸体合并一体裹紧,再用针线缝好,就可下葬了!”这么说完,首先自己脱了一件衣服。
哭哭啼啼的众嫔妃也纷纷脱下自己的一件衣服。
涕泪交流的徽宗和几个皇子赶紧把王贵妃的两片身体合在一起,用衣物裹紧。
众嫔妃纷纷啜泣着跪了下来,用针线缝着衣物。
一嫔妃顾影自怜地感叹道:“唉,王贵妃惨死了还有我们给她缝合尸体送葬呢,今后我们死了,还不知有没有人给忙活这些呢!”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长吁短叹、嘤嘤哭泣起来。因为想到了自己一片黯淡、吉凶未卜的前景,人人都不由得忧心忡忡、提心吊胆起来。
让我们把目光再转移到东路。
黄尘漫漫的河间古道上,被押解的宋人俘虏那长长的东路队伍缓缓地走了过来。
他们一个个蓬头污面、唇口干裂、形容枯槁,走起路来也歪歪斜斜、松松垮垮、步履维艰。
金兵挥鞭抽打着、吆喝着、叱骂着:“您们这些笨猪,怎么走得这么慢?这样跌跌撞撞、磨磨蹭蹭,猴年马月才能到达燕京啊!”
一名宫女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口渴难耐,便下意识地盯着一名金兵身带的水囊,伸手向那名金兵苦苦哀求道:“军爷行行好,给我一口水喝吧?俺渴得嗓子眼里都冒烟了哇!”
那金兵傲慢地用鼻子“哼”了一声,嬉皮笑脸地说:“我还有一泡尿呢,你喝不?”
那宫女低声骂了一句:“金狗不得好死!”
可这句话尽管声音很低,还是被那金兵听到了,他立马将那名宫女一阵蒙头盖脸地拳打脚踢。
那宫女被打急了,高叫道:“反正这日子也没法过了,俺给你拼了!”这么说着,就蓦地使劲向那金兵狠狠地一头撞去。可无奈她的手被长绳给拴着,尽管使足了气力,可她的头并未能撞到那位金兵。
一看这宫女居然反抗,那金兵狞笑一声:“哈哈,居然想撞死老子,与老子同归于尽啊!好哇,不想活了是吧?那老子就成全你!”说着,便残忍地挥刀一下子将那名宫女从长绠上砍下!可尽管人“啊”地一声蓦然倒在血泊之中了,可一条胳膊却仍旧晃晃悠悠地留在了长绠上!
众宋人看着倒在血泊中的那宫女,皆纷纷惊叫、痛哭起来。
不远处,被五花大绑着的月姑、丁信也看到了这惨不忍睹的一幕。月姑禁不住大叫道:“你们太灭绝人性了!太丧心病狂了啊!我要找粘木喝抗议!”
那金兵走过来,斜睨了一眼月姑,挖苦道:“你以为你是谁?你也撒泡尿照照,脸儿还有以前那么白吗!”
一看金兵肆无忌惮地辱骂自己的妻子,怒气顿生的丁信“呸”地一口痰吐在那金兵脸上,怒喝道:“闭上你的狗嘴!”
那金兵恼羞成怒了,立马恶狠狠地抡起鞭子,照着丁信没头盖脸地抽打起来。
被绑着双手的丁信根本无法招架和反抗,只有无奈地接受这非人的毒打和虐待!
一道道流着鲜血的鞭痕立刻挂在了丁信那英俊而刚毅的脸上!
不远处的钦宗看到了月姑、丁信挨打和受辱,亦大叫道:“不准打骂他们!不准打骂他们啊!我要找你们的大帅粘木喝,让他管管你们这些无法无天、滥施淫威的家伙!”
那金兵朝钦宗嗤之以鼻:“哼,重昏侯,你以为你还是皇帝吗?你以为我们的大帅会听信一个俘虏的话吗?”
“不管他听不听,我都要找他!让他管管你们这些恣意妄为、残无人道的家伙!”钦宗声嘶力竭地大吼着。
当天晚上,押解宋人的东路长队在河间府的一处院落停顿下来。
月姑、丁信被带进一间铺着麦草的小房子里。
一金将把蜡烛点亮,放在窗台上,又把二人捆绑着身体的麻绳解开,每人给发了一个大饼,一碗凉水。
月姑、丁信稍微活动了一下被绑痛了的臂膀,便饥不择食地吃起大饼来。
丁信一边吃着大饼,一边盯着月姑的脸和腹部审视,终于禁不住问道:“我从见到你就觉得不对劲儿,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也没好意思问,月姑,咱们的孩子——”
月姑闻言,忍不住,“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丁信着急地说:“别哭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月姑擦了一把伤心的泪水,啜泣道:“过黄河时,皇上和朱琏双双跳河自寻短见,俺下河去救他们,一不小心滑倒在甲板上了,所以——”
丁信闻言激动地抚摩着月姑:“唉,月姑,让你受苦受罪了哇!”
月姑亦与丈夫扑在一起,无限歉疚地说:“丁哥儿,俺知道您太想要孩子了!可又偏偏没能保住!”
“唉,国破家亡,人身无着,命运如此!这能怪你吗?”丁信安慰着月姑,而自己也不由得泪流满面了!
二人抱头痛哭起来。
门外的金将看到这感人至深的一幕,也多多少少良心发现,有点儿同情和怜悯了,便催促道:“喂,你们别卿卿我我地穷黏糊了,今个晚上有时间互诉衷肠,现在就快快吃大饼、喝凉水吧!”
二人只得和着倾流的眼泪继续吃起大饼、喝起凉水来。
少顷,金将看他们吃过喝过了,就走了进来,又动手捆绑他们。
丁信说:“怎么,这夜间还绑,让人怎么睡觉呀?”
金将解释说:“我也想给你们小两口儿一个顺水人情,不绑你们,让你们好好地睡上一夜;可你们不是一般的人,大帅特别地吩咐要绑紧你们!至于怎么睡觉嘛,你们小两口儿就商量商量呗!”
月姑感慨地说:“唉,想不到咱们两个人就这样度过一夜!也好,那就彻夜长谈吧!”
金将点了点头,阴阳怪气地说:“对对,你们难得一聚,好好地说说这些天的相思之苦吧!”这么说着,就把二人捆绑结实,又把门在外边锁上,这才哼着小曲儿走了。
听着金将渐渐地走远,月姑便悄悄地对丁信说:“皇上自从朱琏死后,更是心灰意懒,俺前几天才给他鼓上了劲儿,正在想着怎么采取行动呢,不想你们倒提前实施返航计划了!”
丁信闻言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实施了返航行动又有什么用?唉,天不佑宋,冤家路窄,偏偏在大名府码头,遇上粘木喝押送你们渡河哇!”
“唉,偏偏就这么事不凑巧,狭路相逢!”月姑连连扼腕叹息着。
丁信想了想,又说:“不过,咱们不能这么乖乖地被押送燕京,咱们还得想办法逃脱!”
“对,咱们逃脱了就伺机刺杀粘木喝,解救这些被俘同胞!”月姑补充说。
丁信闻言激动起来:“对,今天咱们俩能聚到一块了,恐怕这也是天缘相凑了哇!”
“那、那咱们就快快商量商量用什么办法才能逃脱吧?”月姑喃喃道。
丁信想了想,一时也没想出什么好的办法,就说:“反正一夜长着呢,咱们就慢慢地想想逃脱之计吧!”
二人巴眨着眼皮,陷入了沉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