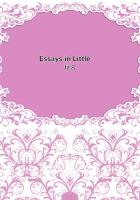傅深连连冷笑,“我的亲生骨肉,为何不能带走?安大人既是阁臣,想必精通律法,儿女是否应当跟随父亲?夫妇是和离也好,是义绝也好,母亲能不能带走孩子?”害我们父女分离十几年还不够,事到如今居然还想霸着我女儿不还。
“我必要讨还女儿,经官动府也在所不惜。”傅深越想越恼怒,大声说道。其实这样的家事若能私了,最好无声无息的私了。若是惊动了官府,于傅家、于安家,名声上都不好听。
谭瑛手脚冰凉。若是真到了官府,解语一定保不住了!无论律法,还是人情,都不允许母亲带走夫家的儿女。谭瑛眼泪潸然而下,安瓒替她拭去泪水,送她回了室内,“你且歇息片刻。”
安瓒再出来时,傅深脸上讪讪的,“哭什么,她霸占了女儿十几年,我便是接了解语回去,不过一两年的功夫,解语也该出嫁了。”一个是十几年,一个是一两年,谁吃亏谁占便宜?她占了大便宜,倒哭上了,真是的。
“我认识阿瑛以来,很少见她哭。”安瓒声音客气而冷淡,“我头回见她时,她已是濒临绝境,却没有一滴眼泪。”谭瑛不是遇事只是哭泣的女子。
傅深想到当年的曲曲折折,很是心虚,那是自己亲娘做下的好事!本来他对于谭瑛另嫁这件事痛恨已极,怒气冲冲的觉得谭瑛背叛自己,对不起自己。隐隐约约知道当年那些情事后,傅深退缩了,不敢回头看,不敢追究,不敢提起。他打个哈哈,顾左右而言他,“父女亲情总是隔不断的,是也不是?”再怎么着,我女儿你不能抢走。
安瓒淡淡看了傅深一眼,说道“傅侯爷说的极是,父女亲情是隔不断的,不管解语姓安还是姓傅,总归都是傅侯爷的亲生女儿。”解语就算继续在安家,还是你的亲生女儿。
傅深觉得这话听着很不对,又说不出哪里不对,一时有些发楞。安瓒客气的倒了杯茶递给傅深,“父母爱子女,则为之计长远。解语还未出生时,我和阿瑛已是千百遍想过她的将来。”
傅深重重把茶杯放在桌上,脸色铁青。“安瓒,你欺人太甚!我的妻子,我的女儿……”傅深按住腰间长剑剑柄,怒视安瓒。
“阿瑛性情高傲,当年她如何自艰难困苦中渡过,必定没有告诉过你。”安瓒神色坦然,“如今,我来告诉你。”有些事,不是你不去想,就可以当它没有发生过。这些往事不告诉傅深,他会一直逃避,却会一直纠缠。
傅深按着剑柄的手无力垂下。当年的事他听了一半,之后便不敢再听下去,“我不想听!不想听!”他心中叫着,却说不出来话,只一动不动呆坐着,一言不发。
“当年我扶着谭大伯跌跌撞撞赶到贵府,贵府太夫人和谭阁老的继室夫人,已把白绫横在阿瑛颈间,逼她就死。”安瓒的声音平静中带着丝愤怒,傅深面如死灰,“母亲说不曾想过要阿瑛的性命,她骗我的,骗我的!”傅深绝望的想道。
安瓒根本不理会傅深,自顾自讲了下去:谭大伯是个老实人,面对高贵端庄、义正辞严的傅家太夫人和谭阁老夫人,谭大伯根本不是对手。“这等败坏门风之人,留她做甚!”“便是傅家放了她,她还有脸活着么?”你一句我一句,夹枪带棒的抛了过来,谭大伯不懂得应对,只一口咬定,“我家阿瑛不是这种人”“她不会做这种事”。
普通女子到了谭瑛这境地,多多少少是会有些慌乱的,谭瑛一点没有。她扶着谭大伯,静静说了一句话,“大伯,我的嫁妆单子您那儿有一份,若我死了,请大伯把嫁妆收回,全部捐给谭家族学。”
谭瑛这句话一说出,形势马上不同了。之前是婆婆、继母一起逼迫她,之后变成婆婆一个人孤军奋战。继母和异母弟弟害她为的是什么?不就是那份丰厚的嫁妆么?若是嫁妆捐了给谭家族学,他们图什么。
继母和异母弟弟一旦闭了口,傅家太夫人一人孤掌难鸣,难以定下谭瑛的死罪,最后眼睁睁看着谭大伯带着谭瑛离开。等于谭瑛是用自己的嫁妆,换回一条性命。
黄豆大小的汗珠一滴一滴淌了下来,傅深握紧拳头,咬牙说道“她该到宣府去寻我,便是寄封信给我也好。”我当年不知道!若是我知道了,若是我知道了……
安瓒冷冷说道“谭大伯年龄大了,受了这一番惊吓,回到家便病倒了,连发几天高烧,梦中还一直叫着阿瑛的名字。阿瑛不眠不休,一直守在大伯床前。”哪有功夫去宣府,哪有功夫给你写信。
大伯慢慢好转之后,谭瑛又倒下了。大夫说“没什么大碍,怀了身孕之人,多多休养。”谭大伯知道谭瑛怀了孩子,知道六安侯府已是声称谭瑛“病亡”,又是愤怒,又想不出什么法子。
“大伯正愁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之时,傅侯爷回京了,还办了喜事。”安瓒定定看着傅深,一字一字说道。
傅深很有些狼狈,“家母身体欠安,要冲喜,要冲喜……”一边是“私通仆役”“背夫私奔”的妻子,一边是重病在床,需要冲喜的母亲,傅深毫不犹豫依从了太夫人,“好,我娶鲁姑娘。”反正谭瑛已经抛弃自己了。
“小玉是个机灵丫头,知道阿瑛怀了身孕,曾经在贵府门前徘徊很久,想跟傅侯爷通个信儿。”安瓒声音平淡,像在说跟自己不相干的事,“可惜傅侯爷是大忙人,她总是见不到。”小玉也算机灵了,却根本见不到傅深。
“大伯知道傅侯爷另娶,老泪纵横,一直念叼着‘阿瑛怎么办,她往后可怎么办’,大伯他老人家本来年纪就大了,身子骨也不硬朗。”安瓒声音冰冷,“阿瑛听闻阁下另娶,一个人坐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一动不动。”
傅深嘶哑着声音说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如果我早知道这些,自然不会娶什么鲁氏,这可恶的鲁氏。
“是解语救了阿瑛。”安瓒声音温柔起来,“她不知是伸小手还是打哈欠,触动了阿瑛。”也或许是饿了,在发脾气。是那一回胎动,唤醒了谭瑛。她捧着肚子,脸色慈爱,不复是茫然、无措。
“傅家,是不能回了。”谭瑛坐在大伯床前,声音很低,但是坚定、清晰,“莫说傅深已另娶,便是他光明正大接我回去,难保太夫人不使第二回毒计。真到了那时,难道大伯再来救我?大伯若不嫌弃,我便在家中服侍大伯终老。”谭瑛想得很清楚了,傅深绝不会拿他敬爱的娘亲如何,顶多整治几个下人仆妇出出气。自己若回傅家,还要仰太夫人的鼻息。那又何苦?分明是自寻死路。
至于腹中的孩子,谭瑛咬咬牙,“这是我亲骨肉,我定要抚养他长大成人。”谭大伯一迭声说道“那是自然,那是自然。”亲骨肉,自然要好生抚养,那还用说么。
这之后谭大伯做主把谭瑛嫁给了安瓒。一个是得意门生,一个是亲侄女,两人成亲后和和气所过日子,奉养谭大伯安渡晚年。大伯最后走的时候,拉着谭瑛的手,“阿瑛啊,阿瓒是个好孩子,会对你好的。大伯走了也安心啊。”
傅深只有苦笑,无话可说。算算谭瑛和安瓒成亲的日子,自己在做什么?远赴贵州,去追捕“奸夫”。太夫人跟他说了,“奸夫”是贵州人,谭瑛怕是跟他一起去了贵州。
在贵州好似有蛛丝马迹,却最终什么也没追捕到。之后这十几年一直在各地暗中搜索,只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到,原来谭瑛从没离开过京城。
“傅侯爷想不想把六安侯府,变成一个国公府?”安瓒轻飘飘问道。傅深疑惑的转过头,国公府?什么意思?安瓒微微一笑,把近来之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傅深跳了起来,解语进宫?这可不成!这丫头脾气死倔死倔的,只合嫁个听话识趣的有情人,舒舒坦坦过日子。进宫去服侍皇上?伴君如伴虎!一天到晚小心翼翼的,孩子不得憋屈死!
“你家邻舍那傻小子,就是他了!”傅深悲壮的说道“把解语嫁给他!”傻就傻吧,解语喜欢。唉,本来还打算接回家里养上两年再出嫁,如今看来是不成了。
本朝后妃一向选自民间,只有平民百姓才会风闻皇家要选妃,便急急忙忙胡乱嫁女儿,如今自己也沦落到这一地步了!圣上什么都好,只一点,要什么世家贵女做皇后,平民的女儿不好么?前面几代皇后,都是平民之女!
“贵府太夫人,若有孙女入主中宫,想必是乐见其成。”安瓒慢吞吞说道。阿瑛说过,傅深只要遇上太夫人,必会方寸大乱。这会子他顾虑解语日子舒不舒心,谁知回府后被太夫人一顿敲打,会不会改主意。
傅深呆了呆,“家母也是疼爱解语的,极疼爱。”该是不会吧?傅家的荣华富贵都是靠男子一刀一枪挣来的,犯不上往宫里送女儿!可太夫人行事往往出人意表,若她真想要解语进宫呢?傅深决定这阵子先不回家了,“安大人,速速定下亲事要紧。”先定了亲再说。
“如此,解语便在我安家出嫁。”安瓒神色温和,“傅侯爷以为如何?若认回贵府,不知又会生出多少波折。”傅家,你不当家,当家的是太夫人。
傅深犹疑许久,最后下定决心,“解语便一辈子做安家女儿!只一件,她将来生下儿女,须跟我姓傅!”太委屈了,亲生女儿没团聚过一天。
“这件事我代解语应下,”安瓒微笑道“将来不拘男孩儿女孩儿,总归是有一位跟着傅侯爷姓傅。”傅深心有不甘,怒道“我要男孩儿做什么?自然是要女孩儿。”最好跟我闺女小时候一模一样。
安瓒也不跟他计较,微笑着一一答应下来。送走傅深,安瓒回到房中,笑道“我说过什么?傅侯爷疼爱解语,必会为她着想。”细细说给谭瑛听了,谭瑛又开始哭——这回是高兴的眼泪。
郊外一片松柏林中。张雱素衣素服祭拜过亡母,岳培坐在坟前对着墓碑说话,“阿媛,你看看咱们雱儿,年纪轻轻做了大将军,多么威风!”“雱儿快娶妻了,过阵子我带儿子儿媳来看你。”
等到岳培说够两车话,父子二人方骑马缓缓离开。“爹爹您怎么才回来,”张雱抱怨道“等您等得急死了。”万事俱备,只欠老爹,偏偏老爹迟迟不归。
这傻小子哪里是想老爹了,分明是急着娶媳妇儿!岳培乐了,“无忌莫急,爹爹这便托人提亲去。”张雱认真的点点头,“是,要快。”岳培乐呵呵答应,“好好好,要快。”爹爹也盼着早日喝上媳妇茶。
“无忌陪爹爹回侯府可好?”岳培跟张雱商量,“你也该给祖母请安。”张雱摇摇头,“改天吧。爹爹,我这几日都在兵营练兵,没回过家。”
没回过家?那肯定也没有翻墙了?岳培笑咪咪说道,“那赶紧回家罢。无忌,明日我设宴请你师傅,请贴已送过去了。”
“他让我拜他做义父,我没答应。”张雱表功似的说道。岳培微笑,“无忌为什么不答应啊。”张雱答得自然而然,“我这不是怕您伤心么。”
岳培看看爱子,温柔说道“那有什么,无忌,爹爹便是盼着多个人疼你方好。”张雱精神一振,“您不反对啊?那他下回再说,我便答应他了。”
“答应他好了。”岳培笑道“他的伯府尚在修整,爹爹便把你邻舍买了,请他住下。无忌,到时你们小两口住在中间,一边是岳父岳母,一边是义父,可是不缺人疼爱了。”
张雱勒住马头,问道“爹爹,我两边的邻舍,您早就买下了?”哪那么巧,解语买了左邻,岳培还能买右邻。
“你们母子二人独居,爹爹哪能放心。”岳培叹道“左邻右舍住的都是爹爹心腹,暗中保护你们。”只不过沈迈实在厉害,还是让他劫走无忌好几回。
张雱张了张口,却是什么也没说出来。父子二人分别后,张雱快马回到当阳道,“天怎么还不黑?”他嘟囔过好几回,采绿端庄的走出屋子,随即笑弯了腰。
好容易等到天黑了,张雱还是不能翻墙:沈迈一白天都在外喝茶下棋,这会子赶巧回来了,看见张雱眉开眼笑的,“阿雱回来了?好几天没见你。”献宝似的拿出一盒酥点,“阿雱你不是爱吃点心么?一得阁的蟹黄酥,很有名的,很好吃!”
啰嗦了半天,沈迈才说了一句有用的话,“阿雱,我替你定过亲了!”张雱吓得跳了起来,“您替我定亲?”这是怎么话说的?
沈迈说话也说不大清楚,“反正是替你定亲了!跟安大人定的。”文渊阁的大佬们全都在场,这亲定的极好!听沈迈颠三倒四的说来说去,张雱皱皱眉头,“我去问解语。”翻墙去了邻舍。
这傻小子!沈迈跺脚。老子几天没见他,才见面儿他就去翻墙去!看着张雱施展轻功大鸟一般去了,又有些得意:这傻小子一身功夫,全是老子教的!
张雱到了邻舍,采蘩、采蘋恭敬行了礼,备好点心茶水,知趣的退下了。“大胡子,吃点心,”解语明显心情很好,“唔,这榴莲酥很好吃。”自己居然还记得榴莲酥的做法,居然还能做出来,难得,难得。
她怎么这般高兴?张雱害羞的想道,她也知道义父给我们定亲了?“哎,你也知道了?”张雱鼓足勇气问道。
“知道什么?”解语有些莫名其妙。“没什么,没什么。”张雱不好意思说出来,掩饰的端起一杯热茶,“真香,真香。”
“我高兴的事情是,”解语笑盈盈说道“今日悯忠寺的大慧禅师给一位姑娘卜了一卦,卦相上说,那位姑娘命格贵重,贵不可言。”这信儿一传出去,可就热闹了。大慧禅师可是世外高人,受人敬仰。
张雱剥了粒栗子递过来,解语吃了,“又甜又糯。”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盛。命格贵重,贵不可言,先传出这个信儿,过两天,自然会半遮半掩传得尽人皆知:那位命格贵重的姑娘,便是魏国公府的大小姐徐离。徐家,开国之初可是出过一任皇后的!
解语越想越得意,越想越乐呵。张雱脸红了,解语这么高兴!其实我也蛮高兴的,张雱负责剥栗子,解语负责吃,两人一个剥一个吃,配合十分默契。
徐离姑娘做了皇后!解语想到美妙前景,手舞足蹈,得意忘形。张雱又剥好栗子,她张开樱桃小嘴,张雱下意识的直接喂了给她。
解语笑咪咪,“真好吃,大胡子剥的栗子特别好吃!”张雱呆呆看了她片刻,突然起身走了,“太晚了,太晚了。”逃之夭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