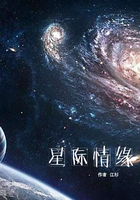留置室本来有马桶,但没隔成专门的卫生间。李二全尿憋了以后,不知何故,不敢往马桶里撒,全撒到裤裆里。他自己还想不声不响夹紧裤裆熬下去,直到裤子慢慢焐干。别的几个人稍微闻出些味道不对,揪他站起来一摸,发现他湿了裤子,简直乐不可支。鸭哥看不过去,大声地叫唤。一叫唤我就听得到。
“怎么撒裤子上了?不是有马桶吗?”
“我都不知道自己憋尿,也不知道几时撒出来的。”他声音拖着隐隐的哭腔。
“真有你的。关你两天,赶紧回去守着你爸妈,不要随便乱跑了!”
我把他弄出来,铐在值班室固定杆上,并叫连宝下来帮我盯一阵。我上去拿一身不会再穿的衣裤要李二全换上。留置室里没人,我指了指那里面。我后脚跟进去,这家伙还有点不好意思,迟迟不脱内裤。我龇牙一乐,突然间觉得自己像是他父亲辈的,还想在他屁股上拍一巴掌。“限你一分钟,马上出来。”我转身出去。
他换好衣服出来,跟我说:“叔叔,你就把我铐在这里好不咯?……我不吵你,一声都不吭。”他眼巴巴的。他这眼神搞得我有些不适应,忽然觉得这家伙有点贼,我刚把他当小一辈的看,他就冲我发嗲。我吼他一声:“不要那么眼巴巴。”他就低下头,很委屈。
“唔,也行,你到这里陪老子坐到十二点,然后再回去睡。”闲着无事,和他聊了一会儿话,果然如调来的资料反映的情况那样,父亲卧床,母亲的眼睛几乎是看不见的。我问他姊妹几个,他说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
“哦,你不是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吗?”我记得李二全的档案资料和他说的不一样。
“……不是,哥哥七八年前就出去打工,从来没回来过,我们全家就当没这个哥。是有两个姐姐,有一个是从小送亲戚家养大,但这几年她老是回来帮做家务,还给我爹妈塞钱。我就两个姐姐,没哥哥。”
“弟弟又是怎么回事?”
“弟弟……”他嘴皮动了几下,还是老实交代,“没上户口。”
“真拿你家没办法,尽是这些乱七八糟事!”我嗔怪着,拨一支烟给他,想象着那个多灾多难的家庭。抽着烟,我怀疑他父母并不想生那么多孩子,只是舍不得糟蹋钱买避孕套,而计生委下发的避孕套,又为省玩具钱,拿来给小孩当了气球。
十一点刚过,李二全又说要解手。我忍不住骂他:“懒驴懒马屎尿多!”
值班室旁边的厕所堵了,往里撒二两尿,地面的积水硬是能陡涨两寸。老朱用马桶搋子弄了半天没弄通,叫了疏通机也老不见来。厕所用管道都是相通的,一楼一堵,楼上几层的厕所也不能用。穿过操场,那所修建于半世纪前的大厕所仍然屹立,里面一溜蹲坑,坑底经年的积粪用枪都打不穿。我将李二全从固定杆上放开,再次铐上他双手,指了指那边的厕所,规定他三分钟回来。我还塞了他一把手纸。派出所这个院子密闭度很好,大门已经落锁,要想出去,值班室是唯一的通道。我看着李二全准确地走进男厕所。
三分钟,他没回来。五分钟,他还没回来。我穿出值班室后门,冲厕所方向喊一声,李二全!但没人回答。我叫连宝下楼守值班室,然后捏着电筒往那边厕所赶去。
一钻进那厕所,薄膜一样的浓稠的空气便罩在脸上。电筒照亮的地方,光线浑浊模糊,并产生重重叠叠的光晕暗影。这里面竟然没有人。我走到最里面。最靠里的三个坑被厨房小马改成了猪圈,猪圈底部是密闭的木筒子底板。******,这小子哪去了?我闭目想了想所里的环境,当然足够密闭。只有……这厕所的后墙并连着院子的院墙,厕所的蹲坑显然不会只有这么小的空间,它肯定会外延出一个粪窖。老一点的厕所,差不多都是这么个结构,没有化粪系统。我用电筒一个坑一个坑地照。果然,正中间那个蹲坑出现状况——坑底下,枪都打不穿的积粪,竟被人的身体拱出一个大洞。经年的陈粪已经干燥,钻出洞子也不坍塌,保持被钻动时的样子。
老朱听见我喊连宝,觉察到有事,扔掉马桶搋子赶到厕所,问我怎么了。事已至此,我也瞒不了,让他看看蹲坑里那个大洞。
“我的个天,这么硬的粪也钻通了。狗不吃陈粪吧。”
我说:“刚才那小子跑了,应该是从这里钻了出去。老朱,这能通到哪里去?”
“我也不知道,大概能通到墙外。”
连宝继续守值班室,老朱陪着我绕到围墙后面。粪坑果然通到墙外,墙外有一个十来个平米大小的粪窖子。派出所后面这一块菜地多年前就被卖掉了,菜农不来舀粪,粪淤积得几乎溢出粪窖子。
“啧啧,这家伙钻出来,少说要闭气一分多钟,一憋不住张开嘴,就会吃到老陈粪。”老朱看着墙外粪窖被钻出的洞,忍不住感叹。
“他应该跑不远吧,找找看。”
我让鼻孔用力翕张,想循着气味找,可惜我不是狗。这时候我多么希望自己变成一只狗啊。老朱却说他嗅得着一股臭,要我跟着他走。沿着小道走不远,就来到洛溪江边。江雾浊重,夜色四溢,江水很浅。对岸是一大片零乱的工地,散放的建材一堆一堆,比孔明先生摆的八卦阵还玄乎。沿着江水流势往下游看,远远看见江心洲锐利的洲头,将江水破开两股。
我说:“十有八九是过河了。”
“不要撵过去了吧,跑一个小偷,没得好大个事。”老朱出主意说,“反正,领导也不会把这种小毛贼当一回事,少了就少了,可能都不会有人注意到。”
“要是明天有人问起呢?”
“就说讯问了没发现什么大问题,偷东西只是未遂。留置室的人太多,教育一顿这小子态度非常好,下定决心痛改前非,就把他放了。”
“这么说就混得过去?”
“我在这里干这么多年了,你信我就是。”老朱皱巴巴的脸此时格外沉稳。
我俩悄然回到值班室。连宝问我怎么了,我没有声张,叫他去睡。他配合地打起一串哈欠。坐下来,我越想越放松,李二全这号无足轻重的家伙,跑了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李二全为什么要钻粪坑逃跑?试想,任何一个人,他是宁愿被关上两天,还是钻进一个枪都打不穿的粪窖逃走?想到这一层,我眼皮就狂跳起来,捂都捂不停。
6.赖毛信
十点半,我被叫到刘所办公室的时候,伍能升也在。我走进去时他冲我吐一吐舌头,表情很是无奈。刘所看着桌上的东西,那是一张复印的通缉令,公式化的几行文字下面是通缉犯的照片。
这天我轮休,刚睡到八点,符启明一个电话把我弄醒。他兴奋地说:“丁狗子,这下你立功了。昨天那小孩真的是通缉犯……怎么留置室里找不见?”
我说:“发神经吧?一个小偷,哪来的通缉犯?我把他放了。”
“你真把他放了?”
“真的放了,为什么不放?”
“所里领导都还没发话,你自己有什么权力放人?”
“少他妈拿领导压我。符启明,你也就是个巡逻员,吓唬谁?这种事情我用得着向你请示怎么办吗?”
我嗓门一大,他就相应地将声音低下来:“昨天我答应拿那对鸡姐鸭哥和你换,不是开玩笑。你何必放人?不想立功,拿来和我换赚几个钱,也不错嘛。”
“放就放了,你还想怎么样?有种你就去跟所长说,大不了开了我。”我挂了电话,估计符启明去告诉领导的可能性有多大。他不说,领导不会在乎这种事。但他一说,还强调这家伙是什么通缉犯,分明就是冲着我来,所里的人都会认为他是为了编制的事,向我发动攻击。他不会不考虑这些情况。挂电话后我倒头就睡。十点多,连宝敲我的门,说刘所找我。我爬起来打开门,他还问我:“昨天你抓到那个小偷是不是跑掉了?”
“我把他放走的……又不是什么大案。”
“从厕所逃走的吧?我进厕所看过的,中间那个坑被钻出一个洞。我的个天,我宁愿被人打一枪,也不愿用这种办法逃跑。”
“我把他放走的!”
“好的,我不会跟人说,厕所那个洞还在,你自己想想办法。”连宝说,“你快点下去,刘所脸色不好看。”
现在,刘所盯着我,像盯着犯人。“你为什么要把人放走?”
我就用昨天和老朱商量的那一套跟刘所交代。刘所一听也不是没有道理,一个小孩家庭困难出来打工,吃不饱饭第一次偷东西还他妈未遂,关进留置室又被几个老油子欺负。这小孩迟早是放走,早一天晚一天又有什么区别?刘所又指了指通缉令上的人:“是不是这个?”
“不是!”伍能升抢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