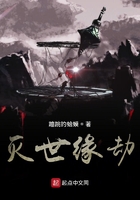只不过转眼,阮狄宸已失了刚刚的柔情,此刻他端坐在马背上,执着马鞭,居高临下地看着跌坐在地上的文酒酒,冷言道:
“包袱里有衣服和碎银,能不能活着到玄国,全看你自己的造化!“
说完马鞭一扬,凌空抽了一鞭,喝道:
“走!“
文酒酒的眼泪还没止住,她踉跄地起身,胡乱地抹着眼角,仰头看着马背上周身冷意的男人。
“七七……“
她上前一步,“啪“一声脆响,马鞭抽在她身侧的红杉木上,将破碎的树皮溅起,文酒酒侧身闪过,含泪望去,阮狄宸又爆喝一声:
“走啊!“
文酒酒抽噎着拾起地上的包裹,向东走了几步,忍不住又回头去看。
“啪“又是一鞭,这次抽在文酒酒身后的灌木,鞭尾扫到她的后背,带破了一层衣衫,文酒酒惊叫一声再不敢回头,抹着泪跌跌撞撞地向前奔跑。
身后的阮狄宸此时仰着头看朝阳氤氲而升,将将浮出树梢,林木被照的斑驳陆离,阮狄宸不敢低头,怕眼中掉落出什么来,他本铁汉男儿,怎可为一女子落泪!笑话!笑话!
待文酒酒身影消失在密林之中,阮狄宸这才顺着她远去的方向去看。
“酒丫头……“
他低声喃喃。短短数日便可爱上一个人,却偏偏要用一生去遗忘,恫悟出灵魂的纠葛竟是这样的撕心裂肺……
鹤源城郊,风吹散雨雾,卷来的是马蹄滔滔,草陈铺新土,留下的是车轮滚滚。绯玄两国军阵对垒,晁飞和公孙敖各自坐了五马拉车,遥遥相望。
身边的阮狄宸身披赤甲,眉头紧蹙,肩上的披风被雨淋得湿漉漉地,却浑然未觉,只警觉地看着前方,顾安冉依旧坐在华盖内,状做慢条斯理地摇着折扇,这华盖,挡得住雨,却止不住风,人虽立在其下,心却早已随着风雾奔腾而出,顾安冉盯着晁飞身后死寂的鹤源城,渐渐有了非常不好的预感。
晁飞那方首先出一骑,马蹄下泥土飞溅,携着议和书而来,公孙敖展开略略看了看,随即紧皱眉头,阮狄宸策马趋近,问:
“什么要求?“
公孙敖猛然收起手中的书帛,恨恨道:“还是要东城郡!“
“东城郡和晁飞现下的云岩西相连,晁飞要东城分明是要自立为王,以后为我们绯国也是一大患!不能答应!“
一旁的简绥远抢白,顾安冉手中的折扇晃了晃没做评价,公孙敖侧头看了他一眼,身边的阮狄宸怒道:
“先谈鹤源城的百姓!晁飞那厮到底有没有屠城?我怎的觉得那鹤源空空如也,仿若死城!“
说完看了一眼公孙敖身后的佘行之,今日她又是一身男装,想必公孙敖还没看穿她的身份。
“对!先问问鹤源六万百姓,死了多少?伤了多少!“佘行之顺着阮狄宸的话往下说,公孙敖微微颔首,招来身边的亲卫低语了几句,须臾,一骑带着公孙敖的话向着晁飞而去,不肖片刻又辗转而回。
“晁飞怎么说?“
“回大人!晁飞说百姓的事等大人进了城便知,不必多说!“
“岂有此理!“阮狄宸爆喝:“若是他屠城,我绯国要一空城何用?六万血债在身,那晁狗也敢和我们讲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