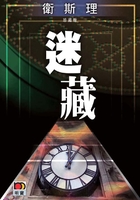这样的戏,永远不会在乡村的土台子上演出。女演员用脚尖走路,乡村的土台子没有那么平,露出块小石头,就会把她们绊倒,让她们扭扭歪歪打不了仗。她们要是不用脚尖走路,把脚放平,她们就跟乡村的女戏子一样了,值不得人为她们惊叹。她们全副武装,穿了裤衩。少数几个拿枪的男人倒穿了长裤。照片印在报纸上,纸张远远不如印做饭女人的图片好,没有彩色,看不出她们跳舞的腿白不白,所以很难断定她们烧什么燃料做饭吃。看她们穿了裤衩打仗,就知道战争在热地方爆发,男人们倒穿了长裤,令人费解。女人们穿了裤衩参战,男人们就应该赤膊上阵,男人比女人更不抗热。郑小群把报纸拿在手上,杜炳成只瞥了一眼,就断定服装出了问题。杜炳成根本不考虑作战地点是在热带丛林,男女都会很热,理应平等。他说黑旋风李逵手拿两把板斧,穿小裤衩赤脚追杀,母大虫孙二娘照样穿了衣服,裤腿用带子扎起来。自古作战,都是男人比女人穿得少,从来没有反过来的道理,三国里的许褚也是如此。女人不是不准许当兵打仗,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用的也是男人的名字,穿了男人的铠甲,不露大腿。她要是露出大腿来,就极易中箭。女人上阵,即便穿了男人的铠甲,也需要拿了盾牌防箭,保护身体。乱箭射脸,她们倒不那么害怕,射中眼睛,拔下来就把眼珠子自己吃了。郑小群分明记得,从眼睛上拔箭吃了自己眼珠的战士是男人,杜炳成说得不对,他也不敢跟杜炳成辩论。南下淘金以来,唯一没跟杜炳成发生争论的淘金人,就是郑小群了。他就是听出杜炳成说话不对,也不说什么。他倒不是那么害怕杜炳成瞪眼,他是觉得自己没有杜炳成念书多,杜炳成用文化威胁他,他就是不胆怯,也会惭愧。文化,说到家不就是一种让人惭愧的东西吗?人只要不失去羞愧之心,就要时常在文化面前惭愧。
郑小群耐心地等待杜炳成不说话了,他再集中精力独自欣赏。他从政治层面,理解了当兵的女人穿裤衩。妇女要解放,拿起枪杆来,她们从三座大山的最下面,翻身出来,浑身轻松,自然要比男人们穿得少。要是男人们穿了裤衩,她们穿长裤,那就跟没有翻身的过去一样了,她们拿起枪来也是白搭,枪林弹雨打过来打过去,还是替男人们干的,妇女仍然压在最底下。她们穿了裤衩,就扬眉吐气了,站成一排横握枪,全部用脚尖走路。一齐抬腿,金鸡独立。她们还会高空劈叉,一排人像飞起来一样,大腿挺直,裤衩无碍。穿了长裤的男人也想劈叉,但是显然打不开,只能在半空屈了腿,学飞翔的样子。男人们就是穿了裤衩,劈叉也难。他们选择了长裤,倒有利于护短。妇女翻身,从此定了。郑小群想起“九大”召开之前的夏天,在公社的大屋子里开会。人多得大屋子里盛不下,临时改在大屋子外面的广场上开。文件念到一半,一队红卫兵从大道上开过来,打着旗直接走进会场。他们是三河一中的红卫兵,旗手不用男生,就用女兵,女红卫兵胖墩墩的,穿了裤衩。她后头的红卫兵无论男女,全穿了长裤,只有她一个人穿了裤衩,一花独放。天有些阴,还没有下雨,郑小群看见女旗手的腿润泽发亮,膝盖一走抖出一个肉窝。郑小群是第一次看见女人穿了裤衩走路,他像很小的时候看见杨贵妃脖子上抹粉仰身弯下去一样,脚指头抓地,下体抽搐,一连四下。第二天不开会了,继续下地干活,顶着烈日回来,他看见朱萍儿戴着草帽,走到村子东头的水渠边洗腿,洗完以后,不放下卷起的裤腿,带着两腿亮晶晶的水珠走路,腿比女红卫兵白,露得也多。
朱萍儿的腿再白,郑小群也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们不在一个生产队干活,郑小群看不见朱萍儿的膝盖能不能走出肉窝。东顶的土地分布在三道山岭上。只要不是在高粱地里干活,高粱秆儿把弯腰的人挡住,郑小群在哪里,都能找到朱萍儿戴的那顶草帽。有太阳的日子戴草帽的人很多,要找到稍有困难,不下雨的阴天就好了,满山遍野,唯一的一顶草帽就是她。朱萍儿如花似玉,草帽遮颜,她的艳名还是在乡野流传,挡也挡不住。村子里的前辈美人儿小妹唱戏专当主角,艺名过盛,差可自慰;朱萍儿要是不演那个开店的杨二嫂,解下小围裙,穿上红毛衣,演了主角,她就色艺双全,完全盖过了小妹。
自从公社书记李玉明领导修对手沟水库,严青青喊号子砸夯,被柳弦子发现了美貌,严青青的美名就在中流河两岸传开了。对手沟水库进入二期工程,朱萍儿也上了水库工地。一个工地上同时出现了两个美人儿,双花争艳,久经情场经验丰富的柳弦子也看花了眼,无从下手。他大弦子在怀,按时一抖,在剧团里采花,从未遇上此等难题,剧团花乱,闭着眼见花就掐,捡到篮里就是菜,根本用不着比较和算计,他没有过乱花迷眼的苦恼和困惑。两朵花在眼前摇晃,数量有限,他瞻前顾后,左右为难,担心一时眼花,断不准高下,顾此失彼。情窦初开的郑小群倒没有这种烦恼,他未上情场,纯洁而敏锐,不带功利性混浊,他略加比较,就认定了朱萍儿比严青青美貌。就算她们两个人同样美丽,难分高下,朱萍儿比严青青腿长,就占定了花魁的高枝。郑小群从来没见过严青青把裤腿卷到那么高洗腿,那就是美女自己懂得藏拙。三河一中的红卫兵女旗手胖墩墩的,穿了裤衩,走在队伍最前头,她不是为了展示自己的美丽,她是为了战斗,是一个勇敢的红色娘子军,她腿上的润泽和肉窝,是别人眼里的光景,不是她有意叫人看了。
如果对手沟水库永远修不起来,中流河东岸十六个村子的土地像过去一样干旱,郑小群干枯的心田,就会得到爱情渠水及早浇灌。由于有了严青青和朱萍儿同时上工地,由于有了老两捏细嗓子唱“麦苗儿青来”,由于有了柳弦子龇着金牙微笑追逐美女,对手沟水库充满了热烈的爱情气氛。郑小群躬逢其时,也被派上水库工地,他即便不能植起爱情的树苗,开花结果,能跟朱萍儿一起干活,不必在两个生产队劳动,远远地寻找那顶草帽,他早熟的青春也会健康地丰满起来,他会饥渴,却不会扭曲。有了跟朱萍儿的哥哥朱建国学习拉胡琴的理由,他自然有了多一些的机会,看朱萍儿两条长腿闪耀着水光。奇怪的是,他越是想借着跟朱建国学拉胡琴的机会,接近朱萍儿,去村子东头那所房子越频繁,父亲的脸色越是不好看了。有一次他刚刚抱着胡琴要走,父亲还严厉地阻止了他,警告他少去朱萍儿家。父亲不说明警告的原因,他便始终没有想明白。村子里三姓之间会有世仇,可是,朱萍儿胖乎乎的母亲,每一次见郑小群抱着胡琴进家,总是笑嘻嘻地跟他说话,不像有仇恨,倒像有一种特殊的亲密感情,她要是不老不胖,差不多也是一个朱萍儿一般的美女。郑小群猜不透父辈的隐秘,他只有面对现实,坚持刷牙,不管父亲如何反对。他可以服从父亲的警告,少去村子东头的那所房子,可是父亲再反对,他也要继续刷牙,坚持不懈。在对手沟水库工地上劳动,比较愉快,郑小群那一天开心一笑,朱萍儿看着他,说了一句话,成为郑小群坚持刷牙的不竭动力,美人儿说:
“一口小白牙挺不错的。”
郑小群十分感谢农中的女老师让他学会了刷牙。他没有当成“赴京代表”,去北京大串连,接受伟大领袖检阅。那一年冬天,农中的女老师带队,他们去青岛串连。青岛会有什么?女老师也说不清楚。只知道一直往南走,离太阳近一些的地方,革命的烈火应该烧得更旺。徒步行走,拒不乘车,后面开过来的大卡车,走到红旗跟前停下,要送红卫兵小将一程,大家一齐摆摆手。第一夜宿在一座新村南面的工厂里,工厂容易让人遗忘,路过的新村永难忘怀,那是因修水库迁移的村子,全部是青砖灰瓦,粉白的灰盘,整齐的街道,整个三河县没见过那么新的村落。当夜下雪,第二天早晨起来,郑小群还没有打起背包,看见了女老师在女生宿舍门口刷牙,喷出的漱口水在雪地上击出了不规整的雪窝,呈黄色。吃饭的时候,他看见女老师的牙齿雪白,想起了在老书上看到的一个词:“明眸皓齿”。他们一直走了六天,第六天傍晚看见了青岛的灯光,女老师再也走不动了,她犯了关节炎,一瘸一拐地走下来。女老师行走艰难,不忘刷牙,牙齿一直保持雪白。他们住在一所橡胶学校里,串连青岛三十二天。女老师腿病渐好,遍走青岛商店,买了三河县买不到的布料,准备回家结婚。郑小群没再看见女老师刷牙,可是一看到女老师明眸皓齿,向往未来,郑小群就知道,女老师刷牙不辍,一直在为美好的未来充分准备。离开青岛回家,他们不再拒绝乘车。大卡车早就联系好了,围了席棚。回程的雪从席棚缝里钻进来,他们摇一摇头,挤在一起,郑小群没有注意到女老师坐在哪里,女老师分明是将明眸皓齿好好保藏了。这一个冬天奇冷,郑小群在最寒冷的一个早晨开始刷牙,用“大鸡牌”牙粉。父亲不满地反对他。他知道,父亲不是因为他把牙龈刷得出血心疼他,父亲是舍不得让他花钱,一包“大鸡牌”牙粉五分钱,能买半斤咸盐,够全家吃十六天。
革命年代开始的卫生习惯,有了美人儿的赞赏和鼓励,哪怕空着肚子挨饿没有东西吃,郑小群也非要坚持下去,让牙齿雪白不可。南下淘金,郑小群带上坠琴的同时,也带了牙具,到了他琴艺大进能够自拉自唱那一天,他将口齿伶俐,绕梁不绝。南乡尚非青岛,虽然离太阳比东顶稍近,亦恐难以接受刷牙。初到南乡,冬天的雪还未融化,郑小群比别人早起一会儿刷牙,趁无人看见时,像农中的女老师一样,把漱口水喷到雪里。他没有想到,他的举动会得到下台党支部书记杜邦的理解,杜邦披了衣服起来尿尿,看见他咕噜咕噜漱口,像在梦中一样咕哝了一句:
“刷刷牙挺好。”
可惜朱萍儿没再说他“一口小白牙挺不错的”,也许她连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都忘了,她好像原本就没有把郑小群看在眼里,她艳名盛传,自然会有美人儿瞧不起人的通病。朱桂美像她的影子,从宿舍到伙房,再到干活的工房子,总是一起来去。你看见了朱桂美像男人一样迈大步走路,同时就会看见朱萍儿娉娉婷婷袅袅娜娜,像大白菜旁边摇摆着一枝杨柳,像地瓜跟前立了一棵葱。朱萍儿要朱桂美形影不离地陪伴她,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朱桂美是朱萍儿太阳正高时挤扁的影子,她自己没有萎缩的痛苦,倒常常膨胀,泄露一些别人不知道的秘密。还没到南乡的时候,朱桂美就说,她看见过朱萍儿和哥哥朱建国躺在一铺炕上,那一天下雨,朱萍儿和朱建国都没穿衣服。
红色娘子军
有一些秘密,只有朱桂美那种走路迈大步的姑娘口没遮拦,才敢说出来。朱桂美坐在两盘大磨后头,拿两把铁勺挖砂子,她需要好好瞄准,才能将砂子投进磨眼里,她泄露秘密,却不加思量,而且一下子就能击中要害。郑小群最初听到了那个秘密,曾经很绝望。他原本就觉得自己不如朱萍儿的哥哥长得好,抖不起来,从此后将更加惭愧,不敢让朱萍儿看他拉琴。有一段时间,他希望能看见朱萍儿跟朱桂美打架,她们两个人一打架,就将证明,朱桂美泄露的秘密是假的。朱桂美像个影子似的,附在朱萍儿身上拆不开,南下淘金,又一起来了,贴得越发紧密,郑小群就觉得,朱桂美泄露的秘密原本就不是真的。南乡淘金以来,她们两个人住在一户人家的闲屋里,一铺炕上睡觉,朱桂美知道的秘密自会更多,她再也没有透露,不是她懂得了保密,而是她没有找到证据,来证明朱萍儿和哥哥不穿衣服躺在炕上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