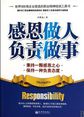从真正意义上的生活这一角度出发,尽管我们从事的还是同样的事务,但是结果是完全不同的。那些看起来是浪费时间和生命的事务开始变成生活的意义表达物,变成一个人领会世界的方式、观念传达者和思想的承载者,既然在这些事务中已经寄托着个人的思想和意义,它们就被纳入这个人的生活之中,不再是完全另类的存在了。一个人学会生活的过程是漫长的,而且理性的形成是学会生活的基础。我们首先在心中逐渐形成一种意义和观念核心,这些意义和观念是对生活的反思以及从别人的思想和事件得来的,然后将这些形成的意义和观念投射到所从事的事务当中,从而得到这些事务的意义和动机。不过,这一过程不是单向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我们将自身的观念和意义投射到事务之中,事务也要向我们展开它自身特有的性质,事务的特性反过来会影响我们的意义,并找到一个结合点,这样构成一个不断领会和阐释的过程。按照习惯,我们将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区分为基本生活、精神生活和生活理想。不过,这些区分只是为了便于我们进行把握,其实人的生活本身是一个综合体,在生活过程中,这些方面不可能区分得开。
三、从生与死的维度发掘生命的内涵
不同的文化系统具有各自不同的生死观,不同的生死观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生命问题的多种可能性,我们分析一下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生死观,分别从不同的渠道来窥探生命的内涵。
(一)从中国传统文化生死观理解生命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严格来讲,要追溯到诸子百家以前,但是,我们需要考察自始至终影响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文化,我想,公认的说法就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这三者共同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这三种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三个思考问题的角度。
首先,儒家的生死观注重生,也注重对待死的礼节,但是,没有对死亡作出过多的假设和探究。“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在孔子看来,死是无法捉摸和把握的事情,而生正是我们每天面对的也是必须面对的事情,一个人连能够接触和体会到的事情都没有把握和理解,又怎么去理解和把握那根本就触及不到的东西呢?这分明就是舍近求远、很不明智的做法。而所谓“知生”,就是知如何“事人”,事他人,事自己。一个人要做好“事人”,要做到“知生”,就需要领会天地阴阳的变换和转化,要明白人生和世间万物的相类相应之处,并将从天地造化中学到的智慧运用于人事,做到“仁”“义”“礼”“智”“信”。对待死亡的各种礼节,也包括在面对人事的这五个要求之中,可以说,它是为了更好地尽人事。所以儒家思想要求人在现世上努力,尽到自己的人事,从现实的标准上做到尽善尽美。
其次,道家思想具有天人一体的意蕴。“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天与人的“合一”既不以人的喜好为转移,也不以人的认识为转移,而且,天与人是不会相互冲突的,相反,天包容人于自身之内,人也可以领会自然的真义,但这只有“真人”才能做到。庄子的意思是:天与人是合一的,这个“合一”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道家学派认为人的生和死其实没有根本的差别,人的死亡只不过是回归到自然,回归到天地之中,没有什么可悲的,既然人的死亡和人的生存都在天地之中,只是形式不同,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也没有失去什么。“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熟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这一点与儒家思想完全不同,儒家认为死是不可把握的,将死与生看做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这两个方面是对立的,所以人死后是应当感到悲伤的,而道家思想认为死与生是其一的,两者就像人身上的不同部位一样,其实同属于一个大全体,没有根本的分别,而这个大全体就是天地本身。所以,道家学派提供了一种人生境界上道德升华的渠道,它为人们展开了另一种超越于人事的心境。
最后,佛家思想认为生死轮回,注重因果报应。不过,中国的佛家思想同样渗透着儒家和道家的意味,比较独特。佛家思想注重因果报应,指的是,一个人在世上所做过的事情并不是做过以后就完全过去了,而是任何一件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和我们将要做的事情,以及任何一件我们正在面对的事情和将要面对的事情都不是随意发生的,它们必然有其缘由,这个缘由就是事情的因,所有人世间的事情都处在相互关联之中,甚至一个人在这个世上所遭遇的命运也是有它的来由的。所以,一个人在行事的时候,不能仅仅看到眼前的厉害,要明白,这些事情都会成为以后事情的缘由。而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指的就是这些缘由的关系是同类传递的,一个人对他人做了善的事情只会成为自己遇到善事的因,同理,对他人做了恶的事情必然成为自己遇到恶的事情的因,如果一个人不想自己以后遇到恶的事情,就要尽可能不做恶事。而且,一个人做了善事往往不是在活着的这一世中得到体现,所以佛教认为,人的灵魂是轮回的,可以转世,把这一世的善因转入下一世的善因,导致了下一世的善果。所以,佛教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从人事和生命的相互关联中,来规范和约束人的行为,要求人面对生命的时候,更加谨慎,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宗教性和道德性的生命观。
(二)从西方文化生死观理解生命的内涵
西方文化中的生死观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它从注重生的现实到注重死后的情景,最后将注重死后情景这一点投射到生的现实中来。
古希腊时期,也是西方文化传统的萌芽和产生时期,在这一期间涌现了许多思想者,在这些思想者中,大多数都注重生的现实状况。而注重生的现实也分为两个倾向,其一是将生看成我们追求幸福和快乐的过程;其二是将生看成人类顺应自然本性的结果,人要按照自然赋予人类的理性行事。
第一种倾向的典型是伊壁鸠鲁。围绕伊壁鸠鲁,形成了伊壁鸠鲁学派,伊壁鸠鲁将快乐划分为三类:“自然的和必需的,如食欲的满足”;“自然的,但却不是必需的,如性欲的满足”;“既不是自然的又不是必需的,如虚荣心、权力欲的满足”。这是一种很基本的、很原始的区分。然而,伊壁鸠鲁又从另一个角度来区分人的快乐,从这一角度来看,人的快乐又分为持久而平稳的快乐和激烈而短暂的快乐两类,他更加倾向于追求前者。人应当尽量追求那种平静而持久的快乐,那些激烈的快乐虽然能够给人的感官带来强烈的刺激,让人得到的快感很强烈,但是,这些快乐会转瞬即逝,因为快乐是感觉的产物,而感觉都是当下的,所以,尽管这些激烈的快乐是令人陶醉的,但是它们比不上持久的快乐源源不断地为我们的感官提供快意来得好。但是,死亡总是困扰着人,一个极力追求持久快乐的人,只要一想到死亡,就会变得垂头丧气,这样就中断了快乐的获得,所以,一个要寻求持久快乐的人不仅要尽可能在两种性质不同的快乐之间选择它,还要面对死亡的威胁,将死亡的威胁变得微不足道,使之不影响人们对持久快乐的追求。因而,伊壁鸠鲁指出,死亡并不可怕,因为一个人死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还惧怕什么呢,死亡不是人真正能够接触到的,况且,神根本就不关心人类,一个人生前怎么样并不能带到死后去,神既不奖赏人,也不会惩罚人。人唯一要做的就是活在当下,追求生的乐趣和幸福。
第二种倾向的代表是斯多亚学派。斯多亚学派认为,世界的本性就是“逻各斯”,人是世界的一部分,当然也要服从世界本性,要按照“逻各斯”来寻求生存。在他们看来,人的生与死都是依照自然世界的“逻各斯”完成的,违背“逻各斯”是不明智的。生不是人所能够选择的事情,死也不是人所能够选择的事情,每个人的生和死都严格遵从“逻各斯”,我们为此付出的努力都是白费,生和死的这种状况被称为命运。不过斯多亚学派也承认人具有自由意志,这种自由意志不能用来选择人的生与死,但是它却可以用来选择人以何种方式行事才能符合“逻各斯”,人的生存就是这一内在磨砺和进化的过程。至于死亡,人既然不能选择,就大可不必计较。这一点和伊壁鸠鲁学派是一致的。
到古希腊晚期,新柏拉图主义者开始关注人死后的幸福,并开始偏重对灵魂的探究,从而超出了对现实生活的关心。普罗提诺就认为,人的灵魂“一方面可以上升到最高本体,另一方面可以下降到可感世界。同样,人的灵魂既可以通过思辨和观照追求神,也可以耽于肉体而陷入身体不能自拔”。灵魂的上升和下降演化为天堂和地狱的区分。上升的灵魂居住在天堂里接受神的恩赐,得到完满的幸福,而下降的灵魂禁锢在地狱里承受神的惩罚,痛苦不堪,为自身洗去在尘世的罪恶。“基督教吸收了新柏拉图主义对生死两界的这一区分:好人升天堂,恶人下地狱,这就把争取个人幸福的战场从人世间扩展到了死后,人生的概念也成了双重的了。”整个基督教统治的一千多年,对于死后灵魂的偏重几乎近于狂热。
这一点在近代西方文化中得到了改变。它基于两大变革,即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新的基督教教义开始在西方思想中形成,这一新教教义要求人不仅要关注死后的灵魂得救,更要将这种关注投射到现实生存中,将这一期望转化成改变现实的强大力量,这也是支撑近代资本社会快速发展的一种强大精神动力。
(第二节)生存教育
——以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为依据
人在世界上存在面临着一个摆脱不了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一种生存的张力,生存状态的好坏就决定于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是否处理得当,这两个方面就是自由以及自由所面临的限制环境和存在条件——境遇。
一、大学生对自由的普遍理解
高中生进入大学以后,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环境的变化,这一变化并不仅仅表现在大学校园的自然风景和教学设备之类,它更多地体现在大学校园为学生提供的一个多样化、自主化的学习空间。高中生活,甚至可以说整个高中以前的学生生活,都具有很强的约束性,,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学生每天所能够做的就是完成学校老师和家长安排的学习内容,有时候这些内容甚至变成了一种任务。学生希望有自己的时间,但是,他们又没有机会拥有自己的时间。久而久之,无论学生是情愿的还是不情愿的,他们都会逐渐养成被安排学习的习惯了。在漫长的中小学学习过程中,这一习惯不断被巩固和加深,等到高中毕业的时候,它可能已经变得根深蒂固了。
将这一习惯带进大学校园,这些已经养成了“被学习”习惯的学生就会感到不适应。从中学到大学的环境的转变,实质上是一个从他人管理到自我管理,从他人约束到自主自由的转变。这是一个迎接自由到来的时期。在这一转变面前,绝大部分学生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大学生要么表现得不适应或不愿适应,要么表现得过度兴奋。首先,那些不适应或不愿适应的学生往往想要保持过去的生活状态,想方设法让自己被安排。他们认真上课,无论老师讲什么,讲得怎么样,都按时上下课,遵守学校各项规则,按时完成作业,努力考试,如果还有闲暇时间,就报各种辅导班,考取各种证书,当然,这是一种学习方式,但是,如果心态和习惯没有从高中时代转变过来,还处在一种被学习的状态下,就可能只有学习的形式,没有学习的内容,或者说,学习的收获甚微,高分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代表学识了。其次,那些不适应或者不愿适应的学生还容易走上歧路。这部分学生不适应的不仅仅是没有被安排,而是不适应开始拥有大把的时间,这些时间没办法打发。以往的学习时光实在太过紧张,以前是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现在突然拥有大把自己的时间,就像一个饱受饥渴很久的人,面前突然出现了一顿丰富的午餐,他们开始几乎报复地将这些时间用在以前想做但是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做的事情上,这些事情不论是好是坏,是可控的还是不可控的,他们都不在乎,在乎的是这种自己掌控的感觉。可能有些学生很幸运还在这一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向,并开启了以后的人生之路,而大多数学生却在这一过程中开始被某些事物控制而不能自拔,更不幸的是,有些事物是性质恶劣的。这样一来,这些学生不仅没有得到向往的自由,反而陷入更深的禁锢,走上了歧路。
同样面临大把自己的时间,有的学生兴奋过了头。他们实在被压抑得太久太深了,就像一个人突然从一个地洞来到地上的花园一样,对什么事物都好奇,对什么事情都充满热情。大学里面可以接触到无数新奇的事物,一个饱含热情的学生可能会选择很多课程、参加很多活动、加入很多社团,表现得很活跃,而心情很浮躁,对事物没有深入的把握、蜻蜓点水,一学期下来,结果可能是成绩不好,活动质量不高、收获不大,社团令人失望,于是开始变得不安,变得迷惘。这种没有方向和目标的人生当然也谈不上自由。
纵观以上各种情况,我们发现,当代大学生,尤其是低年级的学生,对自由的理解状态可能有两种,一种是对自由无意识,也就是说,他们在通常情况下可能根本就没有自由这一概念;另一种是对自由的理解存在偏差或对自由存在误解。第一种状态的学生往往表现为不适应或不愿适应,第二种状态的学生往往表现为过度兴奋或者走上歧路。
那么,对自由的真正理解应当是怎样的呢?要对自由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恐怕不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也可以有各种表达,所以,我只能指出自由的存在需要具备的条件。自由必须具有理性的指导,理性具有主动的特点,一个具有理性的人通常能够主动行事而不是被事物牵着走,这是自由最重要的条件。在这一条件下,自由需要随时保持面对事物的主动性,就是说,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是自己决定去做,而不是被要求去做。同时,在理性的主导下,要求一个人在判断的时候进行权衡,时刻在各种事物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就是说,这个人不能因为做了一件事情而使得他想要做的另一件事情受到限制,而这一限制不是他主动决定的。人总是存在各种思想和想法,因而以上说的这三点也包括对思想或想法本身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