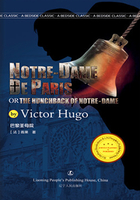霍俊明(1973-),1973年出生于河北丰润,文学博士。着有专着《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在《文学评论》等发表学术论文及随笔300余篇,在《诗刊》《人民文学》等发表作品400余件,印有诗集《秋天的老式过滤器:1994-2004年诗选》、《京郊的花格外衣》等。诗作入选《诗选刊》、《2007中国年度诗歌》(《诗刊》社编)等选本。现执教于北京教育学院人文学院中文系。
南长街的水果车
人民广场西北侧的小巷
电线上站满成群的乌鸦
或大或小的雪
仍在一次次推迟
从京郊来的马车
逆行在熙来攘往的首都人流中
那匹慌乱的马开始奔跑起来
这对卖水果的夫妇显然有些吃惊
妇女的奶子在廉价的薄汗衫中抖动
香白瓜在马路中央摔成这个下午破碎的阳光
他们已不能控制眼前发生的小小意外
此时旁观的人们却感到快意
密集的车流,严密的管制
有时需要一次小小的冒犯
这失控的马车多像我儿时站在红色拖拉机的后座
乡村路上愉快的颠簸
遥远的澄迈(给江非)
去过海南,但不知道有一个澄迈县
你到这个过去年代的渔村正是北京的夏天
你那些远道而来的山东朋友带来了煎饼和大葱的气息
他们紧握我的双手你却背起了行囊
一只蚂蚁上路了……
一只蚂蚁带着平墩湖去了椰子和海滩的南方
但海风是潮湿撩人的
连南方姑娘温柔的方言也是苦涩的
我知道诗人路也去过江南
那是她爱情的江南,小资的江南,古典的江南,诗意的江南
她把小虾小蟹,小花小草都写成了两情相悦的童话
可你的南方呢?
平墩湖的夜色更深了,院落也空了
你诗歌的卷宗越来越充满着光亮,也有同样的幽暗
三十多岁的皱纹被尖厉的铁轨镀亮
我会想到某一刻你重新来到北方的情景
那双老式的棉布鞋会印证我
一个又一个布满血丝的夜晚
北京的大街上只有车来人往
我的朋友在遥远的南方
澄迈比海南更远
儿子的手指在阔大的地图上滑动
狭小的澄迈让儿子吃惊
他的被咬的锯齿状的尺子已经丈量不了
北京到海南的距离
尽管你带着油墨芬芳的手抄稿就在我的枕边
让我在这个时代感谢澄迈吧
她让一个三十多岁的老男人重新拾起了思念
还有忧伤
我的儿子已经学会了和我讨价还价
而遥远的远方,澄迈的一个楼房里的灯光
却是为我照亮
夏末的皮影戏
此刻,已是初秋
黄昏的光线清冷而模糊
我和母亲
十几年没有一起走过这样的夜路
青纱帐的巨大阴影遮盖了熟悉的脚步
宽阔的玉米叶子在身上擦出声响
母亲手中的旱烟忽明忽暗
在场地上坐下来的时候
母亲已经有些气喘
屁股底下的两块红砖证实了她的疲惫
这里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庄稼人
缭绕的烟雾伴随着低声而欢快的问候
小小的舞台,白炽灯耀人眼目
驴皮影人,一尺精灵的人间尤物
演绎着大红大绿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卡着嗓子的嘶哑声调
在夜晚的乡村也充满了呛人的烟草气息
母亲神情专注,双目清朗
这个夜晚充满着水银的质地,沉重而稍有亮色
夏末乡村的皮影戏使我不能出声
哪怕只是一次,小小的咳嗽
十二月的广场
挤出地铁车站的沉闷天气
广场上灯火辉煌,人流疏远
我远远地将你打量
谨慎的身躯消化在伟人头像的阴影里
遥邈的夜空,游移的风筝高低错落
滑旱冰的平胸女孩
雕塑的空隙中穿插往来
快活的欢呼声是我们并不衰老的身体
十二月的风仍未止息于粗糙的额头
广场上的探照灯打在脸上
我们友好的拉手
也是空前的可疑
而他们不管这些,外省的青年男女
紧密的搂抱和值勤的警察仅三步之遥
十块钱的牛仔裤绷紧着壮硕的身体
搂抱、抚摸、接吻的姿势如此标准
我也知道,你们的城市拐角处的窝棚太过狭促
宽阔的广场,伟大的心脏
适合你们小小的愿望
明天照旧抱着煤气罐和铁秤躲避城管的吆喝
在第一场雪中去昌平
第一场雪
飘洒在北京到昌平的路上
第一次望见了高速路旁
那些白雪的屋顶
而多少次
夏日灰蒙蒙的呼吸让我厌倦
现在是赶往昌平的路上
雪越下越大
稀疏的枝干上黑色的鸟巢
微微颤动
那些因暖冬仍发青的树冠
能否承受这凛冽的赐予
当年,曾有诗人在这条路上行走
在这条
去往昌平的路上
人定湖公园
剪草机在远处轰响
银杏树叶在风中扑落
这些斑驳陌生的脸庞
人定湖公园,这小小的
圆形广场,儿子欢快地滑着轮滑
他和刚认识的小女孩已经打得火热
紧密的追逐和小小的吆喝
鞭打着我曾有的往日
窄促的水面在轻轻抖动
黄昏斜递过来的阴影
遮盖着我的三十岁
不衰老也绝不年轻的身体
我承认
秋日给我生疏的内心带来感动
但远没有天空飞过的鸽群那样高淼,那样洒脱
是儿子让我想起乡间的墓群
此时已接近春天,尽管这个早晨
风将喜鹊的长翎高高扬起
“我害怕死去,爸爸”
儿子的低语让我震惊
往日的胶片倒转是这样匆忙
那年我12岁
夕阳将院外的白杨镀成病态的黄
我突然感受到死亡的恐惧
这小小的肉体会有朝一日,再不复来
我在上初二的时候才学会了骑自行车
那是1989年,天气酷热,没有星空
上完自习的时候已是九点多
冒着被肥胖的教导主任批评的危险
偷偷溜出校园,我要回家
一墙之隔,校园外是空旷的田野
我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拿着手电
夜太黑,路上满是大大小小的坑
过不了多久,我就会经过五里之外的乡村墓群
那黑压压的颜色让人毛发直立
先放慢车速,然后,疯狂猛蹬
冲过那片墓地,浑身已被汗水湿透
成排的白杨在手电的斑驳中忽隐忽现
村口的那片坟地更让我心惊
早年的阴森故事在此刻是如此清晰
没有漂亮的狐仙,只有闪烁的磷火
而今乡间的墓群已经侵占了早年的鱼塘
看守鱼塘的是一个姓王的聋子光棍
那年夏天的大水冲跑了鱼,也拔倒了那片白杨
我们只顾高兴地在土沟里抓那些鲤鱼和白鲢
水早都干了,而坟头却一个个挨着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大舅、二舅、二舅妈
他们都躺在这里
我也会在某一个黄昏或清晨来到这里
故乡的墓群,萧瑟而温暖
我曾带着儿子从墓群中穿过,走远……
京郊的花格外衣
穿橘黄马甲的养路工
正在不紧不慢地刷新路边的护栏
不久的明天,尘埃仍会光顾它们
京郊公路旁堆满了刚刚收割的玉米
麻雀在秋阳下踩踏着落叶和草茎
短暂的午后
有多少沉静,就有多少喧嚣
来自耳边的声响
切近而又遥远
往日厨房的细节被一一唤醒
也在逐一掩埋
我知道,我的花格外衣
还挂在窗外
那棵梧桐会给它添加斑驳的色彩
秋阳下的长安街
我的儿子最喜欢西单图书大厦的儿童乐园
我穿插在中间,愉快而又不安
身旁的小女孩多像隔壁家的三女儿
我儿时的同桌
秋阳铺洒下的长安街
落叶还没有这么早到来
拉着他的小手,往日的焦虑和对他的斥责
成为惶恐和内疚
路在脚下也有些发抖
肯定,在多少年以前
我的母亲同样拉着我的手
在乡野的田塍上看油绿的庄稼
远处的落日
在长安街上这样慢慢游走
风紧了
儿子拉着我的衣角,大声说
看--
“那个金黄的树真像奶奶的脸”
秋夜北大
在狭仄的厨房烧这顿晚餐
内心的不安和小小的惊喜被微弱的灯盏打量
即将到来的诗歌朗诵会有些让我心动
水流漫过手中的菠菜,亲近而脆弱
北三环路上拥堵的车流夹杂着司机的谩骂
中关园的路程扩张为两小时枯燥的生活课
这多像我刚刚在家用水发过的肿胀木耳
而窗外的夕阳
同样镀亮了一个个不安而倦怠的脸
秋夜下的北大校园人流匆促
玩滑板的女大学生
巨大的电影海报上落下斑驳的梧桐树影
风中的树叶响得更紧
未名湖畔有多少秋声,就会有多少落叶
秋日的旅程
普通快车已经驶出北京的东郊
劣等车厢的旅客疲倦而健康
粗大的指节敲打着油渍的桌角
哐当作响的车窗又摇晃着秋天的力量
高大的白杨和细弱的庄稼
秋阳中闪亮的立体画面
马车缓缓行驶在昌黎大片的葡萄园外
这温暖又忧郁的老式景像
在喧嚣的光线中还能站立多久
对面的老人在无故地垂泪
斜略过的树影遮盖着那些幼小的动物
三十岁的身体发出锈蚀的声响
乡间的墓群急速的成为秋天的阴影
尘埃中干化的浆果和霉味的落叶
曾经,承受着怎样坠落和失重的挣扎
等待下车的民工狠吸着劣质烟草
紧紧攥在手中的行李揭开了局促
而黑暗已经降临
海口的拖拉机和颠簸的南方女人
海口的美兰机场,充满了热带的风浪
而此刻,我们在去机场的路上
我们应该是到了郊区
低矮的房屋烟火缭绕
农人的蔬菜和奇形怪状的热带水果
而我更惊讶于身后的那辆破旧的拖拉机
颠簸的女人和那个衣服脏乱的男人大声叫嚷
我听到了,海浪的声音,拖拉机的破嗓门
这个南方女人,我永远听不懂的方言
我北方乡下的好哥们,每天开着同样的拖拉机
车上没有水果
满车的水泥和板砖
像土拨鼠一样不见天日
躲避着路卡和蓝色的帽檐
我不会再幸福或痛苦
不会在破旧的拖拉机上颠簸
但我童年的花格外衣还在,在潮湿的柳皮箱中
躺成人的形状
谁能不在秋天有所怀念
谁能不在秋天有所怀念
京郊车站的高压线割裂着落日下的天空
收割后的旷野,幼小动物的身影在其中闪现
曾经熟悉的乡土路布满这草梗和新鲜的粪肥
列车的铁臂拉扯着往昔的记忆
母亲仍在每个清晨
打扫着庭院,落叶和灰尘
父亲骑着老式的自行车,他们是几十年的老搭档
四村五里的牲畜等着他的治疗
冬日来临的时候
少有的空闲点亮老年的额头
满屋的烟草味呛得人欢快地流泪
父亲每次打电话给我总是念叨着母亲
她仍每天挂念着他的小儿,三十岁的大学教师
面对着偌大的北京
却不能面对母亲梦中低烧的额头
现在是四月
现在是四月
人们开始在房顶清理油腻的烟囱
清水开始灌溉麦田
这一切是多么熟悉,又是多么陌生
火车正在经过华北平原
田塍上的农家孩子正在远处眺望
这多像我的童年
而不远处正是我的故乡
四月的菜田青青
翻着水花的机井在突突作响
呼啸的列车
却整整覆盖了京郊的这个下午
写给两位女性与另一个
黑暗的楼道和午夜的敲门声
是否构成一场暗示
你们
错乱的书籍搭配着高脚杯
堆放的内衣和零食纠结
你们欢快清脆的笑声摇亮我模糊的往日灯盏
你们也谈到了我的妻子
尽管明天
对美丽妖娆的女子我仍心存二意
我们
都来自遥远的海滨城市
语言比河蚌光洁
长喙的水鸟单刀直入豁开脆弱的主题
窗外飘起最初的一场冬雪
你们轻声欢叫
精巧的鼻子贴紧碎花的毛玻璃
可是我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