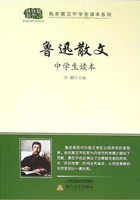1914年10月
据说日本7000人的增援部队已经抵达。整个上午日本人不停地从海面上进行轰炸,中间只有短暂的间歇。下午2时左右,伊尔蒂斯山、第一步兵堡垒和(坐落在阿里文住宅后面的)海防指挥站被敌人的炮火击中。仅是海面的敌军舰艇就发射了240枚炮弹,但没有造成值得一书的损失。此外,伊尔蒂斯山和第一、第二步兵防御堡垒都遭到了敌军从地面发起的轰炸。透过楼上的窗户可以看到日本军舰发射炮弹船身震颤的景象。
下午出现了很大、很明显的日晕景观。
夜里飞来了一架日本飞机,从它发出的嗡嗡声可以知道它一定飞得很低。然而透过暮色的月光却依然无法看见它,它却从不知何方的黑暗处投下了炸弹。
1914年10月30日
凌晨,红十字会的一支分队去湛山照料伤员。但他们却空手而归。原来村里的居民都被转移到了一个小岛上,以躲避炮火的袭击。一整天伊尔蒂斯山和第一步兵防御堡垒都遭到了敌军舰炮的猛烈轰炸,其他的军事要塞也遭到了陆炮的袭击。湛山村的房屋被炸成了一片废墟。但我们的要塞并没有受到实际的损害。下午我坐在图书馆里进行翻译工作。当我从伏案中抬起头时,发现老旧的“猛虎”号炮艇正遭受敌人陆炮的狂轰滥炸。
这艇炮艇已经派不上什么用场,所以整个战争期间一直都被遗弃在小小的港湾里。人们之所以没有把它与“鸬鹚”号、“猞猁”号和“伊尔蒂斯”号一同于9月28日炸毁,是因为觉得它的纯水蒸馏器在一旦发生缺水的情况下还能派得上用场。因为昨天敌军轰炸的缘故,所以人们把这艇炮艇拖出了港口,停泊在水雷库房后面偏北的方位。但现在它再一次遭到了来自孤山方位的轰炸。但敌人的轰炸明显大失准头。尽管敌人向炮艇连续轰炸了数小时,而且炮艇自始至终一步未挪,但绝大部分炮弹纷纷落在了炮艇四周的水域里,溅起很高的、带着光亮的水柱,而炮艇却只挨了两枚炮弹,其中一枚炸去了它的一个烟囱。当轰炸暂告一轮后,炮艇仍然静静地泊在原地。船员们早就离开了炮艇,全部补充到了海军连队。只有3个打算趁着炮艇无人看管之际顺手牵羊的中国小偷在轰炸期间一直待在甲板上。这些倒霉蛋该有多么害怕呀!也许很少有比以这种更为间接——因为这几个小偷并没有真正受到什么伤害——和更为幽默的方式惩罚犯罪的了!
晚上留在饭店里吃饭。饭店全部被德国红十字会占满了。我们围着一张小桌坐了下来。单从晚饭就可以看出目前所处的战争状态。匆匆忙忙扎起来的花束耷拉着脑袋插在花瓶里,那副蔫蔫的样子更像是一堆野草。毫无装饰的墙壁将我们熟悉的俾斯麦侯爵石像的胸膛映照得更加苍白。大厅里弥散着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极不舒服的气氛。
有人说起医院的一些护工在战斗的前沿地带被捕后今天却又都被放了回来,“因为他们可能即将迎来繁忙的工作”。日本军官们甚至还在与这些护工分别的时候送给他们一瓶白兰地酒。
此外,还有许多真假难辨的消息四处流传,如果完全听信这些传闻,所有海军部的官员都应当被逮捕。还有的说,一些日本军官在德国军官里有熟人,并偶尔会给他们提供一些情报,例如“我必须要把您团团包围,这让我感觉非常遗憾。所以我每天都往胸口划十字,祈祷您不要受伤”。
1914年10月31日
深夜,德国方面把“猛虎”号自行凿沉了。天刚蒙蒙亮时,日本人新一轮的轰炸又开始了。炮兵弹药库、后勤给养部和天文台附近都遭到了炮火的袭击。炮弹呼啸着从我们的屋顶上飞过。早晨7点半,造船厂中弹着火。过了不久,标准石油公司和亚细亚火油公司的两个储油罐也先后被炮弹击中,两道黝黑、巨大的烟柱拔地而起,直冲云端,四周烟雾腾腾,熏染了整个天空,就连太阳也显得苍白无光,仿佛出现了日食。浓烟穿过了整个胶州湾,并渐渐减弱,但仍然熏黑了海湾里的海水。在海湾的尽头,一个日本人的阻塞气球徐徐升起,但却在德国榴霰弹的射程之外。同时还有一架日本飞机飞了过来,但此时已经没有人再关心它了。
中午,日本人往大鲍岛扔了6枚炸弹。人们看着炸弹往下坠落,每时每刻都等待着看哪里又中弹着火,但每一次又都是云消雾散。整个下午青岛、大鲍岛和台东镇都遭到了猛烈的轰炸。
医院挤满了伤员,或在动手术,或在包扎伤口。我走过去安慰这些伤员,并给他们一些喝的,他们对此深受感动。许多伤员大腿骨折,还有一些人的腹部中弹,有一个人的一只胳膊必须要截肢。等待区的地面上堆积着好几大摊鲜血。这些伤员最终全部得到了治理,并被送上了病床。但长夜漫漫,过得十分辛苦。所有的伤员全部起了高烧,有的伤员因此还大发谵妄,狂躁地将身上的绷带撕扯开,并剧烈呕吐。另一些伤员躺在床上疼得直哼哼。太多的病人需要抚慰了。但我却在身边明显感受到了上帝的神助。许多病人非常虔诚地抓住神灵的帮助不肯撒手。
吃晚饭的时候,索伊弗特先生又过来和我们讲述了外面被轰炸的场面。俾斯麦兵营、毛奇兵营和兵营外的活动平房以及日耳曼啤酒公司,特别是台东镇和驻扎在附近的奥匈帝国军营都遭到了严重破坏。但陆军阵地的地下掩蔽部仍完好无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