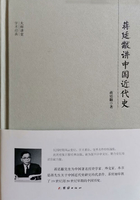焦躁,无法平静下来的焦躁。脑海里不时的会响起那声声的尖叫,还有那刺耳的刹车声,谭文柏即使再冷静也无法抑制内心的害怕。
这种害怕还夹杂站自责和懊恼,在她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不能第一时间站在她的身边,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时刻萦绕在他的心头,让他无法平静。
文沫醒来的时候,映入眼帘是她熟悉的景色,她所住的酒店房间。她的脑海有一瞬的空白,浴室传来的水声刺激到她的听觉,空白的一瞬刹那间闪过片段的记记。
咖啡厅,释总,弗德尔,还有酒……酒……她陡然之间睁大眼睛,刷的一下坐了起来,倏地发现自己未着寸缕,那一刻她整个身体都僵硬着,一股冷意自四肢漫延,整个人如同掉进了冰窟里。
冷,好冷。
她下意识的拉紧被子包裹着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手臂上的痛意又不时的刺痛着她脆弱的神经,刺激着她的记忆。
她记得她想要逃走,被弗德尔抓了个现着,然后她怎么做了?伸出手臂她目不转眼的望着手臂上即时过了一夜伤口还很鲜红的牙印,那片段的记忆慢慢拼凑起来。对,后来,后来她晕过去了,然后……
她突然抱着自己的头压抑不住的颤抖,她不记得了,完全不记得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想到了那个电话,文柏的电话,眼泪就这么不受控制的流了下来。
浴室的水声停了下来,文沫下意识的拉紧裹着自己的被子,抬头望着浴室门口全身紧绷,脸色瞬间变得毫无血色。
门轻轻的被人拉开,只裹着一条浴巾遮住下半身,赤着上身的释然就这么出现在文沫的视线里。
他的头发还在滴水,赤着的上身有好几处被抓伤的痕迹,深邃如同海一般的眸光在对上她的眸光时有片刻的凝滞,只是一瞬便恢复清明,然后当着她的面套了件上衣,再然后……
文沫撇开了视线,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
“释总,回国之后我会以文件的形式解除我们之间的合约。”
不管昨天他处于什么样的角色,她都没办法再与他一起共事。
套上长衫长裤的释然走到文沫的跟前,清亮的眸落在她的脸上,让人摸促不定的表情,沉默一会的说:“先去洗个澡。”
文沫倔强的与他对视,并不所动。
释然挑眉:“是想让我帮忙吗?”
文沫一僵,最终妥协的裹着被子跑进了浴室,褪到被子然后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手臂上的几处咬伤尤为清晰,身上的表紫交错,当看到脖子上几处映着暗黑色的唇印时,她的情绪终于崩溃。
打开花洒,双手环抱着自己慢慢的蹲下,任由着水冲在身上,她的脸上不知道是水还是她的眼泪。
许久,她站了起来,一遍又一遍的清洗着自己的身子,擦到皮肤泛红,又到发白。
释然站在窗前微微垂着头,手指间捻着一根烟,神色讳莫如深。
半个小时过去,浴室的水声还在,他的眸光一眯,将早已燃尽的烟头丢到烟盅里,大步的走向浴室门口,沉声道:“文沫,给你一分钟的时间出来,一分钟不见你,我会破门而入。”
话音一落,门打开来,一脸苍白的文沫站在门口,哭红带肿的双眼冷漠的看着释然,然后从他身边掠过拿了一只矿泉水,打开喝了一大口。转头淡漠的瞧着释然,她冷笑的道:“释总,满意了吗?”
释然眯了眯眼,被她淡漠不带任何感情的眼神瞧着心口莫名的堵了一口气,上不上下不下。
“有烟吗?”她坐在沙发上突然问他。
他皱眉。
“给我一根。”她说。
释然走到床头柜从烟盒里拿出一根送给她,压下心头的不舒服感觉,淡淡的道:“文沫,我们谈谈。”
连称呼都变了,文沫自嘲的笑道:“释总,想要谈什么?”
她并不觉得他们之间有什么好谈的。
释然帮她点燃烟,看着她捻着烟并没有吸上一口,而是夹在两指间低垂着头,因为看不到她的神色并不知晓她的想法,只是她这样的态度让他心堵。
是,他承认,他对她动心了。
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不知道,只是从昨天他才确定对她有了超乎男女之间的感情,这种感情容不得她受到任何的伤害,包括昨晚……
他愿意为他心动的女孩放下身段,于是接下来他说了一大串:“我没有不良嗜好,只是偶尔抽烟。偶尔也会泡夜店,当然我可以保证从今天开始不会再有。文沫,我会对你负责。”
文沫饶是再淡定也因为他这个表白而怔愣了片刻,反应过来她讥讽的笑道:“释总,我并不是什么贞烈女人。我不否认刚开始不能接受这一切,只是事情发生了,我不可能改变。一夜情而已,没什么大不了。”她垂着头,语气淡的不能再淡的说:“大家都是成年人,一夜情而已真的不必太意。”
一夜情而已!
释然看着垂着头的文沫,深黑的眸如海浪在翻滚,双手紧握拳头松开再握紧,压抑着心头那不识滋味的心绪,哑着声几乎是咬着说出三个字:“一夜情?”
“释总,真的不必太在意。”
文沫突然抬首直视着释然,她的眼神出奇的平静,平静到释然狼狈的避开了她的眼神。
“如果释总愿意看在一夜情的情份上,那就解除我们之间的合同。当然,该赔偿的我一分都不会少。”
他脸色一沉,松开的双手又用力的握紧拳头,喉结动了动几次想要开口却又咽了下去。许久,他的嘴角泛起一抹自嘲的笑:“很美好的一夜情。”语气一顿,一字一字的道:“文律师,一夜情是没有情份的。”
所以,合同不会解除,他也不会解除。
因为他知道,一旦脱离了工作上的关系,以她的性格他们之间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他怎么可以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她不知不觉中将他的心拐走了,她怎么可以甩手走人!
文沫,是你先惹我的,哪怕没有爱情,他也要让她记住他。
原来,他的爱会是这么的极端。
“文沫,我们来日方长。”释然说完,转身走出了房间。
文沫目送他离开直到房门将他隔开,绻缩着让自己深陷在沙发里,有种深深的无力感和挫败感,还有无助。
她想放空自己,她很想静下心来思考,更想昨晚的事情什么都没有发生,然而身上的痕迹,无法冲洗掉的痕迹让她没办法自欺欺人。
她想到谭文柏。想到文柏担忧着急的一声声呼唤,揪在她的心头如同散不开的阴霾,没办法再故作镇定,眼泪无声无息的顺着眼角滑了下来。
文柏,文柏,文柏……
默念着他的名,一遍又一遍,她哽咽的低喃:“对不起。”
对不起,我暂时不能面对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