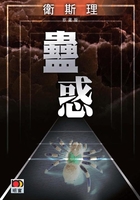——不好,山火!人一惊,听觉敏锐了,他先听见几声藤竹的毕剥爆裂声,视线难及之处,传来一片听不清辨不明的异响。夏日雷暴天气,热带山林最怕这种骤起的野火了!可是连日大雨,空气湿重,一整天山里头也没起过雷暴呀!莫非是儋州佬、黎胞猎户烧火轰赶山猪?——这常常是当地引发山火的另一种由头。正这么想着,果真有一片像是山猪拱林的杂沓响声迎面而来。他喝住惊惶的牛阵,一弓身,几个大步跃上前去,却像有一阵热浪扑来,他被呛得连连倒退了几步——有人?!错愕之间,只见火影浓烟之间冲出了一个黑影,怀里鼓鼓囊囊像抱着一团什么东西,一见他,哇哇惊叫了两声,一个趔趄仰翻在地上,嘴里连连叫着:火!火!火!……
定睛一看,那个身影却又一纵身,扑通一声消失在烟雾里的一片水声之中。路北平大吃一惊,才发现脚边不远处竟是一汪水潭。——不知什么时候,他和他的牛群悠悠转转,又转回到第三道河曲尽头的那个小水潭边上了,简直像是神差鬼遣一般!
没由他多想,那个滚落水潭的身影已经爬起来,却是赤裸着上身,挥舞着湿漉漉水淋淋的上衣又向烟火冲去,嘴里仍在大叫着:火!火!火!……
路北平一时无法辨清他的脸相,也顾不上迟疑,抄起腰间的砍刀噼里啪啦砍倒一棵小灌木,顺势在水潭里浸过,拎着水珠弹跳的树枝便向火场冲去。
山下的钟声,忽然痉挛一般地急响起来。
这已经不是路北平第一次遭遇山火了。往常由雷暴引发的山火总是来势汹汹,呼啦啦连天接地地逼人吓人,非得火路、水路的一起上不能平息的。“火路”就是用人工放火烧出一片火场隔离带,“水路”即是使尽惯常以水克火的所有能耐。
眼前这一场火显然是小范围突发骤起的,大概是连天大雨的缘故,火场上四处是烟,火头并不凶猛。他挥舞着湿淋淋的树枝左拍右打,呛人的热浪里听见另一个声音也在霍霍地抽打着灭火,一边打还一边胡乱喊着:火!火!火!却看不清彼此的身影面相。很快,浓烟里响起了杂沓的脚步声。显然是山下的钟声招来了正在四面胶林干活的农工,一通手忙脚乱的扑打,火势很快就被控制下来。火头迅速被断了路,只剩下这里那里的焦枝埋着的暗火,隐隐还吐着红焰。
有人用胶桶从水潭里提来溪水,滋滋地浇灭各处的残火。浓烟渐渐消散,路北平环望四周,想分辨出刚才那个冲出烟火又滚落水潭的身影。眼前浮动着的都是割胶班、林段班闻声而来的灭火人群,刚才那个突兀的身影,却再也找不见了。队长的响锣大嗓却从烟气涌动的另一头传过来:
肯定又是那些赶山猪的儋州佬惹的祸!队长喝问,是谁最先发现的山火?是谁?——
路北平等着那个最先从烟火里冲出来的身影应答——那年头,这或许是一个可以立功受奖、出人头地的大好机会,谁都愿意争抢这一功的。
可是,没有人应声。
奇怪,没有人抢头功?一边问着,队长魁梧的大个子从烟气里晃了出来。
路北平听见有人怪声怪调地笑道:抢头功?就怕抢着个“阶级敌人纵火”的罪名哩!——那是朱弟,从来口无遮拦的朱弟。
朱弟你胡说什么?队长哈哈大笑,——那肯定,你就是那个阶级敌人!
不敢不敢!得了麻风病我也不敢!朱弟大叫。
大家伙儿于是推搡着朱弟起哄:是朱弟啦,就是朱弟啦,是功是罪,反正都便宜你啦!
哄闹中忽然有谁说:可能是阿路吧?阿路在这边山放牛,一定是阿路先发现这山火的吧?
众人的耳光一下子聚到放牛郎身上。果真,路北平身上的烟迹黑道,最浓最重。
不是我。路北平大声应道,迎向队长:我的牛正在野林子里迷路,先看见有一个人抱着什么东西从烟火里跑出来,才知道发了山火的。
人群哗地大笑起来:哇!可不是真有个什么阶级敌人吧!
怀里抱着东西?队长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阿路,那你看清是谁了?
没看清。我远远看见他跳进巴掌溪弄湿了身子又跳起来打火,火势是他最早控制住的。
哇!英雄英雄!朱弟在一边大叫,那我,就算是那个战胜阶级敌人的灭火英雄吧!
又轮到你作怪?朱弟!队长喝道,声音里却少了刚才的戏谑,不知为什么变得严厉起来。他的目光在人群里溜了一圈,忽然在什么地方停住了,皱皱眉,响声说道:阿路,这头功算是你的!若不是你砍倒了树枝做灭火扫把,这火头是压不住的!阿路,我要为你通报嘉奖!
是阿路啦!那就是阿路啦!人堆里又哄闹起来。没的事!路北平憋红了脸,真不是我!我犯不上领这个赏!他抗顶着朱弟和几个知青在背后捣弄的手脚,忽然指着人群发作起来:丢那妈!又不是做贼!刚才那个人是谁?那个跳落水潭的家伙……你你你,有种灭火,你为什么不敢站出来?!
路北平的火气来得突然,农工、知青们一时面面相觑。哎哟,当上了队长女婿,果真声口不同。朱弟还在嘻嘻笑着说怪话,没想到路北平一巴掌扫了过来,迎头给了他一记大耳光:丢你妈的朱弟!要领赏你去领!要当英雄你去当!
朱弟被这突来的巴掌打迷糊了,刷地白了脸,抄手就抢过谁手里的锄头:你他妈的阿路!你是喝了牛尿还是马尿?鸡巴上树啦?
两人很快就被众人架开了。扑灭山火的兴奋一时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斗殴变得扫兴万分。队长只好呵呵笑着出来打圆场:嘿,学生哥儿,你们还真是说变脸就变脸!
——朱弟,你就别捣乱啦。——阿路不肯居功,精神可嘉,精神可嘉!可是牛脾气也够大!大家散吧,散吧!
人们推拥着还在骂骂咧咧的朱弟,四散开去。路北平一脸无趣,想起他的牛,挣脱着从人堆走出来,听见几位农工一边走一边窃窃私语:怪呀,为领赏也要打一场,这山火发得古怪呀……队长最怕发山火了,这山火可不就是他的心病吗?……
山谷里暮色四合。牛们已经东一声西一声哞叫着呼喊着主人,为急着归家回栏鼓噪着。路北平喝了几声牛,忽然从身后四散的人堆里瞥见一个浑身湿透的身影,觉得眼熟,几步追了上去。那人闻声慌慌回了一下头,又急急挤进人群,遁逃而去。
借着烟气暮色,这一回,路北平总算认出了绿军帽下那张失措的脸——天巧地巧,那是队长的宝贝儿子、他这个“阴府女婿”的“小舅子”——平日三脚踢不出一个屁来的阿荣。
天顶的蛇云渐渐暗淡下去。——阿荣?路北平一边吆喝着牛群,心里一边敲着小鼓。蓦地又发现了另一番惊奇:轰着牛阵踏出野林子,他看见临近水潭那片火场余烬的黑枝炭条下,隐隐约约,撒着零零星星的米粒!
——白米粒!这里怎么竟会有白米粒?!
路北平一惊,这才想起适才的迷路,想起刚刚陷身的那片让人迷迷糊糊又黏黏糊糊的野山谷——那也许就是村里人说的鬼影憧憧的“倒米谷”?——这是从那个“倒米谷”里冒出来的白米,还是什么人在水潭边求神做法撒的白米?刚才那个从烟火里冲出来的身影,怀里抱着的是什么东西?这白米,又和那山火、那家伙、那东西有着什么于系?这么想着的时候,他闻见了一阵像是焦煳的米浆味一样的雾气从水潭上飘过,雾气里传来了溪水拍打崖角发出的呜咽一样的水声。他从涌动的牛头间回过身去,想用目光再打量一眼刚才那片让人迷瞪瞪的谷地——奇怪,眼前落霞飞渡,胶林肃立,那个长满瘤根、猴头木菌的谷地——连同那片湿漉漉的雾气,完全消散了,倏忽不见了。仿佛就像什么人的手背一掀,就把整片山崖水曲变走了,又变回来了。
落霞里,他听见牛们欢快的哞叫声。
3
才是十天半月,他这个“牛司令”已经当出点谱儿来了。
他现在的装束,很像城里那些昼伏夜出的管道工人:长袖工作服上上下下的袖口都用草绳捆紧密封着,不单是为着防蛇虫,更为着对付海拔三百米以上,热带山林常见的会吸血的飞蚂蝗。老农工里有过各种可怕传说,说那些像是发育不良的小蚯蚓似的东西,见缝就钻,要让它钻进了肚脐眼里、女人的阴道里、男人的屁眼里,可以一声不响地把人吸血吸成个僵尸。六月的毒日头,他脚上还得见天套着胶皮雨靴。山里风湿露重,往往每天早晨赶牛出栏,牛还未走出村口的两碗坡,他就一身上下全被露水打湿了,长筒胶鞋就成了膝盖关节的惟一护卫。加上海岛夏日,有云即雨,几乎每天都比前一天迟一个钟点的“定时雨”,下起来劈头盖脸,来去无踪,在巴灶深山更常常蕴发出大雷暴来。有时劈得半边山都是火光,头顶的大树转眼成了焦枝,那绝缘的胶鞋,真的就成了他的救命鞋。
热,倒不太算个大事——他忽然明白了,人的忍耐力其实有多宽的尺度:往日干林段活儿让他打赤膊也热得受不了,如今这样封得严严实实的,他倒可以躺在毒日头下眯一个小午觉。可是,受不住臭。不是熏鼻的牛粪臭,是脚臭——连同他自己,任是谁,也受不住他的脚臭。你想想,风里雨里日日闷在长筒胶靴里走路,那鞋筒子可不就是一个日夜发酵着的腌菜坛子?每天下工,他把雨鞋一脱,将里头积的小半简的汗水往地下一倒——哗,土坷垃间简直可以浇出洞来,蚂蚁甲虫可以被活活浇死!牛高马大的牛党们,常常都要被它的滚滚臭浪熏跑。头几天傍晚下工回来,他拎着一双胶鞋进屋,熏得知青排屋里鸡飞狗跳的。朱弟便话里带骨头地骂他:端什么队长女婿的臭架子,鬼臭鬼臭的!他忽然从这“鬼臭”二字里,寻着了一点报复的乐趣。每日下工,赶牛群进了栏后他便坐在村口宽衣脱鞋,示威似的拎着一对“臭咸鱼”招摇过市,逗引出一村的野孩子捂着鼻子追在他后面。有时候他干脆用那把长柄砍山刀,挑着那两只臭雨鞋——他对朱弟说,林冲逼上梁山,就是这个样子挑着酒壶的——大模大样地踢踏着脚丫子下到井台去洗脚,臭得那些下工梳洗的知青女生们叽哇鬼叫。老光棍阿金听说了,常常会追到井台边上,冲着他背影忙着向那些城里水嫩的女仔们献殷勤,怪声怪气地喊:臭牛仔哎,等着娶我老阿金挑剩的老婆吧!
痛快淋漓。他感觉到一种少有的快意。他还给牛们起了各种各样的洋名字:“保罗”、“彼得”、“安东尼”、“玛丽亚”、“亚历山大”、“阿列克塞”、“马克辛姆”什么的,都是他从带在身边的杂书——《圣经故事》或者苏联、西欧旧小说里随时搬来的名字。这在那年头有点犯忌,可吆喝着那些别扭的洋名字,不知为什么偏偏就有这么一点小小的“冒犯”的快意。“彼得,跟上队伍,开什么小差!”他挥舞着手上的细树枝,吆喝着那头黑牯牛。“约翰!你长眼睛了没有?尽往沟沟洞洞里栽!”他一手攀着小灌木,另一只手揪着那头花毛独角牛的小弯角,把它拽上来。“安东尼”是他最偏爱的一头褐红脸、白鼻梁、长得像匹马驹似的小公牛,偏心认定它就是那通人通灵的“众牛之神”;而那头总是喜欢离群独食、行迹诡秘、老让他悬心的驴脸老牛,他起了个名字叫“犹大”,把他视为面相不祥的“牛中之鬼”。
“亚当”、“夏娃”却是在很久以后才被他命名的,那已经是有人把他这些出格的洋名字报告给了喜欢“操正步”的班长以后的事情。阿芳大概听说了什么,那一回捂着鼻子装得很偶然地在村口撞见他——半月不见,“知青女皇”更见风情万种了,用她一贯讨巧的大惊失色的表情问道:哎呀,你这牛司令的圣经里,怎么独独没有“亚当”和“夏娃”呀?这里有什么讲究呀?
他喊了一嗓子,把慢腾腾落在最后的“犹大”吼进牛栏——阿芳尖叫着往后一跳,他冷笑道,咳,有什么讲究吗,这年头,人家那边的世界是先有了亚当、夏娃,才有基督、犹大,咱们这里么,是基督、犹大老的老了,死的死了,才能生出个亚当、夏娃!
阿芳脸一红,说:你反动,你话里有话!
那你告我吧,他慢悠悠说道,找你的入党介绍人班长同志告我去吧。
还没脱鞋,他已经把她臭跑了。
——他说他不在乎,其实他顶在乎。
朱弟早向他通报过的:在他赶牛入山后的第某天,阿芳在团支部的什么活动里郑重宣布,班长现在是她的入党介绍人。
眼不见为净。他需要把自己放牧得更远。
他在巴掌溪第三个指头的河曲间,搭起了一个简易的牛栏和窝棚。从村口往山里走,出工路又多了半个钟点。借着这个理由,他向队里提出,为了不让牛们吃饱了在路上“跑膘”,往后收工,就把牛群圈在山里的牛栏,他自愿住进山里的窝棚守护,多长牛膘,还保证不减少肉牛们的“存栏量”。好哇,队长慈祥十分地笑着说——这个“哇”字在他听来像是样板戏里少剑波的声口:大战红五月,这是你拿出的实际行动吧?很好,这样做很好。路北平木着脸听着,感觉到他的决定投合了队长某种隐秘的愿望。本来往年入冬,山外草稀,队里是有圈牛进山越冬的先例的。今年正逢大战红五月,四面砍荒的人声惊得牛群不肯认真吃草,这成了队长顺理成章首肯路北平提前圈牛进山的理由。你让司务长给你称一点米和油,队长说,到仓库去领一盏马灯、一件雨衣、一把手电和一套工作服。火枪你不会使就算了,老金头以前倒是配给过他。我想巴灶山里现在除了山猪和黄獍,没什么需要动枪火的野物了。那巴灶蛇怪说得天龙地虎的,你也不必信它。
队长似乎不避“鬼女婿”之嫌,站在村口这么絮絮地对他说着。
隔了两天,队长派人拉了一牛车茅草进山去,帮助路北平加固好了他的窝棚和牛栏。
真是同煲不同柄,同人不同命呀,回到林段班干活的老阿金,逢人就这样抱怨说。
4
无梦之谷。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驻进深山的头几天,路北平就为巴掌溪第三道河曲里的这片谷地取了这么一个文绉绉的名字,其实,是为着平衡自己内心里被雄野的山林逼压出来的无尽怯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