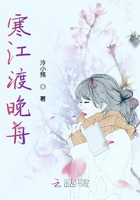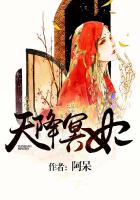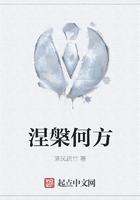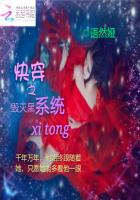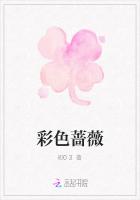我曾从类种角度(本文类种仅指以表现对象为区别的作品)得出中国画历史的这样一个兴衰格式: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个模式之下潜伏的一个如此事实:艺术史上的类种发展,并非像生物的生命那样,依据一个从萌芽、繁荣、衰亡的简单嬗变兴替规律,它也并非是在假想的球体上分布的无数圆的循环。那瑰丽的宿命神话(指西西弗斯的命运故事)对艺术现象的比拟与客观存在的实际把握也有大的距离。与其说这些假说是对历史发展模式的描述,倒不如说这是现代人一厢情愿地把主观情绪弥漫在中国画这块净土上,以“科学”的幻影笼罩其上的结果,不仅诱惑了读者步入这些概念与逻辑交织的“百慕大”,即使作者本人亦陶醉在自我编织的神话里。这便是文化观念对于绘画理论研究过分侵入所带来的副作用。理论模式的泛滥和体系的廉价,导致了以狭窄程式容器挤压纷繁艺术现象的情况发生。
然而,就在我们对于艺术接受文化观念、哲学思潮的副作用进行检讨的同时,却也对这么一种约定俗成的“存在”而感到惑然:艺术史上通常出现由于文化观念的介入而使已有的历史“定论”发生斗转星移的改变。在对中国绘画发展史的把握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么一种情况,不少研究者有以唐宋为高峰,明清衰落,现代将进入复兴的结论。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艺术史本身的类种发展并非一致地以时代发展为指归,它本身成熟与否的标准具有强烈的相对性。如果说冥冥之中具有一条标准,那也是由于理论家在某种文化观念左右下的产物,它可以使“存在”成为合理。文化观念的干预往往会使艺术由原来的自转轨迹不自觉地加入“陈仓暗度”的成分,从而在茫茫的历史海洋中被莫名其妙地改变了航向。这便是文化观念在绘画历史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
正是由于绘画史不能摆脱社会发展史的笼罩,才使我们如此慎重地对待文化观念对于绘画入侵的两重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对于绘画本身相对自律特点的探讨。
在中国的原始社会,绘画作为宗教、文化观念及实用美饰的实现与工具,它们是共同存在并有共同特性的。春秋战国之际,曾出现过以书法及骑、射、数等六种技能组成的“六艺”之说。这当然距离我们现在理解的艺术内涵十分遥远,它只是礼仪和技能上的观念的具体体现。孔子的“绘事后素”及《论语》中的某些绘画论述,也只是对朴素礼仪观的实践的一种阐释。甚至到了秦代韩非子仍是:
“……狗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不罄于前,故易之也。”(《韩非子》)
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待绘画,依然仅停留在朴素的客观传达之上。至汉代,绘画更加广泛地走向世俗。保存至今的大量汉画像砖石便大多是殡仪活动的副产品。然而,就在这些集体意识活动的礼仪观念作用的图像中,已经有了独特的造型观和空间感受。这些也就成为日后绘画艺术走向类种区分的可靠借重契点。凡此种种,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当绘画在外来作用下进行实现的时候,当它受制于文化观念的左右时,其自身的嬗变规律也已具备,这也是由绘画这一手段本身的特性所具备。然而,若从文化观念的影响来讲,此阶段的绘画尚未进入真正的艺术期。这正是把绘画史作为进化论链条观的一种看法。但是,如果我们把此时的艺术现象作为独立的观照系单独抽出,那么我们所感受的便不仅是一种成熟与否的现象。这当然是艺术自律还原论和动态观的阐释结果。从另一角度看,站在宋元山水的立场上进行观照,中国画确有“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稚拙阶段。这也是不容回避的。
我们前面在对唐以前绘画现象的论述上,旨在说明这么一种情况,艺术本身的发展,成熟的标志带有强烈的随意性与动态性。而这些“偶然”,主要由于绘画本身的自律协调于文化观念的“侵犯”而成为既成事实。
从卷轴画被作为一般绘画史阐述的重点来看,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的支持:一是作者背景的透明性及作品的可考据性,二是对笔墨这一中国绘画形成的重视观念。而我们也将无一例外地把卷轴画作为类种分析的对象。
从画的类种方面来考察中国绘画的兴衰的方便,可以从两方面显示出来:一方面类种之间的本来成熟具有较大的逆差,另一方面可以由对象的差别见出表现的差别。当然,它们之间亦存在着这样的不便:重叠性上的复数律与类种交替上的剖离。
从人物画的数量上来看,汉、唐的确是发展的高峰期,我们不能回避汉代画像砖石以世俗生活及巫术神谶的表现目标,它除了在以现实生活作为对象进行表现,还包含着充分发挥作者的智慧才情。独尊儒术的社会环境导致了礼教艺术的盛行,而其挟带而来的天人感应式迷信又导致了对彼岸世界的神秘臆测心理发生。在这种心态下,汉代的人物画发展到一个迷幻而瑰丽的阶段。
唐代人物画的兴盛离不开唐初对于盛世帝国统一后的彰功立表和“法”的成立。但它同时又有足够的度量去容纳其对立面。在书法上,反映出楷书的规矩严谨与草书的不羁倾泻的两极呼应。这似乎同时给人物画以这样的暗示:在人物对象描绘上遵循“法”的约束,但同时亦可以在这种特定规范中,注入艺术家个人的“图式”因素及性格体现(如“周家样”、“吴家样”)。“法”本身也由此而成为一种理性与智性的凝缩体现,成为艺术家情感依循轨迹与反叛“法度”的参照体系。
在这种情况下,唐代产生了大量的人物画杰作同时也造就出一批伟大的画家。如吴带当风(吴道子)、历代帝王的以形写神,以色貌色(阎立本)、贵族仕女的出游及闲逸(张萱、周昉)以及难以估测的王陵墓室壁画。仅从我们见到的几个公主太子墓道两侧的精美画卷可以看出,人物在唐代显然是世界的中心宠物与主体,盎然生机的自然被人所欢娱玩赏。这在代表着高水准的人物画创作中,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物画这个类种在唐代已达到了博大精深的程度,这在绘画本身的史迹衡量上,具有不可逾越的特性。人物本身造型、服饰、美学上的雍容与开阔的气象,均可以明白无误地说明唐代这个历史机缘于人物画的时代,无论质或量上,都是后世所难以望其项背的。
人物画类种题材由五代进入北宋之后,不能否认亦有些许大家出现,如五代顾闳中,宋代李公麟、张择端等人,甚至在中国社会历史上都占一定位置的《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等都在此际产生。然而,与更多数量和杰作迭出的山水画相比,它毕竟只起到一种“调味品”的作用。数量上的衰竭亦使我们不能不慨叹它的凤毛麟角。从理论上来讲,唐前多侧重于人物画的阐述,从谢赫专指人物描绘的“气韵生动”、顾恺之的“以形写神”到张彦远的专指人物画的“书画用笔同矣”的线描理论,以及在《历代名画记》中对“顾陆张吴”历史地位的确立可略见一斑。
而在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中,则明显地扬山水而抑人物,他这样说道:
“或问近代至艺与古人何如?答曰:近代仿古多不及而过亦有之。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顾陆张吴中及二阎,皆纯重雅正,性出天然,吴生之作,为万世法,号曰画圣。不亦宜哉?张周韩戴,气韵骨法,皆出意表。从之学者,终莫能到,故曰近不及古。”
与此苟同,元代赵孟頫对于唐宋人物画的差异也有论述:
“宋人画人物,不及唐人远甚,于刻意学唐人,殆欲尽去宋人笔墨。”(《赵孟頫·论画》,见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
人物画的表现进入元明清三代,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滑坡。除了在个别肖像画家那里有不同程度的建树之外,从整体上看,基本上呈现衰败趋势。明清以来,人物画更是羸弱不堪,缺乏生命底气的人物犹如衣架一般苍白。作为一种纯粹的笔墨与文化符号,它具有的只是不甚适宜的玩赏价值。无论如何,从文化观念介入的角度来看,此时的人物画只是一种处于被动接受与调整的局面,而不是主动的迎合。
山水画的源头我们在汉画像砖石中可以找到。在“成教化,助人伦”的人物描绘背景中,是可以依然窥见艺术家对于自然的拳拳爱心。当然,真正地把山水从人物的附庸地位中剖离出来,还应当说是在魏晋。玄言时代的山水画得以独立,文人们无不以自然的特征比附于自己的气质,乃至于宗炳为了预防老来不能亲善自然,而图佳山胜水于四壁以“卧以游之”。对于山水画的形成,我们不能仅仅视为一种景物类种描绘,它同时反映出文化观念左右的程度体现。也就是说,在山水中可以体现出某些道玄思想。正如左思所咏“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画家明确弘扬的便是来自自然深处的灵魂。我们如果以现存最早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来做参照物,便可以推测出山水画已达到了相当的程度。然而,隋至唐代这段时间的山水画从大的走势上看并没有什么质的改变。从展氏到大小李将军(李思训、李昭道)的金碧山水,只是在敷色上更加凝重华艳而已,它只是技巧上的递增,在表现观念上并没有什么改变。当然,这主要缘于晋至唐这个期间文化观念变化还没有波及到山水这块小小的版图上。后世所传王摩诘水墨山水的境界,从文化侵入角度而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后世追认及赋予的成分要大大地多于它本来的动意。
五代可谓是山水画中转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个阶段中,艺术家们发现自然景物的表现不但可以娱于个人的胸襟,而且还具有“比德”的功能。荆浩在其《笔法记》中有言:
“夫木之生,为受其性,松之生也,枉而不屈,如密如疏,匪青匪翠,从微自直。萌心不低,势既独高,枝低复偃,倒挂未坠于地下,分层似叠于林间,如君子之德风也。”
这就使得山水画具备了更加广阔的表达容量,加入这些伦理的因素,也使得艺术家在沉溺于这个虚幻的世界里会更加心安理得。
山水画在宋元之际发生了审美上的大程度嬗变。宋代山水画受制于表现对象本身的态势,艺术家们更多地着眼于从自然中发现。这也由此使得他们更多地注目于自然的细节与复杂的变相。像宋徽宗要求画工在孔雀升墩时亦要注意先抬左脚还是右脚。这固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足可以反映出某种倾向性。而进入元代之后,除了画面上纯净幽寒、高旷深远之外,表现形式上渲染与混合的皴擦笔迹明显减少外,笔画间独立的笔痕也相应加强了。书法的意义也由此更加昭然。从画家主体来讲,个性的抒发开始左右于画面成像的变化倾向,较为明显的是艺术家主观意志竟能使景物本身改头换面。这种根源可以在倪云林画论中略见一斑:
“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论画》,沈子丞:《历代论画名著汇编》)
在这里,山水画已达到它发展的高峰期。但是,应当说宋代的山水更符合山水画本身的自律嬗变轨迹。正是由于元代道、禅文化观念的过分介入,方使得山水画的自转发生变化。因此,在明代山水画家那里,出现了南宋山水的回归现象。不仅浙派如此,明四家中唐寅亦有明确的印迹。这种对于元画的反拨和隔代相承的作风,却并没有给明代山水的发展带来真正希望。确切地讲,明末清初最具创新意识的四僧山水,也更多地是挥发元代遗韵,而在清代四王手中,山水则蜕化为一种技法的集成性磨炼,这个极端使自然与笔墨符号之间的脱节达到了最高程度。犹若模型一般的山水构成,除了技艺显示之外,其内在精神荡然无存。在审美趋向上亦丧失了创造性的拓展。
汉代画像砖石中虽然也具有相当的花鸟描绘成分,但严格地讲,尚不能作为我们绘画发展模式的研究对象。它是以笔墨形式显示的“前时期”。如果我们把商周铜、玉器皿上的花鸟形象也包含在内的话,这个“前时期”又要拉长许多。但此阶段由于负荷了太多的“理念”,因而使得它与后期花鸟画自律发展上的距离太大。真正使这个类种得以独立应当说在唐代,因为在这个时期已出现了一些专以描绘花鸟而成名的画家。这在《历代名画记》、《图画见闻志》等书中均可见到。
但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不能认为唐代花鸟画值得我们大力推崇。主要原因就是它还处在墓室壁画的衬景及人物画的附庸和它造型上的幼稚而呆滞。宋代院画虽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灿烂的花鸟世界,但是“谨毛失貌”的过分依赖于客观的传达使我们看不到画家主体的自由。这个时期是漫长的,它跨越元代,直到明代末期方得以改观。这里面自然包含有元代对于宣纸的开发利用。当人物与山水的拓展陷入困境之时,花鸟画在此际真正显示出了它的优势。生宣上笔墨大面积宣泄和对花鸟简洁造型观的确立,使得在这一古老的类种上一时名家迭出。也可以说历史的缘合造就出徐渭、八大山人、扬州八怪乃至于现代的虚谷、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等等大家。
花鸟画正是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类种,由于历史机缘的一再误会,方使它沦为晚熟的类种,但也同时说明了它在现代发展上的美妙前景,这一点是值得深思的。机缘中包括各种需要,它便是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人物画由于政治的需要,而得以首先成熟,而山水则更多地由于社会思潮的需要而使艺术家走向林泉,花鸟画则意味着艺术家认同于自我个性的趋向标志。
总的来讲,就艺术类种的发展,除了它的自律性发展之外,无一例外地要受到来自文化观念侵入的干扰乃至于左右其发展方向,从而使评判标准发生大的游移。正如“逸品”这个概念的出现(起初特指山水)开始在唐代是作为正品之外的一种现象提出,但到了宋代黄休复那里则一跃成为逸品之上,而元代绘画恰又正是对于逸品的绘画注脚。它由此而使元画对于宋画反叛的同时具备了新的美学意义。宋代由于苏轼文人画理论的出现,则使宋代院体画之外的一些笔墨游戏而具备对峙的资格,而明代董其昌的一个南北宗论,不仅重新排组了中国绘画史的格局,它甚至使当时画坛并非一流的王维一跃成为南宗鼻祖……
正是由于这些不同文化观念的介入,使得中国绘画史出现了许多兴衰的新闻说,我们如果用现代文化观念去重新审视,甚至可以看出原始彩陶的幽然神秘;商周艺术的狞厉理念;汉代画像石的雍容广博,民间画工特有的造型观;唐代花鸟天真的生命底蕴;赵孟頫“古意”观的历史文化积淀意义,见出“四王”山水的技法美学内涵,明清人物画的文化符号意义……从而使一部艺术史在文化观念的不断入侵下,而成为不断翻案的历史。
也许正是由于中国绘画史上这种判断上的“测不准”,一方面具有灾变性的混乱,另一方面也由此具备了勃发的生命力,从而使中国画这一固体的传统而得以不断流动,使得中国画史不断发出迷人的微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