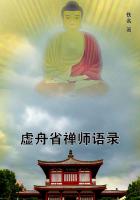可惜的是“下部”出版的时候,我正客居在美国旧金山伯克利大学村,还来不及寄书去求教,却听说柯灵与黄裳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上开笔战,我感到意外,也觉得心如刀割。随即想到不久前在柯灵家中,柯老宴请巴金父女和刚从海外调回来的驻西德大使王殊,作陪的有辛笛、师陀和我。在饭桌上,柯灵与辛笛谈笑甚欢,便在美写信给辛笛,问详情,并要他尽可能开导双方相互宽谅和解;却没有得到回复。一年后我回沪,忙于杂务,还来不及顾及各方面事情,在相隔一段时期以后,在一次巴金画册(照相集)出版、书店开座谈会场合上见到辛笛先生,他跑过来与我招呼,才谈了几句话,又被书店里的事情打扰了,想不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直接接触了。在我再次看到他的时候,已是今年初春在龙华殡仪馆开的那次追悼仪式上,我看到他安静地躺着,虽然闭上了眼睛,但脸上分明仍露着诗人对人世、对朋友的真挚热烈的感情。
现在,辛笛离世已近一年,但作为诗人,他的为人,和他的作品一样,是不会使人忘记的。
写于2004年11月12日
《浙江日报》2004年12月10日
长者风度
徐俊西
我和辛笛先生的交往,是从参加上海作协的工作开始的。那时上海作协的主席团多达十四五人,开会时很少能到齐,但辛笛总是会来参加的,而且总会发言———不过如果遇到有争论的时候,他轻易不表态。
此后,在文艺界和其他的一些活动中,便经常能遇到他。除了一般的问候外,有时还会谈一些作家和文学创作的情况,他总是给人一种亲切和蔼坦诚的感觉。他对作协的工作一直都很关心,后来虽然因为年龄关系不再参加作协主席团了,但每次遇到,还是很关心作协的情况和我的工作。如有一次,我在上海图书馆的贵宾室见到他,他特地把我叫到门外问道:“听说作协在修建中把草坪弄掉了,是吗?这不好吧?我听到有人有意见呢。”我向他解释说不会的,这是因为场地小,施工周转不开,只得暂时占用一下草坪,等土建结束后就要恢复的,而且会比过去更好。他这才放心。
有一次,我在王元化先生处,他说:“你知道辛笛前列腺开刀了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如果我早知道就劝他不要开刀了,现在的医药条件已经能控制了。”我听了也很难过,心想,辛笛先生虽然已年近八旬,但他在我国诗歌艺术上的重要影响和深厚造诣,是还可以为我们做很多事情的,这样一来,恐怕就很难了。
但是在这以后的一段很长时间里,我们仍然能够在很多场合见到他的身影,我也仍然不时能够收到他寄给我的新出版的著作———我虽然是他的晚辈,但他凡有新作,总是会寄给我的,并在扉页上签上名,盖上章,再用一张剪得方方正正的报纸盖在章上。这样就使我这种很少读诗的人,也不得不认真仔细地读他的诗了。
我和辛笛除了工作中和活动中的交往外,十多年来,还有一年一度的春节,也自然地成为我们固定的来往了———每当我走上他家那个老式的、熟悉的楼梯以后,比起那些单纯的、礼节性的访问来,便总会多出一些亲切感和期盼感。每次都是我一按门铃,辛笛先生必然到门口来接我,然后就面对面地坐到客厅中的那张又长又阔的红木桌边,一面喝茶,一面交谈———圣思同志在家时,有时也会过来插上几句,至于都谈了些什么,现在当然已记不起了。但辛笛先生的那种慈祥亲切、真诚宽厚的长者风度,至今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2004年9月
“琐事”忆辛笛
徐文堪
辛笛姐夫去世已有一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如在眼前。我与他见面的次数虽然不少,但深谈的机会实在不多。不过,他生前直至身后发表的文字我却读过不少,阅读时心中的感受和晤谈时得到的印象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所谓“文如其人”吧。恰好圣思要我写一点对辛笛姐夫的回忆,于是把浮现在脑际的有关其文的“琐事”记下来,聊以表达我对他深深的怀念。
我最早看辛笛的著作是他的散文集《夜读书记》。这本书篇幅不大,但非常耐读,收入书中的好几篇文章都值得细细咀嚼。我初读时还不到二十岁,知识自然肤浅,但“小引”中所说的几句话使我难忘,而且引起强烈的共鸣:“世乱民贫,革命斫头,书生仿佛百无一用,但若真能守缺抱残,耐得住人间寂寞的情怀,仍自须有一种坚朗的信念,即是对于宇宙间新理想新事物和不变的永恒总常存一种饥渴的向往在。人类的进步,完全倚仗一盏真理的灯光指引;我们耽爱读书的人也正在同一的灯光下诵读我们的书。”那时我刚开始注意西方的汉学研究和东方学研究史,书中谈有关中国的西文论著的文章《中国已非华夏》对我颇有启发。约二十年后,我参加《汉语大词典》编纂工作,又想起了他写的《英美俚语字典谈》。此文附注中提到:中国人编著的英文习语词典,当以清末曾在美国任留学生监督的邝其照(KwongKi-chiu)的《英文习语例解词典》(ADictionaryofEnglishPhraseswithIllustrativeSentences,1881)为最早;而邝氏在此之前于1868年已编有一部《英汉词典》(AnEnglishandChineseLexicon),1875年刊行修正版。这实在是中国辞书史和中西语言文化互动史上的重要资料,可惜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国内外都还没有学者对此进行专门研究。写到这里,不禁想起致力于十九世纪中日欧语言接触方面探索的老朋友、意大利罗马大学的马西尼(FedericoMasini)教授,希望他把这两部宝贵工具书里的词汇考察和研究一番,必定会有新的收获。
辛笛在文中还提到在二战中逝世的丹麦著名语言学家艾思卜生(OttoJespersen,1860.7.16-1943.4.30,今译叶斯柏森),可见他除主攻文学外,对语言学也有兴趣。记得“文革”结束后,大约在1979年,有一次我在他家谈到当代汉语语言学的泰斗赵元任(1892-1982)先生。他欣然拿出一封赵先生的亲笔信给我看,这是我第一次得见赵先生的手迹,真是喜出望外。赵先生曾经用纯粹的口语翻译过英国作家刘·卡洛尔(LewisCarroll,1832-1898)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早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即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经传诵一时。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打算重印这个译本,通过辛笛征求赵先生的意见,赵先生复信表示同意。此信我当场抄录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信中语句十分幽默生动,可惜时过境迁,现在竟找不到了。赵先生的译文跟今天的语言表达习惯和用词、标点方法等方面已经有了较大的距离,所以为一般读者着想,需要在文字上作一些修改,这就使这本书没能及时出版,直到1990年,在文绮大姐和辛笛姐夫热情帮助下,翻译家方平先生对译文作了审慎的局部改动,才由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与广大读者见面。这件事在圣思的佳构———《智慧是用水写成的———辛笛传》中也有记述,我只是略作补充而已。赵先生的原信我想还完好地保存着,现在商务印书馆正在陆续出版数量达二十大卷并附若干张光盘的《赵元任全集》,这封在学术史和儿童文学史上都有相当意义的信是应该收入《全集》的书信卷的。
梅祖麟先生在回忆其治学历程的文章中曾说起他把第一篇发表的论文寄给已故音韵学家董同先生,董先生回信夸奖,说是“学人的文章,不是文人的文章”。其实,按照中国的传统,学人和文人也是可以打通的,并没有截然的界限。辛笛的文章往往并不长,但读后回味,感到其中既有文人的激情和风采,又有学人的绵密和智慧,这与他的深厚学养是分不开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与他同一辈的留学国外的学人,如他的挚友钱锺书先生、盛澄华先生,还有季羡林先生等,都是如此。他的终生伴侣文绮大姐也很爱好文艺,但她负笈东瀛时跟随的老师是日本史学大家羽田亨(1882-1955)教授,还认真学习过满文。羽田先生是日本西域史研究的开创者和大权威,至今在日本学术界拥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但文绮大姐很少谈论这段往事,更无丝毫炫耀之意,我也没有向她问起羽田教授当时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情况。现在回想,未免遗憾。不过这些是题外话,就此打住吧。
2005年1月
忆拉辛笛老“入伙”
徐芳
很多人走了,很多熟人、师长、朋友,好人、聪明人……想不到我最近参加了那么多次的追悼会,一下子还真不习惯。
去年11月,我们大家刚刚给中国现代文学的耆宿施蛰存先生暖百岁之寿(我在一篇文章里称之为“白寿”,一百缺一是也),当噩耗传来,仍觉突然。当时我可能正在西湖的细雨中以花伞当景,拍照。
杭州是施先生的原籍,西湖的雨雾原也有情有义。我要谢谢那天的风和雨,我虽没赶得上见先生最后一面———先生的大弟子陈文华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因为我的手机没电而没有联系上。虽是遗憾,可亦是天道之常理,风也送了,雨也送了(据说那天上海也下雨了),让我凝然直视又终生难忘的风雨。
也是去年的什么时候,我们去看辛笛先生和师母,一对菩萨一样的老人。桌上一张报纸上谁的名字又被他们描上了黑圈,我瞄了一眼,没多看。
辛笛老,在我读大学时就已被称“老”了。但我们一帮诗社的同学,并没有把他这个“老”当回事,聊天时翘着脚,啤酒抢着喝。也许在一次酒后,一个平时也挺斯文的男生,不知怎么竟公然宣布:“以后你们大家都不要叫辛笛老师,或者辛笛老了!”“那该怎么叫?”大家欢快地叫嚷着,那些年我们能不叫老师的,就不叫老师。当然是分人前人后的。
可那会儿,辛笛先生正笑咪咪地坐在我们中间,那样子比我们还乐。那个男生慷慨激昂地一挥手:“就叫他老辛笛!”此称谓立刻得到一致通过。我理解,这个“老”,一旦放在了名字的前面(不是姓),就意味着一种青春独具的状态,意味着他入伙了……我们彼此不是就互相老什么老什么的叫着,叫得响亮,叫得透亮……老辛笛立刻拱拱手,表示他接受了。
1982年,华东师大夏雨诗社召开成立大会,这么大的事,老辛笛能不来吗?来,而且还拖上从北京来的袁可嘉先生———他的朋友。坐的却是公交车,车票是我买的。不是我客气,也不是我能回去报销,而是他和袁可嘉两个,根本就不可能挤到售票员那里。上车下车时,那种混乱没法说,我既受命于大家,就连拼刺刀的感觉都有了。可辛笛先生的笑容依然谦恭,他必定要让袁先生,理由是袁先生眼睛不好,高度近视,架了副厚厚的眼镜,行动不便。也许他也没觉得自己怎么老,虽然当时他实际上也已70岁,到了古人说的“古来稀”的年龄了。
他和袁先生被挤在车门边上,头与头之间还隔着别人的脑袋,但这些都不妨碍他们谈诗论诗———好一幅现代派的图画。而其时,袁先生确实兴致盎然地描述着现代派诗歌,袁先生给《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写的序言,当时被我们中文系的同学奉为了文学圣经。这个说法是实事求是的,一点都没过分。
袁先生回北京了,可辛笛先生却整日价与我们说起了现代派,白首与我们歌吟与共,可以说正是有了许多这样美丽的时刻这样美丽的景观,做成了我们文学上和精神上的厚厚的铺垫。
当年的老辛笛,在我们眼里,老是那个样子。他仿佛很爱听我们年轻人辩论,我们大战三百回合骑虎难下时,他却绝不伸手拉谁帮谁。乐呵呵的什么似的,仿佛得了最大便宜的是他!
那天听我们说话时,他依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乐趣。可那天的先生与师母,还是有些不同的。他们说了这个朋友那个朋友,却都已故去了。安静的午后客厅里,老先生沙哑着嗓子说:访旧半为鬼喽。一时大家无语,大概这就是伤感袭来?回首、怅惘、苍茫。
今年年初,说“访旧半为鬼”的辛笛,也去了。师母还先行了一步。先生的最后一首诗作,由我编发在《解放日报》的“朝花”上的,新诗,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诗创造》故友林宏的。可发表时加了黑框,特别扎眼。也许没有谁比我更在意这个了:他老人家也太心急了,这么赶着。我并不是为发表的迟滞找理由,令我叹息不已的完全是另外一个角度。
2004年10月
“在同一的灯光下”
徐雁
今年元月八日在上海逝世的著名诗人、翻译家王辛笛先生手掌中的诗国,我是难以自如进入的,尽管读了他《手掌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版)中的那些篇什,情感也不免为其诗行所移:当读到“一个仲夏之夜/在大人的蒲扇下/听过往的流水说话”(《印象》),我仿佛也在那个春夜与诗人一道,自燕京大学披着繁星沿着小河走回清华;读到“科学最高的知识可以劈分原子/但握住那一把刀的却为何还是金钱?”(《文明摇尽了烛光》)相隔不同年代的我,还是忍不住与诗人发出同一声叹息;读到“将生命的苍茫/脱卸与苍茫的烟水”(《航》),我也似乎坠入了诗人“从日到夜/从夜到日”的恒动却也永恒的茫茫然之中……
假如说读辛笛的白话新诗只足以领略其才情,却还不能感知其书卷气的话,那么读他的旧体诗和随笔,却自有一种书香扑面而来。
让我们展卷一读他在1946年秋为《夜读书记》所写的“小引”中说的开篇辞吧———
伤心犹是读书人,清夜无尘绿影春。
风絮当时谁证果,静言孤独永怀新。
这是我闭门索居时作的一首旧诗,对于读书人颇致感慨。世乱民贫,革命斫头,书生仿佛百无一用,但若真能守缺抱残,耐得住人间寂寞的情怀,仍自须有一种坚朗的信念,即是对于宇宙间新理想新事物和不变的永恒总常存一种饥渴的向往在。人类的进步,完全依仗一盏真理的灯光指引;我们耽爱读书的人也正在同一的灯光下诵读我们的书。
作者的文字欧化得可以,长长的句式让人不得不在一再复读之后,才有可能真切领会到寓意的精微。然而,“在同一的灯光下诵读我们的书”,这亦欧化亦诗化了的句子,却以其精辟以其警策,几乎探照了旧世纪读书人的坎坷来路,也映亮了新世纪读书人的进取前程。
———忧患时世,离乱人间,从来百无一用的书生呵,你难道真是不堪任何重寄的吗?不,只要寂寞情怀中永不熄灭维新信念的火苗,那么谁能说你曾经的浏览眼下的诵读、一度的抱残暂时的守缺,不正是某种力量、精神和追求的凝注呢!因为说不定百废待兴之日,正是你这清夜苦读的匹夫,舍我其谁地担当起了存亡绝续的某项文化重任了呢。那么,谁又能说“在同一的灯光下”开卷诵读着的书生们,不是与革命家一般同是真理光辉的沐浴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