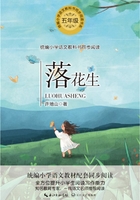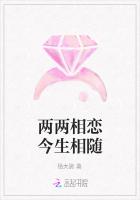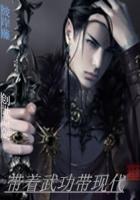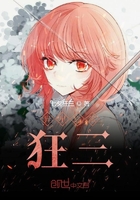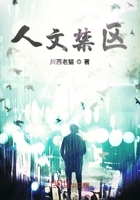近半个世纪以来,告诫作家们要“深入生活”的话语实在讲过不少了。没有生活,自然不可能有创作,这本来是不刊之论。又何必一再谆谆告诫呢?深入那生活之前,人们在什么地方?在生活之外吗?自然,搞通讯报道,写报告文学,反映节制生育,呼喊养猪问题,肯定有一个调查研究,占有材料的过程。不深入,无疑写不成或写不好。写小说或作诗,如曹雪芹着作《红楼梦》,实在没有必要发动他下乡到刘姥姥庄上去同吃同住同劳动。
生活,从来不可能外在地去深入和体验。那是一种无形的别无选择的积累,须臾都不曾离开过每一个作家。那么,读书也应该是一种化于无形的吸取。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不是愚蠢便属迂腐了。
五
正如我吃东西很杂,极不讲究一样,我读书也颇博杂。
我个人订有《新华文摘》、《读书》、《读者文摘》、《围棋》、《柔道和摔跤》等杂志。到资料室翻看刊物,也多是读《百科知识》、《科技和生活》、《武林》、《奥秘》、《新体育》、《连环画报》之类。
或曰:这和创作有什么关系?
可以回答:没有什么关系。
我的生活兴趣相对广泛,摔跤打拳,游泳下棋,跳舞旅游,饮酒猜拳,聊天听戏……好像只是不喜欢开会和排队。我以为人的生活应该多姿多彩,不求生活的最好,唯愿生活的最多。文学创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创作的乐趣和跳舞的乐趣,我觉得皆是乐趣,难分高下。读书嘛,便读书。并不去想这和创作有什么关系。将读书搞得那么“功利主义”,还有什么乐趣而言呢?
不过,文学创作毕竟是充实人生、实现自我的一种重要途径。习作有年,硬说读书时丝毫不练习创作,也不诚实。中国文坛生机勃勃,世界文学大潮澎湃汹涌。通过读书而强化自我,使自己的创作有所进步,这样的主观意图总是存在的。
这几年,随着国门大开,我们的文学从整体上更见出某种哲学上的观照和美学上的把握来了。可算“随大流”,也可称“不落伍”吧。近两年我尽可能读一点弗洛伊德、萨特、尼采之辈的书。借他人之火烛,照自己脚下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读书正是使生活大放异彩的必由之路。书籍,使我们具备了新的眼光,取得了新的立脚点。从新的角度去透视,熟悉的而又似乎已然“写尽”的生活,便会呈现了全新的面貌和内容。由于读书而新知,生活真正成为一座取用不竭的宝藏。
比较三十年代的文学实绩而言,当今中国文学虽大有进步却也未可骄傲。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而就作家的自身建设而论,我们比起鲁迅、巴金一代大师,毕竟少了一条“腿”。他们非但精通国学,而且大多都曾出国就学,取得全新的并且也是全球的文化视角和立脚点。回首中华,定是看得格外分明。也便避免了“小家子气”和“小地方主义”,一出手即进入了全球文学竞争的格局。而我们这一代人难得出国留洋,某些作家的小说偏又讲什么“去国即是叛国”的洋洋洒洒的大道理,不亦悲哉也夫!作为补救的办法,那我们就在批判地继承古典文学遗产的同时,尽量也批判地吸收一点舶来品吧。“古为今用”而“洋为中用”,两条腿走路,我们的步伐才会更加阔大起来。
六
音乐本身原是情感的。在语言停止的地方音乐开始。但高级音乐却又是极富哲理的。
中国文字原是极形象的。形之与义,达到高度统一。但高级的书法艺术偏偏又能取得抽象的美之效果。
读书相对多起来,读故事读人物之外,无形中会对文体和文气有了更高的需求。文体是有形的,文气则是无形的。有的文章,所写的内容也许不过尔尔,但遣词造句布局结构诸般形式却达到极高造诣。使我们不能不认可“形式即艺术”。
而另有文章,内容平平形式亦未见新奇,但字里行间却流动喷涌着某种气韵。使我们不能不折服“文贵有气”。
那么,通过读书我们必然地会提高欣赏水准。接着便会发生“眼高手低”的困惑。而这样困惑之来,值得庆贺。它将迫使我们的创作走向更加完美与老到。
我们会写的更加“讲究”,更美更好而更加接近了艺术。
古虽有言“食肉者鄙”,但食肉者毕竟营养更为良好。从这个意义上说,多读书而读好书,对于创作者的滋补功用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我基本上不读文学杂志。读古典而读“西方”。取法乎上,或可得乎其中。比如《红楼梦》和《聊斋志异》,我是读过几遍的。我认为不曾读之者,等于不曾吃过肉。
七
有句老话说:知识就是力量。
这话其实错了,起码是不全面。应该说,智慧和才能才是力量。
满腹经纶的腐儒我们见得实在多了。他们的智商其实低得惊人。而读遍名着,学富五车的少年我们也见过不少。引用名篇如数家珍,拗口的外国大作家的名字可以当场列出整团整营。论及创作,却连一则短文也作不出来。
那么,这倒反而是受了读书之累了。
西天取经,须得有跋山涉水的脚力;名山盗宝,须得有掮负宝藏的肩膀;鹅肝鱼翅、牛鞭驴肾,固然大有滋补,则又须得有消铁化铜的脾胃。生活经历丰厚已极,却不能反思认识表现它,等于没有生活;读书万卷,汗牛充栋,却不能化作自己的片言只字,等于不曾读书。读书读到满脑袋只剩了古人外国人,读丢了自己,这书也就读得可悲又可怕了。
古人外国人,着述立说者,皆是智商很高的把式。他们把智慧化为白纸黑字来考验我们。那是引导我们浮升的阶梯,也不妨说又是诱惑我们堕落的陷阱。你找不到钥匙,只好被永远锁困。武二郎打不得虎,大虫原是要吃人的。
“的卢”马是一匹千里马,但相马者又说此马“妨主”。那草鞋皇帝刘玄德不愧为一代枭雄,断然道:
人能驾驭马,马怎么能妨主?
这或者应成为我们读书之座右铭。
八
自学习创作始,我不曾做过笔记所谓记录素材之类。我认为生活是一个过程,而过程即我,即实在是无须记录也无法记录的。创作的结果本身即作品才恰恰是记录了我的一部分或一部分自我。而创作的过程则是自身生命的特殊存在方式。生活的积累,读书的功底,借助了创作冲动引发的情绪流一起奔来笔下,创作的亢奋笼罩了整个身心,如魔鬼附体。不曾做过笔记,又有何妨?做过千百部笔记,又有何用?
读书,我也从来不做笔记。
眼下,我的住房条件尚未全然改善。卧室、客厅、书房,三而合一,区区七个平方米。因而,书架独一无二,架上存书寥若晨星。我以为,世上好书之多,实在是买不全也读不完的。买了不读,买它何用?读了不能化解,读它作甚?
所以,在工作之余,跳舞打牌之外,出于天然的兴趣、消遣的需要、充实自身的主观愿望,我尽量多读一点书。以为读通读懂,就弃置一旁。或有心得,它已得之在心,又何必记录。既已得知在心,也就不肯特意存书。没有书架也许是个原因,而主要原因在于:我的书架历来都排列在我的脑瓜子里。或者说,读书而化于无形,无书而有书,是我的读书之追求吧!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
宇宙和我们自身的存在之奥秘,其实是不可言说的。何以言?言以载道。书籍文章,毕竟又是一种载体,是道之所存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还是读书吧——不过,应当同时记着另一句话:
于无字句处读书。
借《北方文学》稿约之机。作《我与书》于上以明志。或多少有与同行切磋交流之功用,则属望外之喜。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匆草于中国作协招待所叙述虚构
场面、情节、人物,向来是小说不可或缺的要素。但这些要素原本都属于戏剧,小说研究历来因循了戏剧研究的理论。直到西方有“叙述学”问世,小说才有了属于自身的专门理论。借助文字来叙述故事,而不是由演员在舞台上演绎传奇,成为小说与戏剧的重要分野。
但一般记叙文、包括报告文学不也是依赖文字叙述的吗?所以,惟有虚构,才是小说的灵魂和生命。
小说,从创作的主体而言是文字叙述,从欣赏的受众而言则是书籍阅读。与戏剧相比,小说的繁荣与大众的阅读能力有关。文盲比例过高,阅读市场过小,不大可能催生出小说的黄金时代。
所谓“小说”,历来不登大雅。中国自古是诗文的国度,有“文以载道”的强大传统。但这里所说用以载道的文章,指经史子集、八股策论、诗词乐府等,从来没有指望小说匡正乾纲、承续道统。
但是,在主流文化强大传统影响之下,中国的古典小说无不强调“载道”。
许多杀人放火描写的《水浒》,历来不免被批评“诲盗”,但其原来倡导的是忠义;露骨描写性交的《金瓶梅》,分明有“诲淫”之嫌,据说也是为了惩戒淫欲。浅薄评论家逢迎上意说《西游记》描写了一只富有造反精神的猴子,那猴子一旦皈依佛法,立即残忍诛杀其他妖精,哪里顾念大家本来都是不服王化的山精水怪。
或者可以说,中国古来的小说家们相当富有责任感。写作的虽然是不登大雅的小说,作者却无不满怀王化道统天下己任。这个特点一直遗传到当代,小说家们个个都要学习鲁迅,要以文学来“救国”,要用小说来唤醒民众。搞得小说不堪重负,搞得作家自己忧国忧民、像要投汨罗江的屈原似的。
《三国》、《水浒》原是脱胎于评话。老百姓历来念叨,“说书唱戏,给人比喻”。平话的产生到繁荣,与戏剧的出现与繁荣,大致同步。
由于中国多数民众没有阅读能力,大家如何满足娱乐需求?大概是城里的市民上茶楼戏馆瞧戏听书,勾栏瓦肆生意兴隆;乡下的村民则依靠赶庙会看戏、借娱神而娱人,偶尔听走村串乡的平话艺人说书、因而才能“听闲书落泪,替古人担忧”。
不再脱胎于评话“说书”,真正供人来阅读的小说,是《金瓶梅》、《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它们应该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的发轫。从小说的内容上看,也不再搞宏大叙事,家长里短开始纳入小说创作的范畴。
上个世纪初,中国开始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其意义怎么估量都不过分。扫除文盲、开启民智,从此成为可能。
唐朝,白居易的新乐府可以听“老妪”评说;宋朝,“有水井处即有柳词”。
那是借助了诗词本身的吟诵歌咏功能,老妪们依靠辨听而不是依靠阅读来接近了诗词。
白话文运动之来,孩子们不再上私塾里读四书五经,而是上国民小学念白话课本,中国的文盲锐减。更强烈的阅读需求,呼唤着更多、更通俗的文学作品。
上个世纪前半页,中国白话小说创作一派蓬勃,作家队伍空前庞大起来。
从大众接受的标准来衡量,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还是趋于深奥晦涩了些。有感于《阿Q正传》如此好文章老百姓无法消受,赵树理一片苦心将小说文字的通俗化发挥到某种极致。赵树理的文字遭贬斥或者得赞誉,都是因为通俗。
事实上,赵树理成为这样一块里程碑:初通文字,不仅能够读小说,而且可以写小说。
不知赵树理是否得过“人民作家”的称号。后来,若干功成名就的老作家、还有个别当红的年轻作家被授予过“人民作家”称号。这个名堂容易引起误会。
好像其他作家属于“敌人作家”。至少也是“反人民作家”和“非人民作家”。
所以,“人民作家”倒不如称为“功勋作家”。
赵树理先生,与其称他“人民作家”,不如称他“农民作家”。
小说作者犹如其他文体的作者,在写作之初无不预设一个“期待视野”。当有人揶揄赵树理的小说写的太白太土,赵树理豪迈地回答:我本来就不是写给你看的!为了初通文字的农民读者能够看懂他的小说,他不惜隐藏起自己更高的写作功力,甘心遭一些半瓶醋的挖苦。
其实,人们哪里能说赵树理的写作功力不高。平易而能近人,实属高大境界。
佛祖曾经发愿,要渡尽众生自己才登彼岸。众生者,包括蝼蚁虫豸。那么,佛祖宣讲佛法能不浅白通俗吗?能格外卖弄自己多么高明吗?与一生倡导白话文的胡适先生一样,赵树理至少具有菩萨那样悲悯的心怀。
伟大的白话文运动,与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启蒙、革命等等运动相伴生。
以鲁迅为首的小说家们,要用文学来救国,唤醒民众、改造国民性。作家,自己发誓要担当大任;小说,从此不堪重负。
何况,到后来小说家都被纳入组织管理、小说创作都要服从宣传的需要。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白话小说几乎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与政治结下了过分紧密的不解之缘。
记得矛盾先生说过这样意思的话:简单配合宣传任务,是小说的堕落。
“堕落”,他用的是这样一个刻毒的词汇。其中多少痛心疾首啊!
而正是矛盾先生自己的作品,大有配合宣传任务之嫌。一切是那样耐人寻味。
赵树理身为解放区成长起来的革命作家的代表之一,作为个案,他的命运值得后人思索。
他看到生活中太多的不平或曰“问题”,他要通过小说来呼吁呐喊。他称自己的作品属于“问题小说”。当用小说反映问题已经来不及的时候,他向中央上了“万言书”。
赵树理曾经被夸奖为“铁笔圣手”,“文化革命”开始则立即被打成所谓山西文艺黑线的“祖师爷”。残酷批斗、被打断肋骨,最终迫害致死。
将一切罪责推到四人帮和红卫兵的头上是方便的;但这是比小说虚构还玄乎的虚构。
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革”结束。
诗歌与小说创作一时异常蓬勃,极其踊跃地呼应参与了思想解放运动。
读者无暇关注什么艺术,大家渴望文学作品来揭示社会问题、呐喊民众心声。号角诗歌、问题小说纷纷制造轰动,接着是专门揭示社会问题的报告文学洛阳纸贵。
轰动效应一个接着一个。作家因为一篇作品最早呼喊了某一个重大问题而一举成名天下闻。
这样的轰动,与作家的艺术功力、与作品的文学内涵无关。
广大读者对文学的“非文学期望”,驱使着作家们仿佛在比赛谁更加“傻大胆”。文学创作的异化状况日益严重,几乎不可救药。
当形势发生变化,比如责任制取代了人民公社,当初歌赞合作化、公社化而红极一时的小说作品立即一文不名。这其实是非常典型的反证。
但小说创作图解政策、追风赶浪的弊病始终极其顽固。
当大家浪漫地欢呼歌唱“文学艺术的春天”已经到来的时候,文学既然一直要干预生活,生活对文学的干涉压制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防止“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叫运动的运动,一个连着一个。
极左思潮哪里会轻易消失;政治干预何尝曾经弱化。
艺术家赵丹临死前痛心疾首地说:管得太死,文艺没有希望。
新时期文学在艰难奋进。文学创作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顽强求索。
有人不负责任地轻松预言:伟大的时代必将产生伟大的作品。
话说得一点没有毛病,时代确实伟大,伟大作品可惜至今不曾出现。
解放前,始终被描述定性成“万恶的旧社会”,那时反倒产生过伟大的作品。
比如《红楼梦》,比如《聊斋》。
这种现象值得深思。
文学创作,作为最个性化的创造性劳动,天才作家、伟大作品的出现,或者并无什么规律。
主管文艺的有关部门,历来最爱对作家们耳提面命:要深入生活。老生常谈,让人耳朵生茧子。
没有生活,当然不可能写出什么文学作品。这本来就是常识。作家们冷暖自知,何须一再唠叨。
原来,那些人希望作家们“深入”到与当前政策有关的生活中去。当前号召养猪、提倡节育、正在搞责任制、修筑了一条高速公路什么的,你们为什么不立即去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