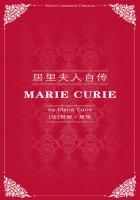1.“材料”出笼
1955年5月13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舒芜”的文章———《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这篇文章所提供的“材料”以及对“材料”所加的定性,后来被证明都是不实之词,而这篇文章本身却真正成了陷害他人的“材料”。然而,在它发表的当时,它却非同寻常。单就文章的标题就能显示文章所涉及事件的严重性,而文中所述的耸人听闻的“事实”也有很大的蛊惑性。还不仅如此,它的不同寻常更在于《人民日报》特别为它加了“编者按”,而且措词严厉。“编者按”说:
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反革命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
又说:
胡风反革命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意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政府提供更多的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政府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革命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版)
在当时,无论是政界还是文艺界,只有在高层的少数几个人知道,这篇“编者按”是出自毛泽东亲笔。
这篇文章当然不是胡风案的开端。在此前的几年里,胡风几乎总是以被批判的对象出现的。尤其这年年初以来,对于胡风的批判日益加剧,但批判声虽强,却还多是就文艺思想问题。“材料”将胡风的问题提高到如此程度,这是许多人,无论是胡风和他的朋友,还是他们的批评对手,都是没有想到的,也是十分意外的。
胡风,诗人和文学评论家。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报《文艺报》编委。早在二三十年代,他就已经名扬文坛。他曾经是左联的负责人之一,也是和鲁迅关系密切的朋友。三四十年代,他先后创办《七月》《希望》文学杂志,培养扶植了一批青年诗人、作家,舒芜曾经也是其中之一。然而,世事难料。五十年代起,胡风与舒芜事实上已渐渐是道不同者。对舒芜的为人胡风已经极不信任。他曾经对前来造访的舒芜当面表示了不欢迎。即使这样,对于舒芜抛出所谓“材料”,胡风完全缺乏预见。又有谁能预见到呢?
舒芜,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古籍编辑室的编辑。从年龄上讲,他比胡风年轻近二十岁,就资历和成就而言,与胡风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可以说,舒芜是由胡风扶持走上文坛的。早在1943年,刚刚二十出头的舒芜就通过路翎认识了胡风。此后,他受胡风提携发表了不少文字。抗战结束后,舒芜带着新婚妻子到上海度蜜月,就住在胡风的家中。曾受益于胡风的舒芜抛出欲置胡风于死地的“材料”,实在不是有品行的文人所能为的。这篇“材料”的发表,超过了他以往所有发表的文字的影响,使他一时间成为名声飞扬的人物。
所谓“材料”大致由三部分内容组成:
从胡风给他的书信中摘取一些段落或句子并分类编排;
对这些段落或句子分别加上的他的注释;
舒芜本人的文字。
舒芜说:“在这里,我要提供一些有关的材料,以帮助大家更好地认识胡风思想和他的反共活动的实质。”他又说,他本人在解放以前“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直到解放后,在共产党的教育下,在参加实际斗争当中,我才初步认识到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
舒芜的这些话,似乎表明他终于大彻大悟,他不仅要“弃暗投明”,而且还要以“反戈一击”的行动来证明他“弃暗投明”的坚定决心。
舒芜的行为对于后来大规模抄家搜寻“胡风分子”信件以做“罪证”无疑起到了主导性作用。
几乎在“第一批材料”发表的同时,全国各地那些被认定为“胡风分子”的人们纷纷被抄家、被收审,由责令交出或由抄家而得的“胡风分子们”的书信被收集到有关人员手中。负责摘录和注释这些信件的是专门组成的“五人小组”,其成员是: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郭小川、袁水拍。
他们投入了工作。5月24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其中收录了胡风致友人的书信共68封。
“五人小组”以高效率继续工作,“第三批材料”很快整理完成。6月10日,定性由“反党”改为“反革命”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共收录书信67封,多为“胡风分子”们之间的通信。
6月,汇集了“三批材料”和所有按语的单行本《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出版,到7月,已经印刷7次,印数达100万册以上。同时,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也风卷全国。
当胡风和各地的“胡风分子”们在此后纷纷下狱、流放并在迫害中家破人亡之时,舒芜不仅名噪一时,还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97年,舒芜在他的《〈回归五四〉后序》(《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期)一文中说,他最初的文章题为《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后被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非他“始料所及”。舒芜的这段话,是很容易博得不明真相者的同情的。他含糊其词,有意模糊《关于胡风的宗派问题》被“一改再改三改”的具体事实。
《关于胡风的宗派问题》——《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标题的变动由舒芜本人所改。标题中的“胡风小集团”上升到“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确非舒芜所改。但舒芜从胡风给他的书信中摘录、再加注、再加他的“解读”和“批判”所构成的“材料”,却完完全全是他的原作。舒芜在文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他提供的是胡风的“反党”材料,那么,标题改为“反党集团”并不与他的文章有矛盾。其实,此前,“反党”一说早在舒芜的文章中使用。
1954年4月,舒芜在《中国青年》上发表《反马克思主义的胡风文艺思想》一文中就已使用“胡风所经营的反党的文艺小集团”的说法。
同月,舒芜在香港《大公报》上就以《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为题的文章发表,更直接地认定胡风是“反党反人民”。
“反党集团”定论的出现应当不会使他感到吃惊的。一句“一改再改三改”不过是就虚避实、模糊事实本质的托词。
只是,舒芜也许真是“没想到”,他的这篇文章在还没公开发表以前就先到了毛泽东手中,而且毛泽东为此亲笔加了“按语”。这个过程非但不是舒芜能想到的,更不是他能做到的。
2.材料是如何升级的
1955年4月,舒芜的“材料”到了林默涵手中。对于这个过程,舒芜与林默涵说法不一。舒芜之说,是林默涵看到了他交给《人民日报》准备发表的文章,托人来向他索要原信,林默涵则说,是舒芜主动将信交到中宣部的。谁的说法更接近事实,两个当事人彼此应当都是明白的。
1989年,林默涵在《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中叙述当时的情形时说,拿到胡风给舒芜的信的原件,他当时并不觉得那些信有什么可看的。过了一阵,才去翻了翻。结果被胡风信中的内容引起了愤怒,因为胡风的信中“攻击”了“党和非党的作家”。他将信转给周扬,并商定公开发表。于是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报《文艺报》很快将舒芜的“材料”排出了清样,康濯(当时任《文艺报》常务编委)加了按语。一切就绪,只等开印。但周扬提出,“材料”要交毛泽东看看。
将“材料”交给毛泽东是周扬的决定。周扬为什么要这样做?以中国的政体,将一篇文章呈给国家最高领导人看,这当然不是一件小事,周扬在已经排出文章清样后想到要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理由。只是他本人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都没有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解释过。而见毛泽东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并不是所有的人想见就可以见的。周扬、康濯、林默涵三个人中能见到毛泽东的只有周扬一个人。而事实上,材料并不是周扬当面送呈毛泽东的,而是附着周扬的信通过其他方式递送到毛泽东手中,此后周扬才见到了毛泽东。当时周扬和毛泽东之间有什么样的对话,毛泽东的态度和周扬本人表示了怎样的态度,周扬从没有说过。他从毛泽东那里回来时,向康濯、林默涵转告了结论,即胡风已经成了反革命。
林默涵在回忆文中对当时事件性质的升级陈述过他的看法,他认为意想不到的事情突变就在于舒芜的“材料”到了毛泽东那里时所起到的作用。他说:
在舒芜交出胡风的信以前,毛主席也并未将胡风打成反革命,只是将胡风的思想定为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批判、斗争只限于思想的范畴。但是,当毛主席看到了胡风背地里写的那些信件(其中并没有攻击毛主席本人的语言)中,对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那种敌视、贬损、憎恶的语言和态度,就引起了他的怀疑和愤慨。我认为这是毛主席将胡风小集团定为“反革命集团”的重要原因。
(《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林默涵所“认为”的是否符合毛泽东的本意,不敢妄议。但有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毛泽东看到的并不是胡风的原信,而是由舒芜摘录出来的段句并分类注释后的“材料”。这犹如一个法官确信了一份诬陷他人的诉控并做出了裁决。
毛泽东否定了康濯的“按语”,亲自写了按语,连同“材料”一起交还给了周扬。“材料”的“身价”迅速提升,它由毛泽东决定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文艺报》只能转载。
5月13日第一批材料发表,胡风即在5月16日被拘捕,其他“胡风分子”也相继被拘捕。此后,从“胡风分子”处搜寻而获的信件经林默涵等人整理分别成为第二批材料和第三批材料。据林默涵说,第二批材料的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按语都是毛泽东修改的,有的是毛泽东亲自加的。至于第三批材料,林默涵说:
第三批材料的编者按语全是毛主席写的。但在张中晓给胡风的一封攻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信后却没有按语,这是不合适的。我和周扬认为,这可能是主席不愿意提到涉及他本人的事,便由我们两人起草了一段按语加上。
(《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先前的“意外”也许是因为对毛泽东的意图未能正确判断,而面对张中晓的对毛泽东的著作有不敬之词的一封信,林默涵、周扬居然不用毛泽东任何提示和任何暗示,就以高超的领悟力做出了在他们看来是合乎毛泽东意图的事。这不能不说是在由前一次“意外”而带来的思想的飞跃提高。
这一段按语当然地成为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的一部分。
……因为党和毛泽东同志号召文艺工作者要歌颂工农兵,要暴露工农兵的敌人,而胡风集团恰是工农兵的死敌,他们觉得暴露工农兵的敌人就会使他们混不下去,就会“屠杀”他们这伙反革命的所谓“生灵”,就会“压杀了”他们这伙反革命的所谓“新东西”。但是他们不敢公开地反对这个讲话,而且胡风还教唆他的党羽在表面上要“顺着它”,有时并引用其中的一些字句。这些,都是胡风分子伪装自己的假面具。而在这封密信里,就完全暴露了胡风分子仇恨这个讲话和反党的真面目。张中晓说:“这书(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许在延安时有用,但,现在,我觉得是不行了。”在文艺界里面不是还有一些人说过同样的话么?……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112页)
这段文字足以显示撰写者的高超悟性,只可惜来得晚了一点。这只因为“意外”,倘若能“意料”的话,其他按语或许就不必由领导人亲自费笔墨了。
3.“密信”中究竟说了些什么?
毛泽东为什么要将胡风打成反革命,因为那些信?因为三十万言书?政界没有人为此作过解释,文学界中周扬是当年与毛泽东直接联系的人,是他向林默涵等人传达了毛泽东的“胡风都成了反革命了”这一主要结论。但他却没有作过其他解释。
峰层领导者是如何作出结论的,无从考证。
可以找出种种客观的原因,可以分析出各种政治背景的因素,认为胡风案的产生有着其不可避免的必然性,然而,再多的理由也不能否认具体的人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一个主观的意志可以主宰一个社会,这本身是可怕的,无数的意志只在依附一个主观的意志则更可怕。问题还不仅仅如此。
胡风的私信以及后来所获的“胡风分子”们的往来信件,能成为一份材料,与下了苦心分类注释的人们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以书信为材料而定罪,是以胡风案为先例的。书信是否可以成为定罪的依据,这在胡风案的研究中一直颇有争议。公民有通信自由,这是常识,也是受到宪法保护的。书信在有些情况下是可能成为某种举证的依据的,但这必定要有严格的法律程序。这在胡风案中是完全缺乏的。还不仅如此,书信还被任意肢解、断章取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