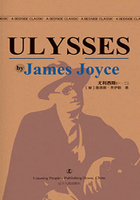选准了方向,就得无怨无悔。离开杨洪桥的时候,天空中的田野正荒凉着。公路两侧的树林枯黄着,齐齐地往后退缩。我明白,许多人生的经历如同河边的风景,不是矗立就是后退。许多次,我试图寻找一种飞翔的姿态,将过去的一切寻找了回来。然而,眼睑随着岁月一天天苍老,忽如灌铅的腿脚已将大部分的梦想全部琐碎成一种无奈。
时光是击碎梦想的无形锏,让你不知不觉中失去一些记忆。每一个人曾经的梦想都是飞翔,飞翔是翅膀浮掠的天空。可真正飞翔的时光在哪里?一大群鸟不经意间淡出了视野。许多个习以为常的鸟突然从眼前消失。惊悚,恐慌,麻木,一个个鸟把我们的生活带走掏空,甚至把来时的路都给封尘。那片时常有鸟的天空只能出现在梦中。常常在梦中看见自己如飞的情景,也能在如飞的过程中感觉插上翅膀的影子。然而梦醒后的旧模样,依然散溢着时光。
飞,一直是个梦。
沿着河,过了桥,渐渐回到熟悉的城市腹地。一切喧闹的声音将外面的纯净全部掩盖。城市是一块土地,原本就是鸟的领地。而现在,从土地长出来的城市,天空很少有鸟的出现。有时连鸟的踪迹也难以看见。没有鸟的天空缺了些灵感,没了鸟的城市少了些灵魂。偶尔,望着城市上空,大地木然。当季节以一缕斜阳方式将天幕重重遮盖时,西山一侧青黛如岚的天边,一群飞鸟正振着翅膀从天幕重围中俯冲了过来,只用一会儿的功夫便将大地遮蔽。
一瞬间,所有的天空都变了。
只有鸟,一直在飞翔中寻找俯冲的机会。它的俯冲像天上的陨石,随便在任何一个人的眼睛里都能砸出一个记忆的坑。那些记忆的坑是鸟的翅膀留下的痕迹,那些坑是飞翔的天空留下的一串串经历。
我望着杨洪桥,一群曾经的鸟振着翅膀,在风雨中淋漓。它们的飞翔里,一场大雨正将大地湿润。然后,村庄的气息将飞翔的姿态凝固。
找找自己
在动物界,与人为善而又甘于掩饰自己的恐怕就是驴了。你看它,任劳任怨,不辞辛苦,让拉磨就拉磨,让驾辕就驾辕,让走哪里就走哪里,即使让人教训一番,还乐此不疲地来回奔波。
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两头驴,一头叫四咪子,一头叫五咪子。四咪子能干,又很能忍受,只要家里有事,不管大小,都使它。而五咪子呢,性格倔,又爱尥蹄子,一使,就出乱子。所以,在家里,四咪子干的活远比五咪子多。后来活多了,不让五咪子干不行。特别是开春犁地的时间,单驴拉不成犁,只有两头驴一起拉,才能配套。可五咪子不识抬举,任凭父亲怎么使,都不上套。到田里,五咪子不是站着不走,就是随意乱跑,弄得田里尘土飞扬不说,还弄得人一身紧张。在田里帮忙的大爹看不过眼,就说父亲,连个驴都治不住,咋能种好田呢。要不行,你把驴借我使几天,我看它能成个啥呢?父亲说行,就让大爹把五咪子带走了。
过了几天,五咪子回来了。只见它耷拉着头,没个精神,套笼头,犁田地,让干啥活就干啥活,就连我这个才十多岁的娃娃也敢一个人拉着它下地干活了。对五咪子的变化,我起先有些想不通,但后来,我渐渐感到做驴的不容易。同样是生命,只因为驴是畜牲,命运就不相同。不听使唤,就打你、骂你、饿你,再不行,上个嚼子勒你,看你听不听使唤。后来我从大爹那里知道了一些情况后,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同情。你看五咪子,都苦日他了,只要有活,还要继续干下去,没有回旋的余地。特别是一到农忙,连天连夜的活,没有驴的参与万万是干不完的。对于驴来说,哪怕吃不上料、喝不上水也得干下去。在农忙的关键时刻,驴才真正显示出其存在的意义。它帮你使劲地往完干活,可是,一旦干完活,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也许是因为家里穷的原因,我从驴的忍耐中也看到了驴的优点。它能让你在最困难的时候感受到生的意义,在最失意的时候自己珍惜自己。在家里,我几乎天天与驴打交道,尤其在农忙时节,和驴在一起的时间更多。我想驴有个脾气还要让人给治了,它不改脾气,就有人打它、饿它,还想着办法治它。对于驴的生存而言,驴的世界就是一个忍耐的过程。知道这回事后,我对驴总是有一种同情。尽管驴是可以教训的,但对于一个生命而言,它的存在就是一种警示:无论你在何种情况下,驴的忍耐足以让你在最渺小的时候看清自己的样子。和驴在一起,捋着驴毛,再有多大的委屈都可以化为一种抚摸。从倔得让人无所适从到任人驱使,五咪子的变化一下子让我就觉得驴是最善于找回自己的动物。
五咪子的变化让我觉得拥有自己的一份个性和自在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有自己,说明自己还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天空;有自己,证明自己还能把握自己,还有一份自觉的清醒。可没自己呢?不是任人驱使,就是丧失尊严,所谓的自己也不成其为自己,只能成为一种生命的附属表现。在这个谁都认为自己就是自己的时代,要想拥有真正意义上的自己,那得付出多大的牺牲?可现实中,属于自己的东西太少了。有些时候,长久地沉浸到一种习以为常的没有什么激情的生存状态中,有多少空间和时间属于自己呢?
找找自己,不妨借个物体照照自己。
妹夫
妹夫是我的一个哑巴堂妹的丈夫,五年前从陕北招赘上门的。虽身材短小,但力气大得惊人,一米五几的身子能抱起近百公斤的粮食。农忙时节,母亲就打电话让我们回去帮收粮食。可每次回去,我们的作用不大,毕竟老待在城里不干活,力气自然就小多了。拉粮食、打场之类的力气活,干一阵就有些吃不住。要不是妹夫,说啥也干不完。我们回去也只是精神上的鼓励,站着装装样子也算是尽力气了。也正因这样,妹夫帮了很大的忙。每次回老家,都要与妹夫喝几盅。后来母亲从乡下搬到城里后,家里的老房子就借给了妹夫,一方面让妹夫有个安身之地,一方面也代为看门。母亲进城后,我们也不多回去了,与妹夫见面的时间也少多了。好几次,妹夫不知怎的给我打了电话,约我回去和他喝几盅。妹夫说,小哥不回来,心里少了个啥。听着这些话,我心里热热的。
妹夫是我大爹的二女婿。在咱老家的风俗里,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的乡里人招女婿很讲究,一要听话,二要干活,三要有力气,否则,二两棉花没弹(谈)头,招你干啥。招妹夫的时候,我的那个从小耳朵就发聋的大爹考虑得很简单,就是让自己的哑巴女儿不要受什么罪。要知道,在现实中让一个残疾人有个圆满家庭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些时候,庄子上到了婚嫁年龄的女子一个个地嫁了出去。一到冬季,嫁女儿、娶媳妇,杀猪宰羊好不热闹。吃一次席,聋大爹就是一阵心酸,自己的丫头啥时候能有个主儿呢?后来跟我父母商量后,还是决定招一门女婿来。于是在堂妹到了婚嫁年龄的时候,大爹就张罗着为堂妹招女婿。
妹夫家住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沟,哥们弟兄六个。齐刷刷六个儿子可让妹夫的爹愁死了。家里虽说种着满山遍野百十亩旱地,可靠天吃饭的日子让妹夫家的生活并不好过。老大快三十的时候,家里还没有给娶上媳妇。那些年,家里穷,想给儿子们娶媳妇,就算铡了指头也没办法。眼瞅着老爹发愁,家里生活又不咋样,妹夫给老实巴交的爹说,我想出去。妹夫的爹看了看妹夫说你走吧,几行泪就落了下来。
带着家人临走时给的二十多块钱路费,妹夫啥也没多说坐上了走宁夏的车,一路摇摇晃晃地过盐池,到灵武。到灵武下站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身上只剩下两块多钱。好在是夏天,妹夫吃了一碗拉面就在街上找了个地方混了一夜。第二天,妹夫就找了个搬砖的活。到了秋天,工地上的活也少了,妹夫又在我舅舅家找了个活。
舅舅家与大爹家离得不远,只是一村之隔。到了来年开春,大爹四处打揽招女婿的消息传到了舅舅的耳朵里。舅舅领着妹夫来了。大爹说:人矬得很么。舅舅说,人家不嫌弃就是好事了。结果把堂妹找了来,让两个人对象。堂妹虽说听不见又说不出,心可灵着呢。两个人一见面,堂妹高出了妹夫一点点。堂妹有些不满意。后来家里人又比划着劝,堂妹才勉强同意。当年秋上,大爹借了两间房子给两个人办了婚事。
守着几亩地过日子,妹夫很满足。从小山沟里走出来,能有个家,能吃上可口的米饭,对于妹夫来讲是再幸福不过的事情了。每次回老家,妹夫都把我喊到他家里,让堂妹做上一顿好饭,然后弄上一瓶子酒,坐在那个垫子都快陷了下去的沙发上划拳喝酒。一喝到兴头上,妹夫的话就多了。说说家里的,谈谈庄子上的,有时,还想想山沟里的老家生活。有一次,我对妹夫说,等你的生活好了,我和你走走你的老家怎么样?妹夫不敢相信地说,哥哥你哄我吧,像你这样的干部能走到我的老家?我说咋了,我又不是啥人物。妹夫说,整个庄子上的人都把你看成是有头有脸的人,到谁家谁家就增光呢。听着这话,我热乎乎的。妹夫说,哥哥要是能到我老家转转,我非让庄子上的人陪着哥哥喝六天六夜。我笑着说,那我就等妹夫的日子好起来了,我陪你回趟老家,也看看两位老人。
春节前,我和我的哥哥骑着摩托车回了趟老家。到庄子上的时候,我发现在我家的门口新建了一幢新砖瓦房。我问哥哥,这是谁的房子?哥哥说,这是小马子的。小马子就是妹夫。我吃了一惊:才两年多的时间,妹夫就盖上了新房子!看完已经进入花甲之年耳朵更聋的不行的大爹大妈后,妹夫又请着我们去了他家喝酒。喝酒的时候,我羡慕地对妹夫说,行啊,房子盖起来了,生活更有奔头了。妹夫对我说,哥哥先别说这个,今年我想和你一起回趟老家,不知道哥哥有没有时间?我说,回老家?妹夫说,哥哥两年前说妹夫生活好了,就陪我回趟老家。这两年,我包人家的地种,自己出外打工,就是为了把生活过好。现在房子也盖起来了,我想哥哥陪我回老家我脸上也有光。
我愕然了,一句随意说出来的话,有时候竟然有如此的力量。
走不了多远
一
没走多远,很多人就以为他走得很远了。说话间,一些人离开村庄几十年也没回来,好像被风吹走的一粒沙子跑得远远的。留下的人站在村口往外看,也没把谁的脚步拉了回来。
人们走得并不远。只不过出去时间长了,让人心里空空的。桥头那棵等人的树天天在长,就是不见出去的人早早回来。树一直长到碗口粗的时候,好些人也没回来。等月亮上来了,庄子上有几家后窗露出了光。一直到深夜,也没有谁叫门。几声叹息后,屋里的灯熄了。后半夜,雨来了,有几堵院墙被雨冲得掉下几块土坯,然后顺着水道流下坡。早早醒了仍然躺在炕上的大伯一边抽着烟,一边让皱纹早早地爬上额头。他心里盘算着,如果过年的时候,儿子回来了要杀哪只猪?要宰哪只羊?
雨下着,心思也上来了。
哪一个人走出去,后面都有人在想。
想谁呢?
想家里的顶梁柱?想心里的一块石头?
想着想着,一缕缕银发上了头。
从庄子走出去的人经常会回头。他们没走多远,顶多也就是在村子外面溜达着。走得再远,也丢不下过去。有些人走着走着,找不着方向了,只好沿着来时的路往回折。快走到村口的时候,又停了下来。长在树上的新叶子认不得他;几个娃娃更认不得他。抬头看看,那棵树比他还老……
二
离家远了,端起饭碗总觉得少了个啥。
一碗饭可以没肉,可以没油,但吃着让人安静。早上醒来,裹在被窝里的娃娃像鸽儿子一样叫得正欢。揉揉眼再看,女人忙前忙后做饭,收拾屋子。等穿好了,饭也上来了。酸菜羊肉也罢,土豆粉条也行,香喷喷的,把心都熏醉了。趁转身的一瞬,顺手在女人的屁股上捏一把,再看回过头的女人,笑里藏着一句话———真不是个东西。娃娃们不知道大人之间的事情,只是拿起筷子往嘴里扒拉饭菜。
吃完饭,眼睛也睁开了。背着手往出走,太阳照着很舒坦。走哪里,干啥事,女人不管,只是安顿早早回来吃饭。才吃掉又操心下一顿,很正常。村里的所有事情都和吃饭有关。走哪里能饿了肚子?能不吃饭?吃是人一辈子的事情,也是活着的主题。吃啥,咋吃,吃到什么程度,不是简单的事情。谁在吃上不讲究,那其他的事情也不好说了。在吃上,好多人一辈子啥没吃上就走了。有些人吃遍了山珍海味还没吃出个名堂。吃与吃不一样。中间的事情很多。有为吃打仗的,也有为吃快乐的。谁家女人的锅灶好,谁家的男人有口福,过一段时间都知道。哪家过大事,专门找锅灶好的女人上锅。听着谁谁谁帮灶去了,庄子里的大人娃娃都跑了去。吃完,都说,味道好。
谁知道呢。反正端上来的长面、干饭油水大、肉腥多,谁吃上谁舒服。吃上总比吃不上强。
背着手往前走,村子前面的河早就断流了,连冰都不结。裸露的河床有几个窝坑还能让人想起过去抓鱼的情景。现在河里没水了,光秃秃的,连鸭子都觉得没意思。
日头一寸寸往过移。有些时候,啥事都没干,又该吃饭了。刚要往回折的时候,女人喊着吃饭的声音飘了来,一直飘到半山腰,成了回音。回音里,饭香在嗓子间的感觉一寸寸成长为对女人的向往。很多时候,一顿可口的饭能把所有的不愉快忘记。在家里吃上一顿女人做的可口饭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回到家里,当女人亲手端上一碗香喷喷的饭时,在外所受的苦累释然而去。
一碗饭盛的是光阴,是亲情,是由不住的内心安稳。一个人走再长的路,只要听见几声喊他吃饭的声音,所有的陌生都会消失。可世上总不能老吃安稳饭。看看女人娃娃的眼神,不出去怎么能过上好日子呢。
很多人走出村子往外闯。他们在异乡吃着热腾腾的饭菜,却吃不出家饭的味道。一些人走着走着便想起家来,实际是想女人做的那锅香喷喷的饭菜。
有人从大老远的外面星夜往回跑,一直跑到村口的时候又不敢走了。他们生怕端着碗吃饭吃不出味道。
三
走累了就停下来。
走得再快也有停下来的时候。与其那样,不如累了就歇歇。歇好了再赶路。前面的路长着呢,再怎么走,头顶上都有云陪着,都有雨随时降临。再走,人也不过是一辈子。路边那些花到秋天会谢,到来年会开。花儿是风留下的影子,是风带给土地的风景。只要有种子,有根系,怕什么枯败盛荣呢。每年开春,不少花重新又开了。那些树也一样。它们生长的每一寸高度都和光阴有关。有一寸光阴,就有一寸成长。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冰霜侵凌,只要有一分劲就从光阴里往出迸。迸到什么程度,长成什么样子,全是自然的事。有时候硬撑着从地缝里长,弄不好就长歪了。成长的路没有顺利的事情。更何况前面的路是黑的,到哪里还没个定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