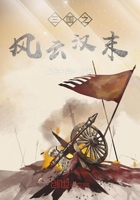洪师爷这个人平时为人持重,为东家辛苦操劳,这大半辈子过去,也积蓄了一点家产,老家手里还有两亩薄地,按照后世的眼光,好歹也算是个小康之家了。自己的前任东家李鹤年出事之后,洪师爷也受到不少人的邀请,不过他仔细考虑了很久,终究还是拿定主意回家养老,这官场的水实在是太深了,他不想临老在把自己也给搭进去。
不过,平日里那些官吏听说自己告老,便一个也不上门了,就是自己时常接济的那几个,也一下都躲的远远的,如今他洪琉熙就剩下这么点东西,一个小匾额,一副字画,仅此而已。不过这样他也满足了,至少在这样的无泥坑里,他还是交到了真正的朋友,就为这个他也对老天感激不尽了。
洪师爷刚才听下人说一个老朋友来访,一时也没想起会是那个,又不好让人久等,这才急忙回来。但见到老赵之后,两人先前共事时,便一直小打小闹地惯了,猛一见面也是改变不了,相互吹骂一气。他洪琉熙也就剩这么几个知心的朋友了。洪琉熙刚坐下,却才看见老赵身后坐着一个熊罴补子的年轻人,这人对老赵也算是恭敬。
老赵在那年轻人身边坐下,看到洪师爷满脸的疑惑,才想起他根本没有见过贾华,正要开口介绍一番,不料洪师爷却是先开口道:“老赵,看看你这也都六十多岁的人了,也不想想自己的平日的所作所为。这又是把谁家姑娘硬按倒床上的,不是我说你,都满头满脸的褶子了,我估摸着你这动一动恐怕都会冒出一身虚汗吧。居然这么禁不住寂寞,六十多岁生儿子,这样一看你老赵古今中外,也算个人物了。”洪师爷说完,见到老赵吃瘪的样子,喜从心来,猛地一阵大笑起来,直笑的眼角里几滴老泪“扑嗒、扑嗒”往下掉。
老赵一看洪师爷把贾华当做自己的儿子,自己都六十多了又怎么会生儿子,就算是能生,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长这么大呀!他被洪师爷这么一逗,真是哭笑不得,急得他急忙解释。
“我可没有这个好福气,这是我家老爷的孙子。”
看着不知怎么办好的老赵,洪师爷停止了大笑,干巴巴的眼睛眨巴了几下,嘴角还一个劲地蠕动。那眼睛看了看贾华,然后又继续大笑起来。这洪师爷一直笑了又约莫一袋烟的工夫,终于停了下来,清了清嗓子说了句:“老赵,你娘的,当我姓洪的是瞎子呀!这是小松子,你怎么不干脆直接跟我说他是你家老爷就得了,就你那些骗人的功夫还敢在我面前显摆?”
老赵也是憋了一肚子话想说,正不知从何说起好,一听这话登时两眼一瞪:“姓洪的,别给你脸不要,他是我家老爷的孙子不错,可你听我那句说他是松少爷了。他是桦少爷,是三爷的儿子,他刚从泰西各国回来,老爷见他伶俐,便给他补了个五品守备的缺。这不赶上郑工决口,老爷和李大人、倪大人当年也是过命的交情,这才让少爷过来,到郑工渠上历练一番。谁想听说您老人家要撂挑子回家,我这不才急忙领着少爷过来,想请你给他帮吧手!”
“当年贾大人从长毛刀里把我救出来,论说这个情我是要还的。”洪师爷摇了摇雪白的头颅,长叹了一口气:“这官场上的事呀!一言难尽啊!”
原来李鹤年被清廷充军新疆,洪师爷觉得对不住自己东家,那天便想着到一些同僚那里走动走动,看能不能将老东家弄回来。他一直忙到中午,却是没有一个人见他,没有落井下石那便是看在往日情分,这个时候大家那个不害怕引火烧身,也有好一点的破费些,让下人给他几十两银子,便将他打发出门。
人走茶凉,他本就有心理准备,但没有想到会如此淡泊。后来他想去京城找内阁学士张之万,在这官场上他最有交情的两人,一人便是告老还乡的贾钰信,另一人便是张之万。当下便谁也没有通知,只是知会了下人,让他悄悄地收拾了包裹,整好东西,当天就起程去京城。
坏了他事的是衙门的一个厨子,那厨子本来是李鹤年从山东请来的,这李鹤年一倒台,厨子自然也要回山东老家。等那厨子刚过前院,刚好看到洪师爷在收拾东西,似乎要出远门的样子,他并不知道洪师爷是想上京城去给李鹤年求情。还以为他和自己一样,要收拾东西回老家,回头便跟府里的差人丫鬟们当做闲话说了。这话立刻传到别人的耳朵里,自然是给添油加醋了一番,说他要上京城去告御状,还说他在李府大骂其他人,说他们忘恩负义丧尽天良迟早不得好死!
那些官吏一听这话那还了得,原本大家敬他,是因为他是巡抚大人的师爷。可如今李鹤年已经倒台,自身难保,这洪师爷现在在他们看来,那不过是蛤蟆臭虫一般,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便吩咐手下衙役去把洪师爷连同他的那个下人一起捉拿了,若是后来陈许道钱严出面担保,他们这才将洪师爷放了出来,让他告老还乡。因为黄河决口,一时走不了,后来这钱严又让人在花园口给他找了个宅子,并一应承担他的生活,这才安顿下来。
等他被李家的几个人吆五喝六地赶出来,然后又奇迹般的搬到这花园口镇上居住,这一切看似合情合理,背后的阴谋却瞒不过洪师爷的眼睛。他虽然现在老眼有昏花,耳朵也有些聋了,可这心里却明白的很,等他想明白这一切都是怎么一回事后,便先给家里头去了封信,让他们不要挂念。他自己却在这里安心住了下来。
那几天他看似有事,每日早早便出去,回来后已是日头要落,其实他那里都没有去,只是去看看郑工河堤,听听那些河工们的怒骂,或者想一些以前的事情,只有这样他这一颗心才能平静。
他会想糊涂虫的贾钰信,会想刚正不阿的张之万,回想那个时候的自己也是意气风发,曾经年少轻狂,所以贾钰信送了他一个“中庸”的匾额。可是想到现在他的心就会一揪。他也打算过收拾收拾东西,直接回家算了,可他清楚知道这样恐怕会连累家人,只能忍气吞声,学学贾钰信当年“难得糊涂”一回。
老赵听洪师爷没头苍蝇似的叹了口气,也不知道他是答应还是拒绝,便风风火火的急着追问道:“还是老样子,没见过像你这样不痛快的,说个话总是捕风捉影,让人一向听不明白。今天你是打不答应,给我个实话。其实你也知道,松少爷是实在人,老爷才不让他当官。好不容易桦少爷回来,老爷给他捐了个实缺。你这当难道不应该前辈的不提挈一把吗?我就看不惯你这个样子,一上来说话就东顾西望的。”
贾华听了老赵的话,差点没被自己的吐沫给噎着。因为哥哥是实在人,才不让当官的,这不是明摆着说自己不实在吗?“老赵,我想洪师爷一定有他的难处吧!咱们还是不要强人所难了!”贾华咳嗽一声,抬头看着匾额,掩饰自己的尴尬,对着老赵说道。
“不是我不肯帮,别的不说,就冲当年贾大人救我一命这份恩情,我也不能不报。不过我也是身不由己呀!要我帮你可以,但你要先答应我两件事情。”洪师爷想了一阵了,扭头对贾华说道。
贾华正一边看着那匾额,一面浮想联翩,忽听到洪师爷问自己,急忙回过身子,说道:“那两件事,说说看?”
洪师爷停下来想了很大时候,挥挥手让他那下人退下,老六眼色活,知道有些事情不该自己听,最好不要听,便也跟着退了出去,洪师爷见屋里只剩下自己和老赵、贾华三人,不禁一笑出声来:“果然有你爷爷的一半糊涂,什么东西都不会急着答应,看人下菜,看事用法。不错,不错!”
洪师爷夸奖了几句贾华,又捏紧拳头皱着眉头,好像怒火万丈的样子,才又接着说道“第一件事便是帮我搬到陈许道钱严,第二件事便是我只能帮你五年,五年后你一定要允许我告老还乡。”
“第二件事没有问题,至于第一件,我想知道为什么?不过不要告诉我是想替我爷爷报仇这样的鬼话。”贾华听完先是一阵惊诧,但他很快掩饰过去,接着不紧不慢的问道。
才开口道:“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贾大人是小事糊涂大事明白,桦少爷不学便已有他三分本事,难得!难得!”
洪师爷又夸了句贾华,这才压低声音说道:“大家应该知道前任巡李鹤年大人从同治元年到光绪十三年间,前后二十多年的时间,基本都是在河南任职。当年为平捻子,他还创建了毅军和嵩武两军,中间又兼任河东河道总督多年。这些年来他以训练团练、兴修河道为名,不知向地方摊派或朝廷索要多少银两,这些银两后来多数都流进了他个人的腰包。其实这里面有些事情,我也产与不少,正因这样我才想,早些脱身告老回家,这样就算日子难过一些,可到底是回老家以后,我那里还有几亩薄田,足以让我后半生无忧。可那里知道这个时候,黄河突然决口,这李鹤年也跟着一子倒台,又被发配新疆。”
“官场这滩水,比起黄河那是更加浑浊腐臭。这陈许道钱严本是李鹤年心腹,也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其实当年,为了能提拔钱严,李鹤年还特意让贾大人去审理开封教案,最后当了他们的替罪羊,被那群清流攻击,这才使他不得不告老还乡。”
“李鹤年出事后,他钱严不是想着如何救出恩师,这时想的却是当年李鹤年贪墨的那些银两,他知道我当了几任巡抚的师爷,又跟随李鹤年多年,应该会知道那些银子下落。先是暗指示人将我打入大牢,好让我断了解救李鹤年的心事。然后又充当好人,把我从监狱了救了出来,还安排房子给我住。这种欲擒故纵的手法,跟不算新鲜。”
“只是李鹤年当时做事小心,我虽然参与,多是出谋划策,根本没有人知道他把银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如今这钱严表面上看似对我客客气气,一但他失去了耐心,我这脑袋恐怕就得搬家。所以,我要你搬到钱严,不然我根本就是死人一个,又怎么能帮的了你。”
“这个没问题,反正钱严也是我的敌人,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贾华说了句后世人人都知道的名言,更是想都没想,便将洪师爷的事情答应下来。见他语气轻松,好像搬到一个道台,和小时候跟大家一起玩耍时捏个小泥人是同一件轻松的事情一样。其实此刻贾华心里翻腾的却是另外一件事,既然大家都想得到,谁也不肯放手,那么就一定要有一个人倒下,敌人倒下,总比自己倒下的好,贾华绝对是那种:死道友,不死贫道的人,所以钱严一定的死。
感谢47367001读者提供很多历史资料弥补作者不足,在此表示感谢!希望更多的人可以提出更多的好建议,让此书能够写的更加精彩,再次这位读者谢谢!
一章相当于别人两章,厚着脸皮求收藏!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