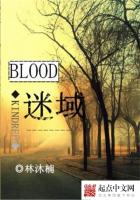周福匆匆换了袍套,手本都没有拿着就急忙出门。刚到北洋大臣行辕,他叫过下人,给门房每人都封了四两银子的钱票,给他们当做打赏费用。进了行辕门内,早就有管事的迎过来。朝着他微微作了一个揖,本来是想向他要手本的,好递交给自家老爷。却被周福仓促打断,求他到李中堂跟前回话,说自己有十万火急的事情,需要马上晋见。另外又送了这管事十两银子的“门包”。管事本来因为被他打断,心里一阵不喜,只是此刻见他出手阔绰,又知道他和自家老爷的关系,这才没有为难他,方转身去回话。等了一会子功夫,就见管事丛里跑出来说:“大人在里面等着,让你到客厅见面。”
周福听说李鸿章见他,心里总算有了些底,赶忙跟着管事向府里走去,先是到宣承差屋里,管事将一封亲供交给周福要他填好,所有事项又交代一番。周福却是没有接亲供,只是直接给了管事一些碎银子,让他将其他人替他打点停当,自己见中堂有秘密事情商议,不要在有别的啰嗦。那管事收了银子,这才又带着周福朝大厅走去。
两人进了大厅,就见正对着门口是一张供桌,供桌上面放着一只平时烧烟火的古鼎、一个瓶子、一面镜子。大厅居中放着一张方桌,两旁各有八张椅子,每张椅子旁边都会放着个茶几。正屋上面梁上,是几个像神像龛子的东西,红漆油成,四周描了金边,这是用来盛放‘诰命轴子’的。诰命,是古代皇帝对五品以上的官员的一种封典,把诰命裱成的锦轴就叫诰命轴子。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周福进了屋子,见正堂上正坐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他身穿五云褂子,官帽后面更是三枝锦鸡翎子,这人便是一等伯、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赏戴三眼花翎的满清第一重臣李鸿章。李鸿章见周福进来,只是问了句:“今天你不在衙门里办差,这么急急忙忙的跑到我这里做什么?
周福见李鸿章问话,不敢怠慢,急忙上前打千请安,然后才恭恭敬敬的道:“中堂大人神算,郑工河渠吴大澂果然派人到了天津。属下刚刚见过他们,这才过来给中堂您回个话。他们本来执意要见中堂,我按您说的,称身体不适。明天再见他们。”
“吴大澂这次派的是谁呀?你当时就没有留他两人吃个饭,他们过来天津一趟也是不容易。这是咱们自家的地头,不能太小气了,让人私底下说咱们北洋不通人情。”李鸿章说话的时候面带慈祥,就像一个慈善的老人在教育自己的晚辈,只是他那一双眼睛,明暗闪烁,让人猜不透他心中的真实想法。
“回中堂大人的话,来了两个,一个是郑州知府贾华,另一个是五品候补同知李胡,据我得到的消息,因为此次河道决口,原来的郑州知府被朝廷罢官,这贾华便因为上一次舍身围堵缺口,被倪文蔚和李鸿藻两人保荐,才补了他的缺。至于李胡,他是吴大澂的手下,算是跟着他的老人了。我们就在大厅里坐了一会子,本来下官也是想挽留他们,却在无意中得知一个重要消息,才不得不将他们打发走,急忙过来跟中堂大人商议。”
“是什么消息,居然让周大人如此匆忙呀?”西边一间房里,走出来三个人,为首一人三十年纪,一身青色马褂,严正干练,第二人却是身体发福,方面大耳,一身富态。第三人年过四旬,却是温文儒雅。这是人正是李鸿章的幕中主要谋士。第一人便是安徽泗县人,现任翰林院编修、庶吉士的杨士骧,字萍石、号莲府。第二人更是鼎鼎大名的晚清第一红顶商人盛宣怀,他是江苏常州武进县龙溪人,字杏荪,现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道台兼东海关监督。第三人更是了不得,他是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字幼樵,直隶丰润七家坨人,由于甲申中法战争中失利,他被发配新疆,后被赦回,现在仅仅只是个四品京堂。
“三位大人好。”周福站起身朝三人拱手致意,态度恭谨。
“忠旺,咱们都是自家人,就别这般虚礼客套了,有什么消息还不尽快说。哼哼唧唧的,你这是想吊咱们兄弟的胃口,还是要吊中堂他老人家胃口呀?”三人在李鸿章对面坐下,杨士骧看着欲言又止的周福,出口玩笑道。
“莲房老弟,你这玩笑可大了。就是借我一万个胆,我也不敢掉中堂大人的胃口,兄弟我只是想着如何说这事情。”杨士骧出身资历自然是无法和周福这种行伍出身的比,其官职也不过是个庶吉士,所以周福一直不大看的起他。若非不是看在他和自己是安徽同乡的这个情分上,周福连话都懒得和他说,只是冷笑一声,回了句。
“啊福,有话就说,有什么好想的,照实了说。”李鸿章瞪了一眼周福。
“其实还是关于郑工河堤的事。”周福一边说,一边盘算着如何能让李鸿章答应下来,给自己弄个道台当当,言语之间便有些吞吐。
李鸿章见他说话不像平常那般不利索,以为他有事想隐瞒,脸色一沉,开口骂了句:“直娘个贼的!在朝廷上要防着这个,提着那个的。这都下来了,难不成还要老头子我和你们猜谜语吗?有个什么事情,都掖着捂着,深恐我老头子知道。你们是不是都拿我当瞎子呀!”
见李鸿章生气,周福吓得有些语无伦次,更是说不成话。虽说平日李鸿章很是善待下属,可毕竟他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钦差体制,不怒而威。这一出口大骂,却是另外一种威严,即便当娘平捻子的时候周福也未曾见过,几乎把他吓昏过去。亏得张佩纶反应快,忙替他招呼道:“岳父,您是上了年纪的人,上回风寒还没有痊愈,医生可是有交代,您不能随意动气。忠旺,有什么就说什么,中堂这里还有什么好隐瞒的。”张佩纶最后一句是对周福说的。
周福腾的一声跪下,急忙道:“中堂大人,下官绝对没有要刻意隐瞒什么!下官只是想着郑工决口,总会空出几个实缺来,就想这补个道台的缺,一时间不知道如何跟大人开口说。这才说话吞吐,请中堂大人明察。”
“想补个缺,开口说就是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们这些跟着老头子的老人,老头子我是不会亏待大家的。”李鸿章一听周福只是想要个缺,心里的火才压下去,这年月那个跟着自己的人不想升官发财的。要官要钱,李鸿章并不怕,他只怕手底下那些人到处捅娄子,表面上还藏着,让他看不到,听不到。这种小动作,说不定那天会让他阴沟里翻个大船。
周福见李鸿章脸色,由阴转晴,连忙抛出一句:“中堂大人,我已经打听清楚了,倪文蔚怕是真的不行了!倘若他真的一撒手,这河南巡抚的职位决不能便宜了外人。”
“此话当真?!”杨士骧听还没有听周福说完,几乎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前些日子就有个朋友来看望下官,他说起过倪文蔚,亲眼见他咳血,当时我并不太信。便派人去郑工河渠调查,昨夜我派去的人回来说,倪文蔚却实有吐血迹象。今天早上郑工河渠来派来的李胡更是亲口说倪文蔚命不久矣的话。这样算来倪老头是肯定不行了。”
“你们怎么看?”李鸿章没有理会正暗自得意的周福,只是对另外三人问道。
“这河南巡抚的缺绝对不能要。”张佩纶朝李鸿章一拱手,决绝的说道。
“这个差事的确不能要,不过其他的藩司、臬司和道台的到是可以争一争。最主要的是郑工采买这个肥缺,一定不能落到别人手里。特别是那群清流手里。”盛宣怀呵呵一笑道。
“这个差事我们不要,可也不能便宜了别人。清流把持河南巡抚多年,早就有人眼红了。只要咱们从中点拨一二,用不着咱们出手,自然有人会跳出来。这样一来,那人为了感谢咱们帮助,恐怕藩、臬、道咱们还能多占几个缺呢!另外,那些清流可比不得咱们北洋,封疆大臣中,他们只有河南这么一个实缺。若是丢了河南巡抚,他们从此也就成了无根之萍,永远也别想成就大气候。这可是一箭双雕。”杨士骧在政治上,不像张佩纶那样迂腐,也不像盛宣怀那样注重金钱,他考虑最多的还是政治利益。
“莲房的意思是,让旗人出任河南巡抚。”李鸿章若有所思的点点头,问了句。
“旗人也不好东西!平日没有少给咱们下绊子,下官不明白,为什么要让给他们?再说了,咱们和那帮子清流还没争出个所以然,不会让人渔翁得利吧!”周福瞪了一眼杨士骧,气呼呼的说道。
“这大清国十位总督中只有湖广总督裕禄一个旗人,一十七位巡抚中,只有江苏巡抚崧骏、山西巡抚豫山和江西巡抚德馨三个旗人。其他皆为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因为旗人都只是会遛遛鸟,整日除了吃喝等死,别的什么都会。咱们汉人那个不是靠着真刀真枪,拼出来的功劳。”
“忠旺,你这句话只是说对了一半,不错,他们的确无能。正是因为他们无能,才要把这个职位让给他们,这样就不会像那帮子清流一般,处处和咱们北洋过不去。还有你要知道历朝那个不都提倡满汉一家,其实都是狗屁!那个敢放任使用汉人的。朝廷那天不总是在提防着咱们,江苏巡抚是为了牵制两江总督,山西和河南巡抚是为了防备咱们北洋的。只不过旗人太不争气了。没有一个像样的,不然河南巡抚这个职位,也不会被清流霸占了二十多年之久。至于渔翁得利,就要看看他们是不是有那个能力,当不当得了渔翁。”盛宣怀一阵冷笑的说道。
“话是不错,可总要提防些才稳妥,如今旗人里头,有资历出任巡抚的无非两个,一个是西安将军荣禄,另一个是三品京堂欲宽。荣禄这个人颇具干才,可惜他后来投错了门,成了六爷一党,才被罢了官。若是现在用他,一来对我们没有好处,二来怕是太后那里也通不过。不如就举荐欲宽,这个人读书学问到是可以,做事可就差个十万八千里远。这样的人没有大用,可至少不会祸害咱们北洋。”李鸿章考虑了一会,开口道:
“莲房,你明日就回京,这个事情亲自去办,但有一条你要记住了。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让欲宽和咱们北洋扯上关系,更不能上折子作保。不然,太后一定会猜忌,反倒让清流那帮子得意了去。这个老佛爷呀!我对她是太了解了!”
“中堂大人尽管放心,这个事情我一定会办的妥妥帖帖。这大清朝别的或许不行,若是想升个官,那门路可多了去。”杨士骧一口应承下来。
“杏荪、阿福,你们两个好好考虑下,看看郑工河渠所需要什么样的物资,然后写个条陈给我。”李鸿章又对盛宣怀和周福说了句,才转身对张佩纶吩咐道。“幼樵你这就替老头子我写个折子,就说郑工河渠所需物资巨大,牵连甚广,一时极难筹措,特举荐杏荪和阿福两人专门督办。”
“岳父高明,这三管齐下,接下来就要看看咱们那位翁师傅会怎么出招了。”张佩纶称赞一声,便不在说话,然后转身到一旁去写他的折子了。
李鸿章看了看张佩纶,心里轻叹一声,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他李鸿章也不例外,本来以为将女儿嫁给张佩纶,算是留住一个人才,那里知道女儿到是愿意的很,可自己两个儿子经方,经迈却和张佩纶八字不和,无时不想把他撵走,而且李经方居然密托天津海关道转御史端良弹劾张佩纶:“居北洋幕中,妄干公事”。若不是他李鸿章发觉的早,暗中给压了下去,这张佩纶夫妇恐怕已经不能在北洋呆下去了。这也让张佩纶学的乖不少,遇事从来不轻易开口。
“道希、柳门你们都看看这个折子,这是刚从河南郑工河渠上发过来的。”一个身穿仙鹤补子,头发花白的老人,将手里的一个折子递给身边的两个学生。
这两人都三四十岁左右,年龄较大一些的那人先接过折子,放在亮处,两人歪着头仔细看了一遍。翁府里蜡烛都是上等的牛油灯烛,两人看的很快,不过却都专心致志,深怕错漏过一个字。
“这是今天李鸿章的折子。”那花白头发的老人便当今皇帝——光绪的老师,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接着又将另外一份折子给了他们两人说,“李鸿章此番让他的心腹筹办郑工河渠物料,他这算盘究竟是何,以为我不知道吗?”
“老师,学生以为,这李鸿章这份折子,名义是为筹措郑工河渠物料,实则为了敛财。自去年老师掌管户部一来,他那北洋海军,各个款项我们控制的极其严格,他没有了海军方面的各种进项,自然会把注意打到别的上面。他这折子,我看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年纪轻一些的便是翁同龢的学生文廷式。他祖籍本是江西萍乡,出生于广东潮州,少年时便是在岭南长大,后来成为一代大家陈澧的入室弟子。光绪初,在广州将军长善幕中,与其嗣子志锐、侄志钧交游甚密。并且还做过现在贵妃——珍妃的老师。文廷式表面上看,一表人才,话语果决,常敢说别人不敢言之言,深得翁同龢信任。
另外一位学生是汪鸣銮,他是同治年间进士,浙江钱塘人。字柳门。先后在京城担任过庶吉士,授编修等职务。善于研究经学。后来外放历任陕西、甘肃、江西、山东、广东等地学政。光绪十三年专任工部侍郎。这时候他也看完了折子,双手交与翁同龢,才道:“学生也是这样想的。”
翁同龢将李鸿章的折子往桌子上一丢,哼了一声道:“郑工决口,国家震动,太后老佛爷和皇上整日寝食难安。身为臣子,不思报效朝廷,替君上分忧,为百姓谋福,却只想着从中捞取好处,此等人物,国之大贼!去年皇帝大婚,过几年便是太后六旬万寿,这都是理应隆重庆贺的。就算是花再多银子,局面再困难,那是为了尽臣子的职分,本无话可说。可是没想到,一个郑工河渠居然耗费如此多的银两,几乎伤及国家元气。我身管户部,常常为此忧虑。在皇上身边也有几次进言,让黄河改道。可老佛爷听倪文蔚之言,就是不允,又怕引起太后误会,这才压了下来。这次李鸿章这折子倒是个好机会。”
汪明銮道:“老师是想让李鸿章向太后进谏,停罢河工,让黄河改道。这恐怕不好办?”
“当然不是,停罢河工,对他李鸿章没有任何好处,他又怎么会听咱们的。”文廷式接过话说道:“不过这里两份折子却是来的太及时了,不如明日老师你再上一份折子,称户部已无款可拨。请求停罢河工,让黄河改道。若是倪文蔚和李鸿章勾结,必然会一意孤行,咱们就顺水推舟,让他们派人专办,此外我们也要派员到天津去,切实稽查他们的每一笔物资货款,让李鸿章从中一分钱也捞不到。另外老师掌握户部,却是一分钱也不能给他们,他李鸿章若是想把事情办成了,便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克扣海军经费。若是办不成,这黄河改道的事情,自然让他们去请旨办理。这样一来既打击了北洋海军,还消弱了他李鸿章的威名,一举两得。”
“学生也准备上一个折子,请派大员检阅海军!”汪明銮也接着说,“本来一个郑工河渠就能让李鸿章不堪重负,如此咱们就再给他加些力,自前年海军大阅后,今年正好三年。按照海军章程,正要海上大阅兵,内务府那帮奴才们,个个都是蚊子生的,只要闻到一点血腥,都是不会放过。当年李莲英一趟阅兵下来,少说也有几十万的进项,这等挥霍,要不了几次,北洋海军必然会被生生拖垮!”
“好!”翁同龢听了后,虽然有些振奋,不过他还算清醒,“只有你们两个还不行,还得让上书房和南书房那些人都要做出响应才行!”
“上书房那帮旗人大爷,早就看李鸿章不满了,只要咱们喊一声,自然会有人应和。只是南书房恐怕要老师出马,先知会他们一声,想来他们也会买这个面子给老师的。”文廷式言道。
翁同龢点点头:“这样也好,不过我心里还是不踏实。”
汪明銮道:“老师是担心那个人吗?”
文廷式忽然警悟道:“万岁爷?”
翁同龢叹了口气:“正是。皇上对李鸿章可算是圣恩隆眷,他每次进京晋见,皇上都会对我说:‘翁师傅,李鸿章和你都是朕的股肱之臣,朕知道当年因李鸿章弹劾令兄翁同书一事,你们结下宿怨。但国事为重,你们更要同舟共济共济才好,千万不可因私废公。’若是他为了保住海军军费而来,故意搪塞,到时候不但贻误郑工。我还担心李鸿章会倒打一耙,把责任推给咱们户部,皇上恐怕也会站在他那边。这个人的算盘之精,不是你们可以明白的。他心目中只有他的海军和淮军,只有他的地位和荣宠,什么为圣上上分忧,替江山着想的话。他是根本会去考虑的。”
听翁同龢这样一说,文廷式和汪明銮两人半天都没作声,只是看着桌子上的那两份奏折,文廷式又翻了翻,这才说道:“既然如此,咱们就先让皇上下个旨意,到时候就是皇上后悔了,想收回来,恐怕那些眼睛里不停的盯着海军和淮军的旗人大老爷,也不会同意。如此一来就算他李鸿章浑身是铁打的,恐怕也得乖乖交出海军。”
“皇上下诏!”翁同龢想了想,“这也是个法子,可如今大权都握在太后手里,若她不点头同意,皇上只怕很难做这个主呀!”
文廷式微微一笑,道:“老师常在宫廷走动,应该知道现在后宫之中,最受太后宠爱的便是珍主儿。我当年在广州将军长善幕中,与其嗣子志锐、侄志钧交游甚密。并且还做过这位主子的老师。若是让学生去找这位主子,只要在太后那里吹吹风,这样一来他李鸿章想不倒台都不行了。”
“哼!”翁同龢猛然站起,对着文廷式骂了句:“国家大事,岂可寄与女人之手。”说完之后,将袖子一甩,便不再理会文廷式和汪明銮两人,独自回后堂去了。
文廷式一转身,见汪明銮也是摇摇头,表示他也不赞成文廷式的方法,又低头看了一眼桌子上的两封折子,无可奈何地叹口气,随即也起身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