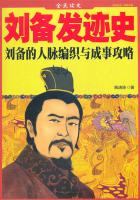手术是成功的。一位医生对梅魁说:“你伯伯真是一个奇人,我们估计他可能受不了的时候,他连一声都没哼过。”
手术后的两个来月,他的体重恢复,饭量增加。彭总自己也说:“看来我的手术效果不错,这一关又闯过来了。也好,搞清了我的问题再去见马克思,省得到了他那里再交代。”
病情好转了,他的心情也渐渐好了些。梅魁发现:伯伯依然是爱开玩笑的、幽默的,讽刺人的时候依然是很尖酸辛辣的。
有一次,专案人员在接梅魁来医院的路上,对她说:“你伯伯又发脾气了,骂人了。我们对他讲林彪爆炸的事,他一直不信。前几天还说是我们有意骗他,要引他犯错误。还说:‘林副主席永远是健康的!’他这样不好啊。你这回去,要做做这方面的工作,可以给他讲讲形势。”
梅魁说:“不行不行,我水平低。形势,我自己还搞不清,会讲出错来。林彪的事你们拿文件给他看嘛,他怎能不信?”
梅魁话是这样说,但等专案人员不在场的时候,还是悄悄提醒他:“你再不要喊‘永远健康’了,林彪爆炸了,死了,这是真的!”
“他们给你讲了我不信?”等梅魁点头之后,他笑了,笑得咯咯的。“我什么时候喊过‘永远健康’?砍我的脑壳我也不会喊。现在我偏要喊,气死他们!”他说着,把手掌贴在胸口,比划着喊了起来:“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纵情大笑起来。
专案人员就在门外,闻声便大步跨了进来,彭总收住笑,故意说给他听:“林彪爆炸了吗?怎么可能?这窗户还是糊得死死的,一丝阳光都不让我见到,这种缺德事,不是林彪,别人谁干得出来?什么时候我这屋里是黑的,我就不相信林彪死了。我就要说,林彪的魂还在!他永远是健康的!”
即使在彭总动过手术,一动不能动的时候,这间三〇一医院外科三楼上一条长廊最尽头的病房里,依然是门窗紧闭,门口守候着专案人员,廊外站着哨兵。彭总和梅魁多次提过,能不能只把窗户的下半部糊住,让上半部透点阳光和空气呢?专案人员每次都说要请示研究,但每次都没有下文。彭总怎能不火呢?
他的话算说对了。直到他死,他的房子都永远是黑夜;直到他死,林彪的魂都还附在“四人帮”身上,继续在作恶逞凶。
但,病情的好转,毕竟又在他的心头唤起了他对大地、对未来许多美好的向往!
夏天到了。梅魁穿一身换了季的衣裳进来,他说:“呵,外头都暖和了,穿单衣了?树叶都长满了吧?城里又是一片绿了吧?我,还在冬天里过哩!”
梅魁对他说,毛主席最近批了好些文件,说要解放犯错误的干部,工厂里好些过去被打倒的老同志又站出来工作了。
他听了很高兴,说:“梅魁,你说,有一天真要再让我出来工作,我干点什么好?”
梅魁说:“你什么也别干了,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养活你。闲不住,你就领着孙子们去逛逛公园吧!”
他说:“对对,我出院以后,他们总该给我说点什么了。那一天,我一定领着你、玉兰、康白、正祥,还有你们的孩子,先到公园里玩个够。你们小的时候,我工作忙,把你们交给学校就很少过问了,今后要补上这一课。不过,靠你们养老可不行,我还要工作几年。我想过啦,回我们家乡去,回太行山去也行,去种地。我要给党写个报告。要求交给我一个公社,或者一个生产队。我敢立下一个军令状,只要三年,搞不好我自己再把右倾的帽子戴起来。我早就想说这句话了:与其把我关起来,不如让我去劳动嘛。这样搞呀,真叫你有劲没法使啊!”
梅魁用眼色提醒他:外头站着人哩!他却更大声说:“这话,我到哪里都敢说!你说你那一套好,我觉得我的想法也不错,有什么呢?大家都试试嘛!给我一个公社,让我作三年主,先给我这点权力,先把我的右倾帽子放在一边。三年一到,我不行,把我的这点权力收了,把我的帽子戴上,那该叫人多么心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