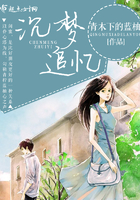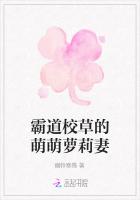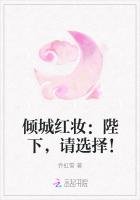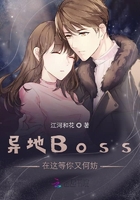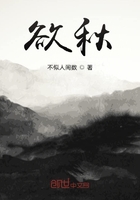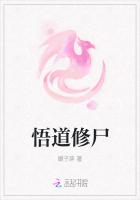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重估问题一直困扰着学界,其中,断定现代中国文学“断裂”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声音一直占有相当的分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对此的回应虽然不断出现,但似乎都流于为“断裂”而掩饰,这样似乎还不足以直接面对“断裂”之说的挑战,究竟中国现代文学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存在这样的“断裂”,我们又当如何来评判这样的现象,在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的今天,有必要认真回答这一问题。
李怡: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出现了许多值得我们深思和反省的思潮或者说声音,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对五四新文学开启的现代文学的性质、价值取向等的重新认识和估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估价中,有一种声音显得非常突出,这就是五四新文学出现了与传统文学的根本断裂。而且,在一些批评家那里,多次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共同作为新文学与传统文学发生空前断裂的标志。这在某种意义上构成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文学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主流的声音。这种声音到目前,已引起许多研究者的注意,并不止一次对其进行质疑,表明了不同的态度。但与断裂论声势如潮的景象相比,质疑和回应的声音还显得很微弱,力量不够。
毛迅: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中国现代文学甚至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合法性及存在根基将变得晦暗不明,令人生疑。仅仅从对现代文学学科的自我维护目的出发,即为了对现代文学学科本身负责,我们也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重新反思。断裂论的这种武断和随意性可能从另外一个层面完全遮蔽了新文化运动发展的一些本质。新文化运动以来延续了这么多年,现在一下要把它彻底摧毁掉,那么,我们如何能够退回到新文化运动以前,这种可能性存在吗?从时间的层面看,历史不可能退回去。而从内在逻辑的层面看,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与传统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断裂。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深思熟虑的清理和分析。因此,对断裂论回应的声音总是显得柔弱,不足以与之抗衡。
李怡:这里有一点必须要认识到,很明显,过去有一些长期从事现代文学的学者对断裂论还是有一种本能的反对。但是,他们的回应的力量很弱小。原因在于,他们往往简单地用不断裂来对抗“断裂”。有人提出,我们的新文化和新文学与传统文化与文学断裂了,他就认为没有断裂。但他在提出没有断裂的同时,却没有回答一个文学史和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现象。的确,现代文学与传统发生了一些不一样的改变,而断裂论者恰恰抓住了这种改变了的形态,在某种意义上夸大了这种改变了的形态或现象,或者说混淆了它改变了的实质。而反断裂论者似乎又想极力抹杀这种改变。前者夸大了这个改变了的事实,而后者则是有意识地回避了这个改变的事实。因为他们没有找到描述这种改变的更好的方式或概念。我们既要承认这种改变,同时又要证明这种改变是有意义的,并不是简单的一种文化上的断裂。
毛迅:从这个意义上,重新提出这种反思,同时在阐述我们对这种现象的看法时,找到一种更新、更有力的叙述方式,在今天显得尤为必要。
李怡:对于“断裂论”,从学术史的角度去寻找其根源,我认为有几个因素值得注意。首先,近代以后,从中国文化自身的转型来说,它承受了来自西方强势文化的挤压,这种挤压不仅是历史事实上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它构成了我们的心理事实,从心理上承受了许多西方文化的挤压。在这种情形下,如何看待自身的力量,看待自身文化的发展规律,也就是说,在承受了如此大的心理挤压的情况下我们能否准确描述出外来的文化与我们自身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第二,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后,整个中国文化界有一种很自觉的对80年代比较明显的西化的批判和检讨,这一学术思潮对于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主流话语产生重要影响。我们看到,90年代后如新儒学的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以及海外汉学尤其是美国的汉学界,在他们的立场对中国新文化也提出了一个加强对传统文化接受的问题。
毛迅:它实际上成了学界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貌似合法的主流话语,一种权威判断。一旦我们讲到现代文学及现代文化,断裂论就成为一个对整个新文化进行彻底批判的理论起点,一种习惯姿态:五四新文化成为与传统断裂的边际,也是一个标志。而这样一种断裂论,其表面形态上的合理性,或者说现代文学研究界对其回应的软弱无力,使得它已经成了一个被固定下来的知识,形成了一个普遍的误导,而其背后的若干的理论问题,无论断裂论者还是反断裂论者皆没有对其进行清理和反思。
李怡:其可怕性就在于此。它已经成为青年一代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新文学的知识构成。
毛迅:我们今天就是想再次对这个基本上要固定为知识的论点——其内在的缺陷甚至是逻辑上的错误进行清理和反思。其实,断裂论及后来衍生的失语症、西方单向影响说等,其逻辑上存在许多问题。首先,传统实际上是连绵不断的,就像艾略特所说,它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就像河流的运行,它不可能被人为地彻底断裂,断裂了就是没有了。即使是修三峡大坝,也只是将长江阻隔了一下,不可能将其彻底消失,长江仍然是长江。传统这条大河,实际上不断有新的河流新的支流的汇入,然后进入一个新的广阔的世界性的海洋,它是不断汇入、融会和发展的过程。
李怡:这个比喻非常形象。拿我们长江、黄河来说,从其发源地到汇入东海黄海,这整个可以来说明我们的传统。从发源地到入海口,构成了滔滔不绝的传统之河,中间经过许多不同地形,形成不同的状,但是,其源头和终点是不变的。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有其他的河流其他的水源汇入,像长江中途就汇入了金沙江、岷江、嘉陵江等,它们是构成长江的主体水流的有机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途这些水源的滋养,长江依然是长江,而有了这些水源的滋养,长江并没有变成黄河。因而,传统它是一个延续不断的自然过程,不是简单的可以人为截断的。在历史上,黄河经历了多次改道,这是基本事实。但是无论黄河怎么改道,我们关于黄河的描述都是关于黄河的历史事实。同时,如果不进行汇入支流,黄河不改道,更不能叫河流。像河流一样的传统,从古至今,绵延不绝,到今天还在滔滔不绝流动这一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变化——一定的变化本身就是传统的自然的内在需求。
毛迅:也就是说,汇入、吸收,这样才能保证传统之河流得更远。从传统之河的界说,我们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传统实际上是一个不断生长着的有机体,其生长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元素加入。从世界文化史发展史看,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它都有一个向外融会、生长的过程,如璀璨的古罗马文化就融会了古希腊文化,英格兰文化是融会了盎格鲁一撒克逊文化,并融会凯尔特文化、古罗马和罗曼文化的结果。今天的美利坚文化则几乎是在英格兰文化的基础上融会所有世界优秀文化的结果。它不是凝固不变的,总有新的元素加入并一直在有机地生长。那么,就拿中华民族自身创造的灿烂文化来说,它的形成也不只是一个单调的最原初的所谓中原雅音这样一个单一的声部,而是由华夏文化、楚湘文化、河姆渡文化、巴蜀文化等许多区域性文化元素的不断加入而构成的。再加上少数民族的交往如西域、北狄、北域文化等新元素的汇入才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成了一部丰富壮丽的交响乐。
李怡:的确,在文化发展的事实上,每当在自己的文化发展过程中有机地融会了其他新的文化因素的时候,中华民族的文化就显得非常的强势和有力。比如,唐代对各种新的文化因素包括当时的西方——西域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部分融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唐之势。这也就有力地说明了,传统自身是如何通过对其他文化的融会来保存自己的生命力,从而成长壮大。一种民族文化形态它要取得世界性的认同,它就是要不断地在融会中生长。这是文化本身生长、发展的逻辑。它只要不凝固,不死亡,它就会不断寻求生长的可能。那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以后,它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仍然是一种生长、发展、融会的关系,并不是对传统的断裂。事实上,回推到五四前的那些历史阶段对外来因素的吸纳,我们都认为其是中国文化。而五四以后,为什么一些新融会的文化因素进来之后这段文化反而就不叫我们的传统文化?而叫断裂?这显然是荒谬的。传统作为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它要沿着其内在动力或者是指向发展的话,这自然引出另外一个话题,同样看到断裂论的逻辑矛盾。这就是,传统一旦形成了传统的一种形态的话,它就形成了自身的内在结构。
毛迅:或者说,借用一个结构主义的说法,它就有它这个传统的深度模式。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去探讨中国文化的深度模式是什么,我们相信中国文化有自己的深度模式,那么,在这种深度模式或是逻辑的限制下,不管是怎样的吸收它都不会改变其生长方向——也就是它本质性的特点。
李怡:在传统之河从源头滔滔不绝向前的流动中,任何人为的切断都是不可能的,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水在这里体现了其内在的韧性,也就是其内在不可阻挡的逻辑指向。任何一个历史形态的归纳——归纳成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某种意义上都带有某种策略性。我们不能因为作出了这样的归纳,就从根本上忽略掉他们内在的有机的连续性。我们说,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它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现代。这个现代,在某种意义上,它的确区别于传统,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正是这样一个区别于传统的所谓现代又继续构成了传统的一部分。以至于当我们今天说中国文化的传统时,这一传统其实就包含了现代文化。
毛迅: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面对的过往的几千年的传统,实际上也经过了无数次的现代。古人当年面对的传统和我们现在面对的传统并不等同,我们现在谈古文运动时,那些当事者们眼里的现代,对我们来说仍是传统。我们所说的现代,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将变成过去,也就成了未来人们看到的传统的一部分。任何现代——历史上的无数次现代,包括我们今天置身的这个现代,共同构成了传统的整体,所以,我们不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方式来理解我们今天的现代与几千年的传统的对立,这是非常粗陋的处理方式。就像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里所写的那样,过去、当下和未来其实是相互渗透、包含的:
Time present and time past
Are both perhaps present in time future
And time future contained in time past……
李怡:事实上,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具体实践来看,这种所谓的断裂论也是站不住脚的。比如,我们抽取现代文学创作中最西方化的创作现象如象征派、新月派、后来的新感觉派及九叶派等来考察,他们的创作是被断裂论者认为是最西方化的,好像是与我们文学传统不一样的形态,但当我们很深入地进入他们的创作文本,做到真正的熟悉,我们会很容易地看到,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明显的传统的思维模式及文化逻辑。象征派、新月派等,是现代诗歌史上比较自觉地向西方靠拢、自觉沟通中西两种文化的典型例子。我们还可以通过现代文学史上那些有意识地尖锐提出反传统的诗人,我们依然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典型的中国式思维及中国式情感。这也同样可以证明,传统文化、传统文学作为一种深度模式的现实存在,比如,典型就是40年代的穆旦。他的反传统恐怕在整个新诗史上都是十分突出的例证。他甚至公开说过旧诗读多了对创作新诗没有好处,王佐良对此还有一个判断,他认为穆旦的成功就在于他对中国传统的无知。我们现在就是要透过这样一些表面化的判断,去探究它的实质。根据今天一些学者的分析,像穆旦的《诗八首》的思维模式也与杜甫的《秋兴八首》有内在的关系。
毛迅:事实上,如西方象征主义,实际上与我们诗歌传统中的某些内在思维方式比较相通。正是这样一些思维形式的内在相通,才构成了新文学主动接受的基础。虽然中国的传统诗学中没有象征主义这样的说法,但仍有托物寄志、假象见义、象外之旨、思与境偕等某些与象征主义相似、相通的诗学思维。这就使得西方象征主义很自然很顺利地在我们这里生根、开花、壮大,这里面隐含了一个道理:凡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实践中能够强势生长的那些外国诗学文化,包括象征派、意象派等,恰好就是因为它们契合了中国相应的文学与诗学传统中的思维方式与欣赏习惯,才可能生根开花。
李怡:这就证明,在实践的层面,是我们文化传统内在的东西在决定我们对外来东西的选择和吸收,这种选择并不是漫无边际的。同时,也就更说明了,在现代文学中即使是那些最现代主义的那些层面的实践,其骨子里面仍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模式的指引下来展开的。
毛迅:所以才可能出现当年中国现代诗派试图沟通中西诗歌根本处、在晚唐五代诗歌与西方象征派、意象派诗歌之间寻找艺术融合契合点的各种探索和尝试。这种情况之外,还有更多的不断主动地向传统回归的潮流。它们虽然是用白话写新诗,用白话写散文、小说,语言形态上好像与传统的语言形态不一样,但在很多方面,如审美观念、意象选取、情绪、音律上有主动回归的倾向,比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诗中的金柳、夕阳、青荇、长篙、星辉等意象的选取以及双声词、顶真手法等的使用,都显示出该诗的传统韵致。因此,新诗语言形态上的差别并不能断掉其与传统的内在的精神联系,一种非常牢固的血缘关系。鲁迅也是一个典型。他作品中对故乡、对三味书屋的复杂的留念之情,表明其骨子里充满了对传统文化难以割舍的复杂情结。新文学创作实践中的这种对传统的细雨润无声似的依恋,从新文学诞生始就从未中断。一直到40年代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理论主张,可以有力证明,新文学从来就没有真正放弃过传统。除了新文学的主流之外,实际上,在我们主流文学史所忽视的广大的白话通俗文学创作领域,其与传统的血脉关系就更为明显,如当时以传统的章回小说形式书写的通俗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等。
李怡:这也说明,我们文化的内在精神结构在起作用。除此之外,许多新文学作家,公开表示就是要从传统文化中极取营养。比较极端的表现是通俗小说和旧体诗,如许多新文学作家公开发表了许多新文学著作,但他同时又不断地写旧体诗。在诗人唱和之间,表达、排遣个人心绪时他自然就选择了旧体诗。如鲁迅、毛泽东等。当他要表达自己最内在的情感时,他就用旧体诗,似乎只有这种方式才能表达尽他的内在情感。再就是刚才所说的中西交融,对传统的自觉和西方的自觉是并行的,如新月、现代派,他试图把传统和西方沟通起来,通过沟通更好地将两者的精华吸收。
毛迅:上述列举的事实说明,传统文化的血脉实际上无所不在,既有显的层面也有隐的层面,一直在流动,从未断裂。可以说,潜移默化的深度承传是绝对“在场”的,断裂只是一种假象。
李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再对所谓反传统——这个偏激口号的存在现象加以研讨。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新文学的始作俑者们的确有许多偏激的口号或者说偏激的言论。但从刚才的分析,首先可以得出,无论怎样的偏激,他都没有从总体上——生命意义上改变他与传统的联系。可以这样说,传统的运行是以多种方式存在并进行的,就像河流有支流要改道一样。但有一种运行方式我们必须承认:传统的延续是通过对他自身的一种反叛性的调整来构成的。打个比方,一个胎儿如果要获得自己独立的生命,就必须先要与母体断裂,如果断裂指的是这样的方式,则这个断裂就是合理的。胎儿如果不从母体断裂出来,他就无法成长为一个生命。但是,他并没有达到那些指责新文化运动的那种意义上的断裂,他们的断裂意味着与传统毫无关系,成了一个异类。一个婴儿从母体诞生后,他并不是生命的异类,他恰恰是充分地吸收了来自母体的营养,甚至接受了她的生命基因、血缘等才成长为一个健康的生命。这种断裂是形态的、生存方式的改变,内在的血脉则延续下来了。
毛迅:如果以婴儿降生为例,那么,降生这种形式所体现的反叛、断裂,恰恰是他继承传统的必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理性地看待一些反传统的行为。这种行为本身就构成了传统自我有效延续的调节办法。因为脐带的割断,是切不断血脉、基因之间的联系的。另外,有时候,偏激的言行——全盘西化的诉求更多的是一种策略。在特殊的语境中要发出一种声音让所有的人来关注,或者说让很多人能够听到,也许就要用一种过激的方式使声音放大。或者,这种偏激就是某种政治上的需要,是就传统的负面因素(对国家的未来、命运的发展有阻碍的因素)从民族救亡的角度来审视、言说的。反传统实质上是反传统文化中阻碍中国向现代社会形态发展的封建专制主义,并不意味着是对传统文化的所有形态、所有内容的全盘否定。
李怡:这也是一种生存的需要。因此,任何一种理论的表述,任何一种语言、概念,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之下,才能准确地判断其真实的意图,离开了语境,单纯的一个词如高、矮,都是一个不确定的漂浮的词语,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高、矮,只有放在特定的语境下,我们才能准确地说出这个词的含义。那么,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为例,当时整个传统文化对新生事物构成了巨大的压力,足以令稚嫩的新生命窒息,这个时候,新的生命为了获取生长的可能性,它的确会采取一种在我们今天看来比较偏激的方式来击破这样一种自我束缚的外壳,只有冲破这个外壳,才能找到一个新的生长点。这个偏激本身具有合理性。我们要理解这个偏激就必须结合当时的整个文化语境对他的影响。没有如此强大的来自传统文化对他近于窒息的挤压,也许连那个偏激本身我们也不能够发现。
毛迅:一潭死水,要它起点波澜,必须要投石,以近似破坏的方式来将其激活。其实这种破坏方式的指向还是封建主义。如果我们再进入那些当年偏激过的文学大师们的文学实践中去,我们会发现,其实他们有着似乎言行不一的整体效果。他们喊出来的极度偏激的言语与他们创作中的那种对传统的依恋往往是矛盾的。比如,鲁迅,其许多杂文里的反传统言论极度偏激,但实际上他对富有传统意味的哪怕是社戏,哪怕是百草院、三味书屋中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血脉相连的依恋。对于这些偏激者们来讲,一旦进入母语表达的层面,自然就接通了与传统的血脉的联系。
李怡: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如新文化的猛将陈独秀、胡适等当时是全盘西化的代表。胡适、陈独秀曾公开宣言,“无反对派讨论之余地”,说得这样偏激。但在胡适的白话新诗中明显可以看到宋诗派的影子,而在陈独秀身上我们清楚地看到那强烈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政治情怀及忧国忧民的追求,他们可以说是两个典型的传统文人。
毛迅:所以,通过认真的事实分析,我们看到,当时喊出偏激口号的人,恰好是用传统的文化方式来反传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传统。其出发点还是想把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扬弃,使传统在吸纳了新鲜血液后变得更加的有活力。实际上,这些反传统者极其的珍爱传统。像徐志摩那样一天到晚言必称西方,对欧洲充满了向往,一旦涉及关于中西文化比较时,他还是认为西方除了船尖炮利外,并不比我们好多少。所以,他在《马塞》一诗中写道:“我爱欧化”,但接下来的是,“然我不恋欧洲”,“不如归去”。这些表面西化的人骨子里其实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是真正的珍爱传统。其言行不一,似乎也表明了他对传统的怒其不争的哀怨式的反叛。这实际上也是对这样一种危机感的激进表达:如果我们传统中的负面因素不清除,则传统中的瑰宝就真正可能被他者灭掉。
李怡:因此,当我们今天要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评价、判断,分析他的基本形态时,究竟应该如何全面地把握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追求的事实?是仅抓住一些只言片语、表面的策略性理论,还是要更全面地认识他们的全部精神成果,特别是作为创作成果的文本——文学文本本身?我们必须慎重地对待这个问题。最近几年,我们的文学批评出现了这样的趋势,自觉不自觉地进入纯理论的建构,而忽略掉了对文学文本的深入细致的解读和分析。我们往往简单地满足于一些表面上的一种清晰的结论,并且就把那些表面的清晰的理论化的东西当做文学事实的全部,这显然是一个非常片面的对文学的一种观照方式。
毛迅:一种非常简单到粗陋的学术研究方式。
李怡:这种态度在逻辑上呈现出一种有趣的悖谬。当我们在指责五四新文化人他们充满话语霸权时,恰恰是我们对那段历史充满了更大的主观、武断的霸权色彩。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现象。文学重新应该回到文学文本的丰富的事实中来。我们首先必须将对文学文本的更加全面、仔细的解读作为起点,才能够分析到底现代文学与传统有什么样的关系。
毛迅:实际上,对文学事实的仔细关注和分析,相当于在法律个案中寻找证据。一个人反传统,不能简单地看他喊出了什么,而要看其真实的动机和反的结果是什么。就五四新文化运动来看,虽然人们喊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和诉求,如我们上述分析所见,其真实的动机实质上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更健康的发展,是为了“走出去,更好地回来”——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他所在的传统更长久地延续,长盛不衰。这种现象在外国文学中也很常见。如拉美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墨西哥具体派诗人帕斯就说:“为了回到原点,首先要敢于走出去,只有浪子才谈得上回来。”古巴的卡彭特尔也说:“对古今外国文化的艰苦探讨和研究决不意味着本身文化的终止。”从拉美文学自身向外的吸纳或者说反叛传统的过程来看,其动机都是为了回去,是为了自身文化的更好发展,而最终也以其独特的文学风格耀眼于世界文学之林。那么,对今天的我们来讲,如果我们找到那些激进的反传统的文化大师们的真正的动机后,从他们的文本事实出发,就可以理解真正的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文学对传统的真实态度。
李怡:在认识到这点的同时,我们的确要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确实发生了一种改变。只是,这种改变不能简单地称为断裂,我们可以寻求一个新的概念来表述它。
毛迅:从近年来的不断反思中,我们觉得,不管是断裂论者还是对断裂论者质疑的人,都对改变这个事实没有进行很好的理解和分析。其实,改变不等于断裂。改变的内涵是生长,而五四新文化也不是要断裂一个传统,而是要通过对传统的改变使这样一个传统得以更好地生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陈代谢的机制,如果这种机制停止了,生命的机体也就死亡了。
李怡:这实际上是一种避免死亡的积极方式。因此,我们现在再来看,所谓由于西方文化大量引入而造成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失语症的担忧,虽然我们很同情、很理解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忧虑和热爱,其实这种忧虑是大可不必的。
毛迅:这种现象与其说是失语,不如找一个更好的词来描述,这就是:变声。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中,从婴儿的牙牙学语到成长成熟,其间会经历多次的变声。只有经过了多次的变化,他才能更好地适应这个世界,而这变化本身是自身生命体发展的一个自然现象。而且,他代表了生命体不断成长的趋势,不能说一个人从童音变成了成年声音后,这个人就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尽管一个人在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时说话的声音不同,但他仍然是在其自身的生命轨迹上沿着其从母体继承来的染色体、基因、血脉在生长,他还是他。变声是生命机制作用的自然生长过程,并不等于生命轨迹的断裂。
李怡:事实上,与变声相类似的人的机体还有很多变化,如婴儿时期的牙齿并不能保证他一生的进食活动和需要,所以在青少年时期到来时会自动发生换牙现象。人的机体的这种变化都是为了保证机体的茁壮成长,所以我们不能对机体自身的这种变化大惊小怪,以至于不能忍受。
毛迅:而断裂论及在其影响下生发出来的失语症及西方文化单向影响论等,所表征出来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将要失去的焦虑,实际上是一些人对自己变声后的新的声音的不适应而产生的。由于人们对自己传统变声后的新的声音的不熟悉,因而造成了广泛的焦虑,这种焦虑甚至误导了许多人对我们自己的正常的健康的生长过程的错误认识。事实上,喊出断裂论、失语症的人,他们的声音也已经变过声的了,而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用变了声的声音在试图说他想要说的童年的声音,但那种童年的声音连他们自己也说不出来了,或者是不会说,或者是已经没有必要说。但是,童年声音所言说的内容,也就是一种文化的精神,在我们变了声的声音里依然可以说出,也就是说,并不一定要讲“风骨”,才能道出“风骨”所承载的那些义涵,用变了声的现代汉语,用当下的其他语词,应该是完全可以把“风骨”、“气韵”一类传统话语的内涵表述出来的。
李怡:而对我们已经变了声的新的文学和文化形态的漠视,实际上,也就是对我们自身的生命的进一步成长壮大的限制,在更大的意义上影响我们更清醒的自我关照——更清醒地为我们的未来找到一个发展的方向。
毛迅:也就是说,我们未来的选择必须是在对我们的新声音的充分的了解、适应的基础之上。换言之,进入到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的文化与文学,在其内在的逻辑理路上,一直在寻求更健康、更丰富的生长,它是我们传统大树上生长出来的不一样的美丽枝条,从来就没有与传统的根真正断裂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