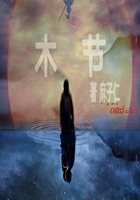如果仔细观察苏锦深的脸,很难用一般的标准去界定好看还是难看。鹅蛋形脸,偏瘦,颧骨微微有些突起。眼睛很大,所以即便微笑起来,眼睛里也会全部充满笑意。鼻子和嘴巴都是小小的。耳朵藏在头发里,偶尔一低头露出耳垂,完全没有任何穿过耳洞的痕迹。把五官拆开独立来看,好像都不够精致好看,可是放在一起,又出其不意的和谐,似乎天生就应该这么搭配。给人的感觉,就好像一头鹿,温和里有一种机警的疏离感。头发黑亮,修剪出漂亮的弧度和层次。
苏锦深低头喝着汤,陈致善得以肆无忌惮地端详她。淡粉色衬衫,深灰色西装窄裙,西装外套和手提袋搁在旁边的椅子上。画着些许淡妆,不是精致用心的那种,好像只是为了告诉别人她有化妆这件事,但因为只是极简单的妆容,所以倒也不会显得突兀或者令人反感。
他很久没有直面一个陌生人并且与之交谈了。不过苏锦深在陈致善心目中,也算不得是陌生人。或许当年平行时空里的交汇,就已经开始过一场没有语言的交谈。
现在的她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似乎应该是有着稳定的工作事业,以她的性格,应该会得到老板器重吧。在簇拥的女生堆里浅笑的十七岁少女,在这个拥挤的城市和嘈杂的人群里,还保持距离吗?陈致善一边抽烟,一边在脑海里飞过这些念头。
“借个火,可以吗?”年轻女孩的搭讪打断了陈致善的思绪。
陈致善递过打火机,手上的烟已经快抽完了。两三个年轻女生,画着极深的烟熏妆,戴着浓密的假睫毛,望过去,双眼只看得到两个黑洞。应该也只有十七八岁的年纪,穿着深V领的连衣裙,露出健康修长的大腿。她们娴熟地抽着烟,其中一个在和人打电话,用失去耐心的声音催促正在前来的同伴。
陈致善在垃圾桶边将烟头掐灭,转身离开。计程车驶离兰桂坊,十五分钟后停在半山的一个高档公寓门口。
这是他父亲的物业。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在这个弹丸之地,已经可以被称作豪宅。倒是环境清幽,在海拔高出几百米的地方,与海平面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楼房俨然两个世界。在他搬进来之前,他父亲偶尔来香港出差,照看这边的业务,也会住在这里。但是自从他入住之后,他父亲就不再来过,只是象征性地留了一个房间,剩下些零星的日常用品。他一个人住,生活简单,也没有请任何帮佣。
他开了门入屋,打开灯,缸里一群热带鱼被这灯光和声响惊动,如离弦之箭般倏忽穿越。他走到鱼缸前,从一边的饲饵袋里倒出些许鱼饵,用手指碾碎了投入鱼缸。四散乱窜的鱼在静止片刻后,突然之间忘记了刚才惊慌乱窜的原因,开始纷纷围拢享受宵夜。
他站在鱼缸前静静地观赏。
这是他永远都不会感觉厌倦的一件事。每一次开门进屋,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在鱼缸前伫立几分钟。在这片刻,头脑一片空白,卸下一身防护铠甲回到毫无防备的柔软状态。就像高科技电影中,超人主角褪去身份符号的装扮,回到平凡肉身。
细微颗粒的鱼饵如雪片般在水中缓缓下沉,突然之间就有鱼从某一个方位窜过来,一张嘴将鱼饵吞噬。这一缸的鱼,构成一个小小的海底世界。他选了一些性情温和,同是慈鲷科的鱼放在一起养。他初时不了解这些鱼类科目,只是听从了水族店老板的建议,搭配了几款王子、阿里和鹦鹉。这些名字如此趣致,不禁让人联想到服装鲜艳、载歌载舞的东南亚裔男子。
他在网络上搜索这几种鱼的属性,发现同属慈鲷科。慈鲷科属底栖鱼类,原产于中南美洲、非洲及西印度群岛,现已遍布全球热带与亚热带地区。大多为卵生口孵,有部分系在巢穴底床孵卵而由亲鱼共同护卫,亦有孵化后将仔鱼含在口中保护者。因为有严密的护幼行为,所以被称为“慈鲷”。他仔细阅读着维基百科对于慈鲷科的解释,感动于这种鱼类的情义。
虽然是同科,但这几款鱼的性格迥然。阿里体形最大,通体呈粉红色,总是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王子全身泛着金黄色光泽,背鳍、腹鳍边缘有一条黑色边,的确如同气宇轩昂的王子,只是性格略微有些霸道。鹦鹉的体形最小,敏感胆小,经常躲在水族箱的山石后面,或者水草旁边。每次与其他鱼狭路相逢,鹦鹉就会迅速退回自己的安全范围。虽然水族店老板保证鹦鹉就算饿一点也不会有事,反而吃太饱容易生病。陈致善对于弱者还是有种本能的保护心理,总是担心它们被大鱼抢走所有食物,所以每次都会帮忙驱赶,或是趁着它们正好游出来的片刻,即刻投放些许鱼饵,如同父母偏爱某一个小孩,偷偷塞些零食般。
水族箱里的热带鱼还在开心地享用宵夜。陈致善到厨房拿了一支冰啤酒,在沙发上坐下。房间里安静得只能听到水族箱氧气泵在水中冒泡的咕咕声。他住的这套公寓,中规中矩的装修风格,木地板,白色墙壁,客厅宽敞。两间卧室都不算大,但还能各自摆下衣柜书桌。虽然家具电器,各式用料都是高档货色,却难以掩盖当初设计装修时想要用钱草草打发的某种敷衍了事。除了客厅里摆放的水族箱和那几尾色彩斑斓的热带鱼,再无细节之处。他一个人住,东西收拾得非常整齐,每一样物品似乎都正确排列在自己应有的位置上。
他喝了一口啤酒,冰啤酒顺着喉咙滑落,冰凉刺激的感觉沿着肠胃一路向下,似乎可以想象那如同田野灌溉流过沟渠的水流在体内的移动轨迹。他从未曾有相亲经历,但和苏锦深的这场相亲安排,似乎与陈致善认知的相亲场面相去甚远。想起来,这顿晚餐的两三个小时里,他们的对话未涉及任何实质性的内容,没有谈及彼此的工作、收入、家庭。他不知道为何她会来到这座城市,亦不知她是否会继续停留。
这本来只是一场盛情难却下勉为其难的相亲,任务完成即可散场,即使在这个人口密集、空间狭小的城市再次遇到,也不过只是茫茫人海中的一张熟面孔。这是陈致善一开始的计划。苏锦深的出现是计划外的事情,如同一道光,撕裂陈致善撑起的温和沉闷的保护伞,投射进来,将他先前心中的计划照得无所遁形。他一度差点忘记两人坐在那个包间里吃晚餐的初衷。
他有些无措,又隐隐有一些欣喜和不知从何而来的小小期盼。在这个千万人口的城市,跨越了几千公里,隔了十几年,他们竟被命运安排在婚姻的边缘。
婚姻,他想到这个词的时候自己也吓了一跳。瞬间有千钧之力压下来,将原有的那些零星欣喜碾得粉碎。所有他经历过的关系莫不动荡脆弱。平常生活里的稳定和谐,如镜花水月,可望不可即。他从不奢望正统社会定义下的关系架构可以实现在自己身上,比如婚姻、家庭。这些词汇都太美好,也太沉实。稳固结构下的个体如若没有同等的稳定性,就会如困兽般互相厮杀伤害。而原先借以维持稳固的架构,也就变成了困住彼此的牢笼。
他一度迷恋寻常巷陌里的烟火气。透过窗户看到灯光下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有时是热闹的说笑,有时各自木然,默默如无声电影,流淌的都是落到实地的生活。
而一直以来他所渴求的,不过是有机会在边缘处扒着门缝朝里望几眼,让漏出的微光照耀一下。
他关上灯,将冷气机开到最大,蜷进被子里。这无边无际的夜似乎可以把一切溶解。白天总让他感觉疲于奔命,再简单的人际交往也是捉襟见肘。他只想快点睡去,结束这冰冷严酷的白昼。梦是他唯一可以期待的。恐怖的,诡异的,光怪陆离的,或是温馨的。没有人可以左右或是控制他的梦。这是他的私密空间,如同打开一个未知世界的门,充满惊喜,无论好坏,独自承担。但总可以全身而退从头再来。
他经常做同一个梦,因为出现得太频繁,以至于有点搞不清楚,这究竟是梦境,还是真实的记忆。他似乎只有四岁。那一天是他的生日。他父亲骑了一辆脚踏车,穿过大半个上海带他去公园。他母亲也去了。他坐在自行车前排的小板凳上,是特意安放在横杠上的自制木板凳,他的母亲坐在后座。他只记得耳边呼呼的风,还有迎面而来应接不暇的五光十色。
“致善帮我按铃哦。”每到路口或者热闹的地方,父亲就会让致善把自行车的铃按响。
丁零零,丁零零。致善爱极了这个任务,如同有魔力的号角般,前方的行人车辆都自觉避让。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像一个高高在上的君王。
他们一家人围坐在公园的草地上,明媚阳光照射出父母年轻漂亮的脸庞剪影。父亲身材修长,手臂强健有力,可以轻易将他高高举起。那是一张轮廓分明的脸,两鬓是青色的发根。与后来那个身材走样、神情严肃、头发灰白的中年男人似乎不是同一个人了。他从未在梦中看清过母亲的脸,都是些支离破碎的细节。风吹过她的长发,空气中飘过淡淡的花露水的香味。小碎花的长裙,尼龙短袜,高跟的塑料凉鞋,脚踝上的凉鞋细带。她温柔地给他擦去脸上的汗水,用一条小格子的手绢,叠得四四方方干净的手绢,可以闻到肥皂的清新气味。
暖色调的公园和年轻的父母,琐碎的若即若离的温情片断。真实似触手可及。
公园小径铺满了鹅卵石,椭圆形的青色石头,走在上面可以感觉到阳光的温度。她牵着他的手带他去看鱼。人工湖里几条硕大的锦鲤成群游动。他伸手去摸,鱼群涌过来,色彩斑斓,阳光照在湖面上,亮晃晃的,让人几乎无法直视。手指慢慢伸进水里,清凉柔软的感觉。光线在水中折射出奇怪的角度,如同在一个装满镜子的世界,映射出各种比例失调却又炫目的景象。他伸手去摸触手可及的鱼,每次却只能抓住一些光与影的碎片,抬起手,只是湿漉漉的水。
“致善,还差一点就可以了。”父亲在身后鼓励他。
母亲还在温柔地给他擦汗。他坐在父亲高大的阴影里,更加努力地去试图触摸,却始终无法成功。焦灼的感觉愈发强烈,直至醒来。每次梦醒的那一刻,睁眼看到天花板,眼睛似乎还没有从阳光下水面的闪耀中回复过来。他有点懊悔,一半是梦中残留的情绪,一半是埋怨自己为何要把梦弄醒。
夜长多梦。
继续睡去,却回不到原来的梦境。转眼间,孤身一人置身于荒原,天空混沌不堪,周遭的一切昏黄暗哑。风很大,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吹来,每迈出一步都需要极大的气力。他想要离开这里,可是无论往哪里走,都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他感觉疲乏至极,想要坐下稍事休息,转身却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公园。
天气依然很差。有几个成年人坐在跷跷板的座椅上,用力地玩耍。跷跷板中间的支点处是一只面目狰狞的黑熊模型。旋转盘的扶手因为生锈已经摇摇晃晃,随着转动发出沉闷的金属撞击的声音。
他走到湖边,在浑浊的湖水里看到一张成年男人的脸。再一看,却看到湖面上漂着许多死鱼,肚皮朝上,灰白的眼珠突出。不远处的湖中心,有几只天鹅形状的脚踏船。年轻情侣,带着年幼孩子的小夫妻,坐在船上游湖。船只在漂着死鱼的湖面上行进,儿童欢快地把手伸入湖中戏水。他猛然间发现自己变成了坐在船上戏水的儿童,急忙把手收回,手上已沾染了死鱼的腥气和尸体的腐朽气息。
船上突然间只剩下他一个人,旁边的几条小船上的年轻情侣和游人早已不见踪影,只剩下锈迹斑斑的天鹅船漂在湖面上。天阴沉沉的,乌云厚重得似乎快要跌下来,大雨将至。他看到不远处岸边有一间明亮的办公室,电脑屏幕后面坐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正在专注地对着电脑工作,他认出来,那是他的父亲!他大声呼喊他,一张嘴,声音瞬间被周围的风吞噬,无论多用力,都无法发出一点声音。他朝他挥手,企图获得他的注意。他看到他父亲从座位上起了身,转身温柔抱起一个小男孩,消失在一水之隔的光线里。
大雨倾盆而至,雨点打在水面上,掀动浮在水面上的死鱼。天鹅船随着水浪颠簸。他站在摇摇晃晃的船里,浑身湿透。雨水打在他的脸上,让他几乎看不清周遭的一切,只感觉到脸上冰凉的水。
他又回到了空旷萧瑟的荒原。雨还在下。荒烟蔓草之上,突然出现一个女童,帮他撑起一把伞,转身离开。
他想要看清她的脸,伸手去抓女童的手,蓦然惊醒。脸上冰凉的水还在,竟是自己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