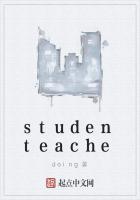大理连下三日霖雨,气温乍然转凉,观月轩里花飞叶落,塘前的枫林一片金黄,映得满庭都是瑟瑟秋意。
这当口,琬玉夜立中宵染了风寒,初时尚不以为意,只当是小恙无碍。喜鹊让曲大娘熬了两碗姜汤,伺候着热热地喝下去,想着发一身汗便好了。隔了两日,琬玉病情不见好转,反是身子沉重,夜里不停咳喘起来,到了第二日竟然连床都起不来了,急得喜鹊连连跺脚,直说自己大意了,悔不该让小姐冒雨去塘边赏叶。
曾府如今重重布防,采买物品都只能送至府门,外人不得无故进入,郎中也不如往日传唤方便。姑爷忙得抽不开身,便令喜鹊拿了腰牌出府,请回一个老郎中瞧病。诊脉后,老先生说琬玉是“寒暑不均,伤及肺气”,加之小姐先天不足,底气嬴弱,这病非三两日能荃逾,需要卧床静养调息,用汤药慢慢去除病根。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琬玉这一病就是十来天,除了最初到清风楼看过二少爷一回,大部分时日都在卧床昏睡,整个人清减了不少。老郎中隔个三两日进府换一次药方,可是小姐的病反反复复,刚刚有些儿好转,第二日又加重了咳喘,把个喜鹊愁得不行。
为怕姑爷沾惹病气,琬玉已搬到楼下耳房独住,小屋里药气弥漫,光线也不如楼上明亮,更加显得气氛阴郁。这场病好象把小姐的精气神抽走了,清醒的时候也是恹恹的,没有什么说话的兴致,只是对着窗外的茶树发呆。
这天日头好,一早阳光洒满了庭院,喜鹊强拉着琬玉出房走动,在后院花圃中小坐了片刻,又说了会话。小姐今天精神不错,晒了个多时辰太阳,两颊沁出些微红晕,午饭时一气喝下两碗清粥,竟有大好的趋势。喜鹊心里轻快,趁着琬玉午睡,嘱咐苗苗在门口伺候,自己去后院取些润肺的食材,小姐原先的梨膏丸快吃完了,得新制几十丸备着。
火房的院坝里,十来个下人正把墨砚围在当中,七嘴八舌地论说什么。午后下人闲暇,手里也没有什么活计,恰逢天气又好,下人们都聚在一起晒太阳谈八卦,连看守宗祠的陈聋子也在其中,还有喜鹊最不待见的瑞香丫头。
陈三娘原先在观月轩当差,和喜鹊很是熟络,让出半边板凳示意她坐,一边问:“二小姐的身子可好些了?”喜鹊苦笑着答说:“略好些,就是精神头还没完全醒转呢。”旁边的鲁嫂递了一把瓜子过来,附和着怨叹:“二小姐这场病生得太不是时候,天天闷在屋里,错过了多少热闹呢,连公主都没见着几面吧?”
“可不,天要下雨人要生病,那也是没法子的事!”喜鹊叹口气,挨着陈三娘坐下来。
坐定后,那头的瑞香满面堆笑,湊过身子问她:“喜鹊,你说二少爷会不会去当缅甸女婿啊?”喜鹊白她一眼,没好气地说:“这我哪知道,我又没长着水晶心肝,昨个晓得主子的心思!”暗忖瑞香今天有点反常啊,竟然碘着脸主动来搭话,不知肚子里卖的什么药。
喜鹊嗑着瓜子听了半晌,原来大家在争说二少爷和七公主的事。下人们意见不一,自觉划作两派:年轻的认为公主富贵多情,二少爷宏运当头,既有江山又有美人,早迟会去缅甸当王族女婿;年老的则不以为然,缅甸再好,终是异邦,二少爷坐拥百万家财,大理的名门闰秀争相入嫁,犯不着千里迢迢去倒插门!喜鹊听得很不是滋味,破天荒的没有参与评说,睁大眼睛专心听着。
老少两派争执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说。末了,刘大麻子粗声粗气地问墨砚:“墨砚你说,二少爷对七公主好些,还是对木兰好些?”墨砚成日在少爷跟前,最是知道情形,说话当然有份量,一时众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他身上。墨砚既得意又为难,小圆脸儿皱成一团,想了一会答说:“要我瞧,二少爷对她俩都挺好的!”
“怎么个好法?总得有些分别吧!”刘大麻子急吼吼地追问。墨砚搔着头说:“二少爷的吃饭洗漱都由木兰伺候,从早到晚都离不开她,每日上下午还要教木兰弹琴。但是两人说话少,一个弹,一个听,屋里静悄悄的。七公主嘛,性子比木兰活泼,每天都要过来跟着少爷学汉话,总是兴兴头头的,一呆就是一下午,有时还唱歌跳舞,少爷脸上也是笑嘻嘻的,和她说的话儿也多些。”
从墨砚的描述来看,的确有些难分伯仲。喜鹊有心回护,不以为然地接口道:“嗨,少爷见了谁不是有说有笑?对七公主笑嘻嘻的那是礼节!再说,咱们这个主子的性情,大家都晓得,院里就算来个挑大粪的,他都能跟人拉扯两句。”众人哄笑一声,都认为喜鹊说的是实话,二少爷跟谁都不摆架子,最招下人待见。而且从小喜欢捣鼓,院里院外的花匠呀木工呀都混得厮熟。
鲁嫂挑着眉梢问墨砚:“七公主看见二少爷床边有人,还是个俊俏丫鬟,就不问一声儿,也没摔脸子什么的?”她故意把‘床边’两个字尾音拖得极长,便有下人挤眉弄眼地笑。
这两天,木兰为了照顾方便,晚上就睡在书房的贵妃榻,和二少爷仅隔了一张屏风,确实也称得上睡在‘床边’。孤男寡女,长夜独处,难免让人浮想连翩。有那心思龌龊的想得深了,七公主这朵带刺玫瑰碰不得,木兰却是枕边娇花任由爱怜。二少爷正值血气方刚,虽说腿上有伤,可又没伤着要害,保不准早就被翻红浪,夜夜缱绻不休,享尽了齐人之福!
喜鹊一直担心七公主对木兰不好,竖起耳朵听墨砚怎么答。说到惴摩心思,墨砚就不擅长了,歪头想了半天说:“我瞧公主对木兰笑眯眯的,还赏了她很多东西,看起来没啥不高兴。”
鲁嫂吐了一片瓜子皮儿,表情有些儿不屑:“卧榻之侧,岂容她人安睡!恐怕公主的笑也是装出来的。墨砚你还小,不懂里头的名堂。”
喜鹊忍不住苦着脸儿叹说:“就怕公主是个笑面虎,木兰心善,早晚要吃亏!”陈三娘在观月轩呆得久,也为木兰回护,忿忿地打抱不平说:“凭什么二少爷就不能有丫鬟伺候?七公主她不也带着个黑大个子吗?那黑奴壮实得像头水牛,成日跟前跟后的,让人看了都燥得慌。瑞香,你说是不是?”
瑞香嗤笑一声,显得万分窝火:“可不是嘛,公主的吃穿用度,梳洗打扮,万事都由那阿布经手,我连公主的身子都靠不拢。”扁着嘴又道:“说来你们不信,阿布晚上就睡在公主门外,一步都不带离开。明明有屋也不去住,怕我半夜进去吃了公主呢!”
怪不得瑞香要对喜鹊示好,原来是对公主满腹牢骚。这瑞香原是淑玉阁的丫鬟,从小在二夫人跟前当差,手脚也称得上伶俐,可惜上头有红姑压着,一直升不上大丫鬟的份位。这回得了机会,原想好好儿展现能干,把公主伺候得妥妥贴贴,到时为她美言几句,让二夫人眼里看得见自己。可惜她到了宜香院,事事插不上手,做的都是些粗笨活计,跑腿的时候比呆在院里还多,自然满心委屈,心里着实窝火。
“你们晓得不,阿布在缅语里是孤儿的意思!黑奴的爹是天竺游僧,得了重病死在大衮,黑奴就变成了小叫化子。”墨砚一脸神秘,眼睛睁着溜圆:
“我听人说,公主出宫时捡到了阿布,带回宫里养着,还请来师傅教他功夫。阿布的拳脚可历害了,这回在澜苍江打跑了十几个山贼,连我爹都佩服他,所以七公主的娘才选他来保护公主。。”
“怪道不得,瞧瞧那身肌肉疙瘩,简直就是个野牛犊子!”刘大麻子匝着嘴说,很有些羡慕的味道。陈聋子抽着水烟瞅了他一眼:“老哥,你要是长成那样,老嫂子还要多下几个娃崽,到时让你养都养不起!”男人们发出会意的哄笑。刘大麻子嘿嘿笑着,转了话头问瑞香:“黑大个子说话你能听得懂不?”墨砚抢着答说:“听得懂,阿布会说汉话,是跟他的和尚老爹学的。”瑞香也点头补了一句:“听是听得懂,就是怪里怪气的,好象八哥学人话。”便有两个促狭的后生,笑嚷着让瑞香学两句来听。
“你们几个嚼舌根也不怕烂了嘴!七公主岂是你们随便说笑的?”哄闹之际,耳边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不知何时,红姑走进来听了半天,冷着脸阴森森地说:“这些话万一传到了府外头,就算二夫人不动用家法,段都督也要治你们诋毁公主的大罪!”众人吓得一个寒噤,想到府门口威仪赫赫的巡守甲士,都是背心嗖嗖发凉,赶紧散开各人做事去了。
墨砚暗叫一声不好,正想沿墙边悄悄溜走,被红姑厉声喝住:“小兔崽子,再不管好你的嘴,让你老子把你吊起来打!”
“红姑奶奶饶命,小的再也不敢了!”墨砚吓得连声讨饶,红姑喝斥他两句,把手里的一包东西递给他:“这是徐嬷嬷要的药材,赶紧拿回去,丢了一样小心你的皮!”墨砚如释大负地一溜烟走了。
喜鹊赶紧从厨房拿了东西,一路小跑,在大槐树前追上墨砚,托他给木兰带句话,让木兰得了空回来瞅瞅小姐。墨砚脆生生应了,喜鹊掏了十个几铜子赏他,又问了些二少爷的近况,方各自走了。
隔日,木兰抽空回来探病,恰逢段奕也在,木兰只得先和他请安说话。姑爷待木兰一如既往地温和,先问她在清风楼可习惯,又问曾振南的腿伤如何。姑爷问一句,木兰便答一句,始终低着头,微露一截粉白的脖颈,态度比原先还要恭谨。好在姑爷识趣,几句客气话说完,便让喜鹊带她去看小姐,自个院中练剑,留下主仆独处叙话。
一进房间,木兰看见琬玉歪在床上,双颊潮红,形容憔悴,一副柔弱可怜的模样。木兰心里一酸,坐在床边替她掖整鬓发,怨说:“怎么不早点请郎中,瞧瞧,小姐都瘦得脱形了!”
木兰越说越心痛,琬玉虚弱一笑,反安慰她道:“不妨事,昨儿郎中又来换了方子,说这病已经到尾声,再吃两剂药就大愈了。对了,南哥哥腿可好些了?”“好多了!雪婵的疗效就是神奇,少爷都能拄着拐勉强走两步了,不过得养些时日才能下地。”
琬玉眸子一亮,顿露宽慰之色,两颊的潮红更甚。
木兰看在眼里,心里着实怜惜:“你们俩呀,真个是互相掂记!二少爷这些天可憋坏了,常在二夫人面前吵闹着要下地来看你呢。”琬玉又是凄婉一笑:“南哥哥做事率性,
不然也招不来七公主了!”木兰暗忖,你得的乃是心病,寻常汤药怎么治得好?
琬玉拉着她的手,仔细端详一番,忧心仲仲地问:“我怎么觉得你清减了些?可是太累了?”木兰知道她话里所指,在她手背上轻拍了两下,
“放心,大家都对我极好,七公主还赏了我好些物件,改日得了空拿给你看。”见琬玉似有不信,又笑说:“我成日好吃好睡,白天只管弹琴与少爷解闷,活计轻省,比在观月轩还轻松呢。”说着把双手递到琬玉跟前:“瞧瞧,久不做事,连手儿都养得细嫩了!徐嬷嬷又见天的做鱼做肉,害我猛长身量,所以你才觉得我瘦了。”
面前木兰玉立亭亭,唇红眉黛,确实没有受苦的迹象,琬玉犹自追问:“听说公主天天都来,真的没有为难你吗?”“小姐一百个放心吧,真的没有!”
木兰神色轻松地笑答:“我和公主河水不犯井水,她来了我就主动避让。再说,二少爷得了吩咐,公主在时绝不使唤我,免得落下口实自找烦恼。”琬玉略松一口气,摇头道:“难得二哥也开窍了,总算学会了两全之策。对了,你成日练筝辛苦吗?南哥哥是个音痴,练起琴可是没完没了!”
这倒是事实,自打二少爷知道了木兰学琴一事,惊喜交加,当即让墨砚去芳春庭取了古筝回来,倚床指点木兰习练,乐此不疲。木兰身怀苦学琵琶的精湛功底,只能处处克制,成日装愚好不辛苦,绕是如此,进度也胜常人几倍,曾振南已经屡次大赞她“悟性天赋,万中无一!”
两人又说了一刻闲话,木兰不敢久坐,恋恋不舍地起身告辞。没法子,清风楼来往人多,二少爷又一刻离不开她,这还是趁着少爷午睡的当儿溜出来的,再呆下去红姑该挑刺了。为怕木兰过了病气,琬玉支使喜鹊去取一匣梨膏丸来,说这是新做的膏丸,药性极好,常吃可以清风润肺。木兰自然领会其中深意,两人借拉手作别之机,不着痕迹地互递了一件物是。临出门,木兰照礼节辞谢了姑爷,苗苗一直把她送到大门,木兰又好好劝慰了小丫头一番。
出了观月轩的大牌楼,木兰紧绷的神经稍稍松懈,她打开紧攥的手心,手掌中,赫然多了一枚玉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