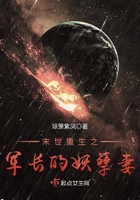我对米最完整的版本记忆,源于一个水碓房。水碓房位于村后的涧溪边,低矮,窗户阔亮。涧水引到蓄水槽,闸门一放,水“哗哗哗”地泻到轱辘上。轱辘有三米高,是厚实的松木制的,转动起来,会有“咿咿呀呀”的响声,像一支古老的歌谣。轱辘的轮叶,“呼哒呼哒”地打在舂米的吊头上。舂槽是花岗岩挖出的凹穴,而吊头是圆而粗的杉木柱,米倒在凹穴里,吊头很有节奏地舂下来,一下一下。枫林人说,舂米就像媾和。吊头有四个,不用的时候,各用麻绳吊在梁上,像一群马,整装待发。水碓房到处是糠灰,还悬着透明的蜘蛛网,麻雀“扑棱棱”地飞来飞去,“嘻嘻”地叫,犹如一群偷吃的孩子。晒透了的谷,倒进凹穴,慢慢地碎,再倒到风车里吹,一箩是米,一箩是糠。守房的,是一个老头,有六十多岁,个子高高大大,常年吃斋,脸色是米瓜的那种蜡黄。他像个禅房的老僧,头秃光了毛,手里拿着芦苇扫把,一遍一遍地扫地上的糠灰。舂一担米,给他一升。他是个孤寡的人,我也不知道他老婆死于哪一年。他有一个儿子,叫春发,还没结婚就死了。春发和一个叫幼林的人打赌,他说他能吃三升米的糯米馃,幼林不信,幼林说,你吃得下,我出三升糯米,再出三升,给你带回家。打赌的那天晚上,幼林家围满了人。打馃的人趁人不在,吃了两个,有人碰见,说,烂是烂了,好糯米,就是糖少了些。春发吃完了糯米馃,被人抬着回家,那天晚上就死了。村里人说,春发好福气,是撑死的,来世不会做饿汉。后来村里通了电,机器取代了水碓,春发的父亲到山庙里做了烧锅僧。水碓房推了,垦出两分田。我年少时,经常去水碓房玩,把牛放到山上,就帮老头种菜。不是我多么乐于敬老,而是老头会炒一碗饭,给我当点心。坐在菜地的矮墙上,稀里哗啦,一碗饭没了,我把他的菜汤也喝完。他有时会摸摸我的头,不说话。我觉得他像饭一样慈爱。
村里有一个杀猪佬,一年到头杀不了几头猪,不是他技术差或品德有问题,而是能吃得上肉的人没几户,要吃,就从盐缸里切一块咸肉,炖炖菜。杀猪佬矮矮瘦瘦,爱喝酒,一喝酒就流鼻涕,一副想哭的样子。她老婆也矮,挑粪萁拖着地。她有一群儿女,两年一个。杀猪佬又做不来农事,更干不了重活,吃米饭也成了问题。有一天晚上,在杀猪佬的柴垛里,一个赌博回家的人,捉到一对男女光着身子野合。男的是一个癞痢头,老单身,女的是杀猪佬的老婆。第二天,村里都流传了这个事。事情就是这样,坛子里的烟雾一旦打开,便散得到处都是。这个干辣椒一样的女人,只要有男人找她,她都要,在菜地,在岩石洞,在油茶树下,在河埠。杀猪佬打了她几次,用刀柄抽。抽也没用。她裸露着脊背上的伤口,坐在门槛上,给路过的人看。同情的人,用猪油给她搽搽,她会抱住别人,说:“我又不是天生淫荡的女人,我又没犯法,为什么要这样打我?我和男人相好一次,就收一斗米。我没办法,孩子饿不住啊。”他就不再打了,当着什么也没发生。他喝醉了,逢人就说:“我的矮×是个粮仓。”
很多时候,我是这样理解的,一个热爱大米的人,必然是一个便感恩生活的人。我回枫林老家,一年难得几次,母亲忙这忙那地为我烧一桌子的好菜。我过意不去,我对母亲说,我回家就是想吃饭甑蒸的饭。我说得也是实话,我想象不出还有比这个更好吃的东西。饭甑是杉木板箍的,上大下小,圆圆的往下收缩,打开盖子,蒸汽腾腾地往上翻涌。饭香袅袅,滚滚而来。米完全蒸开,雪一样白,相亲相爱的兄弟一样紧紧地环抱在一起,仿佛它们曾经受了无穷的苦难,如今要好好地享受血肉亲情。这样的记忆也相随我一生—母亲把一天吃的米,倒在一个竹萁里,放进清水,使劲地晃动,米灰慢慢地在水中漾开,米白白的,圆润,晶晶亮亮。锅里的水已经沸沸地冒泡,蒸汽一圈一圈地缠绕在房梁上。母亲把洗好的米倾进锅里,盖上盖子,旺旺的木材火熊熊地煮。锅里的清水变白、变稀、变浓,胶一样,母亲把米捞上来,晾在竹萁上,到了中午,用饭甑蒸,成了生香的米饭。剩下的羹水切两个大红薯下去,煮烂,我们吃得稀里哗啦。
米饭不软不硬,酥酥绵绵,细细嚼,有淡淡的甜味,不用菜也可以吃上三大碗。小时候,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建一个大谷仓,里面堆满了稻谷,怎么吃也吃不完。然而,美好的生活似乎并不需要谷仓。我现在的家里,一个20斤的铁皮米桶,可以应付一个月。没有米,打一个电话给楼下的超市,他就五分钟送到。
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说,一个没有看见米生长的人,是没有家园意识的。一个有家园意识的人,当他再也看不见米的生长,他的内心是恐慌的。
现在,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生活都变好了,米成了贱货,一百斤米换不到半只鞋,讨饭的人也不要米,嫌背在身上重。人种田是受苦,米出来了又遭罪。有些减肥的女人,不吃饭,只吃水果,或药丸。我爱人的一个同学,差不多有一年没有吃米饭啦。她有些胖,怕有钱的老公嫌弃她,她只吃水果,她觉得米是她不可原谅的敌人。她嫌弃米,米成了原罪。
米假如有人一样的心脏,必然是一颗痛苦的心脏。它有两种颜色的肌肤,一种是红色,一种是黑色。红的是热血,黑的是伤病。然而,米呈现给我们的,是珍珠一样的皎洁,让我们忍不住伸出双手,捧着它,久久不放。
废墟上的远方
所谓远方,并不是地图上的两个点,因为所有可以通达的地方并不遥远。你知道左心房到右心房有多远吗?从手心到手背有多远吗?从左眼到右眼有多远吗?也许远方只是一个悬念,一个没有谜底的谜,一个未知,一个移动的旋涡。它是黑暗的(被某种景象所遮蔽,像抽屉里字迹发黄的日记),萦绕的(一个让你怀念的人,会情不自禁涌入你脑海),灼热的(不是扩散而是聚集的痛,在皮肤上慢慢燃烧)。这样说,似乎有些矫情,但1996年以后,我相信这个说法—我有些偏执,经常按照自己从生活中得到的“真理”,去观照身边的情景与人事。
从你家到W医院,直线距离约十公里,坐直达车不要二十分钟。1996年的市区到郊区,还没开通直达车。在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有时是星期四的晚上,你会去W医院,探望你二弟。你坐车的路线是这样的:坐八路车到交通大厦,转十一路车到三江大市场,再坐上饶县1路车到W镇,步行十七分钟的泥浆路到W医院。线路由两个“N”字组成,像盘结的肠道—我当时确实无法剖解“线路”给我的谕示,生活无非是两种方式: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W镇真远,来回就要三个小时。”你抱怨说。“倒是不远,但确实让人疲惫”,我说,“事情很快就会过去,人和生活一样,不是一成不变。”晚上去W镇,则要十六元租用港田车。港田车是一种三轮摩托改装的,有焊铁的雨棚,污浊的布帘。它奔跑的时候,一跳一跳,屁股(排气管)冒浓烈的黑烟。坐在车上,我会想起古代私奔的马车。
W医院在W镇的东面,比邻河流。医院的院子里耸立着女贞树和白桦,尖嘴鸟、红嘴鸟、灰山雀,“叽叽喳喳“地跳来跳去,显得院子更加空落和寂寥。围墙刷了一层石灰水,楼墙嵌了瓷面砖,惨白的光好像不是反射而来的,而是从物体的内部激射而出,刺骨的寒冷。我没有见过比它更安静的医院—病人睡着了一般,医护人员不是看书打瞌睡,就是对着取暖器发呆。而千米外的街上,一片喧哗,有人打架,有人吆喝,有人搬一张桌子在街边打麻将,自行车后架放一把泥刀的正准备去市里做短工,从车上拎下几麻袋货物的是商贩。另一家在街中心位置的医院,挤满了各色人等。“我小孩已经发烧两天了,会不会有肺炎?”“真是祸从天降!喝醉了酒的司机把大货车开进了我家里,把我老头子的腿都撞断了。”“这是什么医院啊?简直是屠宰场,看一次感冒花了一千多块。”
“这是一个被遗忘的地方。”我对你说。“不。它像个火炉,会把一个人重新燃烧起来。”你说,“你看到的是火炉里的灰烬。”
W镇是上饶县南乡小镇。上饶县以320国道为中轴线,分南乡和北乡。在地理上,南乡像一个子宫,W镇就是宫颈。三月,南方的雨水还没有到来,村野里,泡桐花就迫不及待地宽衣解带。W镇,南方以南的W镇。它有着南方的柔软和明亮,大片的松林和遍地的葱茏菜蔬,是大地的斑纹。酒香被风从酒厂压过来,渐渐与柚子树、山茶树、木槿的气息融为一体,悬浮在空气中,变成小镇馥荔的体香。它那么疏朗,多年以后,被一个人带走,永不复返。
第一次看到你二弟是1995年冬的一个夜晚。你对我说,二弟放假了,我们一起聚聚餐吧。餐馆是解放路的旺旺美食广场。聚餐的还有你的大弟弟,以及他女朋友。我们边吃边聊,一直聊到深夜一点。你二弟是个非常健谈的人,二十出头,脸上长满粉刺,但一脸忧郁。其实,之前我就从你的口中,对他有大概的了解。“你要对我姐姐好。”席间,你二弟反复对我说这句话。他不像个弟弟,反而像个年长者。他的成熟与他的年龄不相称。我无法回答这个话题—我既不是你的男朋友也不是你的未婚夫,而且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和你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听了他的话,哈起腰笑了起来,说:“傻弟弟,傻弟弟。”
我和你交往已经有两年了。我是通过我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的。之前,我就听说过你。你有一副好歌喉。你长得娇小瘦弱、短肩发、脸白皙圆润,有一口皎白的石榴牙。你爱梳洗睫毛,长长的,显得眼睛格外有神。
年后不久,我就听到了你二弟住进W医院的消息。我是从你一个老乡口中得知的。我非常惊诧。我想,可能我愚笨,看不出事物表象背后的东西—那两年,你每隔两个月,就要去千里之外看你二弟,我以为是你对二弟过渡的溺爱。
W镇,它作为一个阴影的代名词,占据了我。以前,我去过无数次W镇,尤其在春天,隔三差五就去看迷眼金黄的油菜花,就像观察一个女人的盛开与衰老。W镇,它以平坦的地貌化解了南方的阴郁,矮小的丘陵把江南的色泽勾画出层次。我第一次去W医院,是在晚上。街上朦胧的灯光,在细雨中,变得恍惚,加速了天空的下垂。天空像一个塑料袋,灌满了水。那年的雨季提前到来,让人喘不过气来。你二弟的病房在住院部二楼。夜晚就连呼啸也是寂静的,掩埋在灰尘里。
你出身于书香门第之家。你家住在郊区。从1995年到1997年,差不多每个星期我会去一次,要么送你回家,要么接你出来,一般是在晚上。通往你家的路,是一条颠簸的土路,只有八路车经过,没有路灯,每个月都有抢劫事件发生。
你家附近的空地长满了乳酸草和小柳树。我作为护花使者的终点站是你家的楼道口。我从没去过你家。我知道,那是一个我想熟悉却不可以熟悉的世界—它是你心灵的仓库。我听一个我尊敬的长者说,你父亲在1995年秋,得了什么病,行动不方便,你母亲也因此打击抱病。你从来就没有向我提起过。我看到的你是一个快乐的人。
“我们是非常默契的谈友。”你说。“谈友”,成了我们的身份。我知道有一个男人在追你,我认识他。他是我朋友的表哥,三十来岁,胖胖的,开了一家小工厂。他是你的老乡。他是一个极其善良的人,在那几年,他几乎每天去看望你父亲。有一次,我和你在影都看电影,与他不期而遇。我们都有点尴尬。
有时,我主动和你谈到了这个男人,我说,他是一个具备优秀品格的人,现在这种人已经不多了。“他是很好的人,可是我们没有语言。我努力地接受他,我发现我根本做不到。”你说。“可能我是一个障碍。”我说。更深入的交谈,只会让你陷入更深的泥淖,也就没有太多的意义。也许,障碍是彼此的。
偶尔,你也住在你工作的单身楼里。那是一栋古典的建筑,在一座小山上,鹅卵石砌的草间小径,迂回,穿过一个木质的亭子,一条在荷花池上曲折的回廊,就可以看见二层结构的木楼。你住在二楼靠右边的房间。从你的窗户远眺,市区尽收眼底,灯光迷蒙,信江潋滟。这样的高度和角度,都是让人产生遐想的—我想,我们的青春期无非如此。有一次,我去找你,你正在为全校的歌咏比赛作准备,教学生唱歌。我站在小径上,教室里的灯光斜斜地照过来。你的手里握着教鞭,面带甜美的微笑。我看了一个多小时,又回去了。我感到我的心里有一只兽,在号叫,在奔跑。兽是突然到来的,它的爪柔软而锋利。
河流两岸肥美的时候,夏天到来了。两岸像一把折扇,被葱绿的河水打开。你每次去W镇,都怀着很高的兴致,好像不是探望一个病人,而是与一个久别的朋友重逢。我记得有一次你对你二弟说:“假如你每天想见一个人,你就会很幸福。”其实,这句话是说给我听的。
2005年3月5日下午,我陪女儿骢骢在滨江路玩。这是一条带有休闲走廊的繁华街道。古老的步行桥通往水南街。我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桥栏杆上,久久地对着河水发呆。我也那样发呆过,我究竟于旋涡中水流是怎样咆哮的。我看着年轻人越过栏杆,飞身而下,重重地摔在水泥桥墩上,身子扭曲(像锄头挖断的蚯蚓),白色的浆液和血红的浆液从他身体喷射出来。他没有叫喊,也没有挣扎。他心里有一堵高墙,挡住了他的去路,他只有飞过去。不知怎么的,我突然想到了你。我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巴,怕口腔里的声音倾泻而出。
1997年秋,你二弟离开了W医院。一千公里的路途是否遥远?上饶到广州,正是这个距离,坐14点30分的火车,次日8点50分到达。我经常坐这趟火车远游,假如有一个异性(适合调情)陪伴,整个旅途是短暂而愉快的。把一千公里分成一百次的等距离走,会怎样呢?四千公里分成二百个等距离来回完成,又是怎样呢?从你家到W镇,刚好是这个来回的等距离。完成这四千公里的方式是公交车、港田、自行车、徒步。
直至今天,我也没有看过你的父母。我只在你的单身楼里,看过你的全家照。照片里的你还是扎个羊角辫,穿花格的连衣裙,你的父亲戴副黑边眼镜,瘦,个子高挑,有儒雅的气质。你母亲穿旗袍,圆脸,双眼里仍然有少女的单纯。我不知道你的父母现在是否还健在。
1997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更寒冷,冬雨绵绵。有一天,我还在睡懒觉,听到“当当当“的敲门声,我开门一看,是你。我的宿舍在书院路的一个山坳里,偏僻,地形复杂,你从没来过。我说,你怎么来啦。你说:“我想请你陪我外出旅游。”你的话让我惊讶。我们商量了许多条旅游线路,广州、昆明、庐山、苏州。你说:“去婺源吧。我只想失踪几天,就近吧。”那天,我抱了你,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天晚上,你给我打电话说:“我今天去你那里,显得有点荒唐。请原谅我,我不去旅游了。”我们通了两个多小时的电话,听起来你很伤感。你很少会这样。1996年夏天,你放弃调入广州某大学也没如此低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