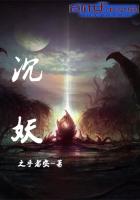而此刻,傅侯府里,青年正百无聊赖的把玩着手中的玉佩。
他神情散漫,露出一副极为享受的悠闲模样。陆怀安从外面走了进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先是与傅云琛说了一通。
后者撑颔似是漫不经心的听着,但若仔细看去,他目光竟是无比清明,哪有一丝懒散。
陆怀安也支着头,面色一正,“傅云琛,你可知晓姜鸿回朝了?”
傅云琛眼皮未眨,“哦。”
“姜鸿选择这个时候班师回朝,你不觉得别走企图吗?四皇子与五皇子岂会坐以待毙?谁若能将其招揽麾下,可是一大助力。”陆怀安摇头晃脑道:“毕竟,姜家可是唯一能与镇国大将军府抗衡的存在。”
他又像是想起了什么,“便是静安王府都蠢蠢欲动,静安王妃又举办劳什子宴会,听闻也向姜府递送了请帖。”
傅云琛把玩玉佩的手微顿,“静安王府?”
“可不是吗?我也收到了静安王府的帖子,大抵意思是邀请观赏花宴。但据我所知,受邀的都是青年才俊以及千金小姐,”陆怀安道:“静安王妃这哪里是赏花,分明是趁机挑人,给柔嘉郡主相看罢。”
“姜鸿的嫡长子姜衡也是一表人才,他若去了怕是能入柔嘉郡主的眼。”
傅云琛想了想,面上的笑意敛了几分,微眯着眼,拉长了声音,道:“姜家……呵。”
“怎么,你有什么想法?”陆怀安兴冲冲的问。
“如今姜鸿归来势必打乱镇国大将军府在朝中的格局,两府倒也是相互制衡。不会出现一府独大。永乐帝自然是乐见其成,两府斗的你死我活,方遂了他的心思。”他道:“永乐帝本就忌惮看似风平浪静不问世事的静安王,若是姜府被静安王府拉拢了去,那又该如何呢?”
“那陛下定当会想方设法永除后患!”陆怀安忙不迭接过一句,“不是有句话说的好,不会叫的狗咬人最是疼?陛下本就生性多疑,怕是早就派人监视着姜家,哪方与其走的近,只会招来陛下的猜疑与”他比划着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
“静安王妃设了一场好局,我岂能不看好戏的道理。”
陆怀安点头,“你最近倒是对静安王府的事越发上心了。”他眼中充满了八卦之色,揶揄道:“你同我说说,到底有什么目的。”
傅云琛睨了他一眼,“没什么,挡路的早些除掉便是。”
陆怀安自然不信只是因为这个原因,怕是傅云琛别有想法却不告诉他。
…………
静安王妃宴会那日,阮潋早早起来,采雪忙着给她梳妆打扮,阮潋素来不喜那些鲜艳颜色,偏爱素雅,采月便从衣柜里寻来浅紫色的衣裙,又挑了同色配饰。
待一切就绪后,采月便笑盈盈的道:“咱们小姐真好看。”满满的称赞不疑有假。
阮潋垂眸看着昏黄铜镜里印出一张清秀的面庞,虽算不得绝色佳人,倒也五官端正。她微微弯了弯唇,菱花镜里的少女也跟着弯了弯唇。
阮潋低低的笑了,其实她应当要感到满足的。上天垂怜赐她一次重来的机会,让她可以认清这些豺狼之辈的真面目,能阻止这场外祖父家的悲剧。
她朝窗外看去,院子里那些海棠花开的正好,似乎一切都是生机勃勃的模样。阮潋恍惚忆起上辈子这时候,她应当是躲在屋子里,闭门不出。
她被禁锢在这日复一日的悲哀中,难以自拔,沦为长安城的笑柄,被世人所不耻,遭亲人的鄙夷厌恶。
上辈子的阮潋是生活在算计中,被父亲当一颗棋子,被蒋姨娘母女当垫脚石。她被这些所谓的亲人榨干了最后一滴血,思及此,阮潋不知是该笑自己的愚蠢还是笑自己活的悲哀窝囊。
采雪仿佛察觉阮潋的失神,她小声道:“小姐却是在想什么?”
阮潋收回目光,淡淡道:“没什么。”
好在这些都是过去,这辈子她自然不会重蹈覆辙,那些欠她的,害她的,她都会十倍奉还。一个个的,都休想逃掉。
正说着,采月突然道:“小姐咱们院子里那海棠花开的真好。”
“是啊,”阮潋笑了笑,“真好。”
这回阮府的马车竟有两辆,便是阮玉不愿与阮潋同乘,殊不知这更是遂了阮潋的心意。她本就不欲与其周旋。
马车摇摇晃晃着前行,经过了闹市区,阮潋闭目养神,想着应该怎么应付静安王府可能会发生的事。突然听见前方嘈杂的人声,尔后她便听见马车夫惊慌的“吁”了一声。
可马匹并未因此停下蹄子,反而像是发了狂一般向前冲去,那马车夫见状,到底是性命重要,不假思索便翻下车辕,而没人驾驭的马匹更是脱了缰绳,完全失控。
马匹像无头苍蝇一般在并不是宽阔的街道上肆无忌惮的撂开蹄子极速乱窜着,街道旁好几个摊铺都因此遭殃,货物撒了一地不提,摊铺也被掀翻。
可马匹还在横冲直撞,采雪与马车夫急急忙忙的追赶着,但双腿哪能追赶上马匹的速度。
阮潋也被这强大的冲击力震的往后一倒,惯性因素,后脑勺磕在马车壁上。她揉着脑勺,本想再一次站起身却因马匹飞快的冲撞,再次跌坐在马车内动弹不得。
阮潋看向马车小窗口,那被疾风吹拂扬起的帘幕,她瞧见马匹正急速的奔跑着。她看到周边的商铺以及躲闪的百姓。
阮潋心下一紧,这马匹怕是受了惊,不要命的往前面奔跑着,若任由其横冲直撞,自己怕也有性命之忧。
阮潋抓紧了马车辕,掀开车帘,登时打消了要跳下马车的打算。且不论马车还在急速的飞驰着,跳下去非残即重伤,再者,她实在没把握敢跳下马车。
就在她思考之际,却瞧见马匹径直要撞上前方一个较大的摊铺,阮潋倒吸了一口冷气。
就在马匹即将要撞上前方的摊铺时,一炳剑准确无比从马车的车轱辘的空隙间穿过,卡在地面的青砖缝隙中,牢牢的将车轱辘固定住。
阮潋惊魂未定,她因马匹痛苦的嘶吼与挣扎又一次被惯性的摔在车厢里。
幸好,这是阮潋此刻唯一的想法,还好她还活着,危险总算是过去了。
阮潋揉着发疼的脑勺,模样十分狼狈,这时有人掀开了车帘,阮潋亦抬头看去,与来人对视。
那人身着一袭深紫色的锦袍,面若冷霜,五官坚毅,目光也冷厉的惊人。只是在瞧见阮潋那一刻,瞳孔微缩,露出了一分讶然。
阮潋自是没想那么多,不等她开口,男子已然直直道:“我救了你。”
阮潋微怔,随口便道:“如此,多谢公子仗义相救。”
采雪奔到马车旁,手脚并用的爬进车厢里,心急如焚的打量着阮潋,急的泪流不止,“小姐,您没事罢?方才可把奴婢吓坏了。”
说着目光一顿,瞧见阮潋原本白皙柔嫩的手背竟沁出了星点血丝,责备不已,“小姐,您的手背受伤了,都怪奴婢没用,没能拦住马匹。”
阮潋垂眸看了眼手背不过是擦破了点皮流了点血罢了,不是什么大事。也不会留疤,倒是把采雪吓得语无伦次,哭红了眼眶。
阮潋摇头,“我没事,不过是小伤。”
采雪抹了抹眼泪,扶着阮潋下了马车,那受惊的马匹还焦急难耐的踢着蹄子。而马车夫早就吓得六神无主跪在阮潋面前,求饶道:“二小姐饶命呐,奴才不是故意的,都是当时情况紧急啊。”
采雪“呸”了他一口,“情况紧急你就能弃马车自个去逃命。我告诉你,幸好今日咱们小姐平安无事,不然有了什么三长两短,你这条命都不够赔的。”
“是是是,采雪姑娘教训的是。都怪奴才鬼迷心窍,还望二小姐饶了我一命呐。”他眼中含着泪水,黝黑的脸上布满诚恳,“小姐,奴才家中上有八十老奴,下有妻女。奴才便是家中的顶梁柱啊!”
阮潋冷眼看他,眸光里划过一丝讥讽,她道:“这些事不必于我交代,回去一五一十回禀祖母与父亲即可。我的命便是这么轻贱了?今日的事,我必将追究到底。”
一直在旁的男子闻言微不可闻挑了挑眉,果真是她,方才他在去赴宴的路上看见丫鬟与马车夫急匆匆的追赶一辆失控的马车。
他本不想多管闲事,哪知无意瞧见那跑的上气不接下气的丫鬟,像极了那夜他在阮府看到的阮潋身侧侍奉的丫鬟。
果不其然,当他掀开车帘看去,露出一张清秀的面庞来,似是方逃脱惊险,少女的一脸迷瞪之色,那模样十足的讨喜。
马车夫心知犯了大错也不敢再多求饶。便面若死灰之色,垂头丧气的。
采雪道:“小姐,方才就是这位公子及时的救了您,避免了一场灾祸。”
顺着采雪所指,阮潋微微颔首,她瞧见男子沐浴在阳光下的容颜,论相貌不比傅云琛那般教人惊艳,但却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就好比那双丹凤眼,十足的勾人心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