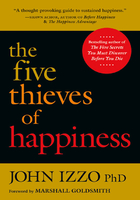生命
8月12日,我听到空难事故的消息。几天过去,却还未弄清事故的原因。这是一个悲惨的事件。
一位前往大阪机场迎接丈夫的妇女对记者说:“傍晚不到6点的时候,我丈夫给家里打来电话,告诉我他马上就要登机了,大约9点能到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难事故的详细情况日渐明朗。每从电视和报纸得知这方面的消息,我都感到难以言喻的痛苦。
面对如此巨大的惨事,在生孩子时所强烈感受到的对生命的信赖,此时变得那般脆弱和无力。
人们来到人世的时候,皆被赋予强大的生命力,而这样的生命却常常被包围在险恶之中,我们实则每天都徘徊在生死的边缘。
自从长子诞生后,我和丈夫之间的话题基本上是孩子。
有时,话题也会从孩子引申开去,但线索总是孩子又有哪些长进,他的动作如何、表情怎样。
“假使在我们的意识中占有重大比例的孩子有一天猝然消失呢?”连作这种假设,于我都过于沉重,我曾把这个念头告诉给丈夫。
“瞎说些什么?怪不吉利的。”丈夫付之一笑,这自然使我稍许感到慰藉。然而在现实里,就真有人在为此胆战心惊。每念及此,我就怀着虔诚的心情,为我孩子的健康而深感庆幸。
六七年前,我还在热恋中的时候,曾在舞台上对观众说过:“为了爱,我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
我知道我说这句话时很动情,而事实上,为了丈夫和孩子,我的确可以随时牺牲自己的性命。
正因为我爱他们,我才惧怕他们死去,也惧怕自己死去。
关于“死”的这两种复杂的感情,在令人惜别的夏季里悠荡着。
神落在尘世的眼泪
寂静的街头,地上树和楼的影子沉默相依。昏黄的街灯像一盏橙色的酒,在路上流淌。
她站在灯火深处,残了妆的脸上布满忧伤,涂在手腕内侧的香水,带着宿命的味道侵向心灵。
爱情真是一种折磨,得到与失去同样让人心破碎。
凤凰经过火的洗礼可以重生。如果可以,我愿意在烈火后忘记关于他的一切,从此陌路。她苦涩地笑。夜的世界,没有人在意她的落寞。
忘却是最好的药剂,能让人心归于安宁。
漫长的夜,她不知该去哪里。与他分手,她像迷路的孩子,无法找到回家的路。
他说爱我,可为什么又将我抛弃,让我如此破碎。她轻轻自语。
有人说,女人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来寻找爱情。心爱的男人才是自己的家,其他一切都可以是过往。
夜风裹着薄薄的冷吹起她的衣袂,她像被神遗弃在尘世的孩子,眼睛里泪珠滚动。
他从公司出来已是深夜。城市的空气夹杂着阴阴的冷,似乎有鬼魅飘过。
他驾着车缓慢向前。从南到北,需要穿越整个城市。
他一眼看见路边黑衣如墨的她,心弦瞬间像被谁拨弄,发出重重颤音。
她怎么会如此孤单。脸上的忧伤不是诗,是刀,正欲割裂她的灵魂。
他有拥她入怀的冲动。她只是一个路人。一直理性的他被自己荒唐的想法吓了一跳。但他停下车,打开车窗问:你需要帮助吗?美好的男人声音。
她看见他脸上温暖的笑。孩子般的笑,让人想去接近。可她此时毫无心情。
你像神落在尘世的一滴眼泪。他看着她的眼睛,很认真地说。
人都是神的眼泪。经历了飞舞后,终要归于尘土。她似笑非笑地答。
灯火下,她别样妖娆。寂寞的美,带着毒。
他轻轻笑起来。梧桐的叶子在风里摇曳。这是美丽的春天。
他说,让我送你一程如何?
她看着他,这一张平凡的脸,为何似曾相识。她忽然很大声地笑了起来。
他看见她眼底的哀伤与疲惫。他走下车,把身上的西装脱下来,披在她身上。她没有拒绝。
这是两个都有些莫名其妙的人。他直接,她不惧怕。这都需要勇气。
车依旧缓慢地向前,她靠在座椅上,竟然在很短的时间里睡着了。
他停下车,听她均匀的呼吸。她像生长在深海的藻类植物,睡着都是茂盛的。
她红艳的唇似蝶,在不知名字的香水味道里沉浮。
他开始专注地开车,朝着城市最高的地方行去。如果在黎明前到达那里,他希望可以看见第一缕阳光。
当第一缕阳光抵达时,他听见了一声欢呼。在他们不远的地方一对情侣正在拥抱。他看了看她熟睡的脸。有种幸福在心底生长。
红彤彤的太阳缓缓升起。天空,山峦,河流逐渐明亮。这层次分明的世界,一切原是如此美好与玄妙。
把关于那个英俊男人的一切都付给烈火。如果他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等我和找到我。那说明我要等的和找的人不是他。她坐在窗前看着灿烂的星空,一颗格外明亮的星星似乎在向她眨眼睛。
他是只不愿意停留的船,而我只是他甲板上的客人。她想着挂在他嘴角沧桑的微笑,就是这个男人把自己丢下了。那些誓言此时看来,只是一缕风,曾经吹拂过心灵,在吹皱的心湖上,那些美妙的光阴纹路已锈迹斑斑。
楼下的孩子又在弹奏需要修习的曲子。单薄的技艺将曲子肢解得伤痕累累。
或许她的痛苦的吧。她想。年少的时光是自由和快乐的。
对面的楼层,没有拉上窗帘,可以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子在跳舞,高举的手随着节奏摇摆,一个有些瘦的男人过来搂着她的腰,他们就这样贴得很近的摇摆,似乎这个世界只有他们两人。
电话在桌上欢快地响起来,彩色的信号灯跳跃转动着,在夜的世界像个天使。
你睡了吗?美好的男声。
没有,睡不着。
愿意出来吗?我去接你。
好吧。
她简单把自己收拾了下,镜子里,有些苍白的面容透着天生的冷艳。
在电梯里,她回忆他的面容。
面容是模糊的。不过她记得他美好的声音和挺拔的身形。
在山的顶端,他们站在一块平坦的大石头上望着东方的天空。
他们像一对受到惩罚渴望返回天界的神灵,在天光到来前,用心迎接绚烂的明天。
霞光在天宇飞舞,逐渐明亮的天地像一朵正在盛开的花朵,吐露着迷人的芬芳。
她靠在他的肩膀上,轻声地说,如果一切总是如此美好,我渴望永生。
没有人可以永生的。我只愿自己能在短暂里看到久久长长的美好。
寂静的山谷传来鸟的鸣叫。寺院的钟声在空旷里越传越远。
他们相互依靠着,都感觉自己身处梦境。
他牵着她小小的手在山径上行走,婆娑的光影在风吹叶动间跳跃。一切好像一幅画。
我似乎找到了我想找的幸福。美好的男声在林间轻悠悠地响。
是吗?你相信人的某种宿命?她带着质疑的口气问。
是的,我一直相信我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某个人来的。
你太感性了,这是女人才喜欢做的梦。说给别人听,他们会笑话你的。她轻轻地笑。看我都笑你了。你真得好天真,像个有皱纹的孩子。
如果他们愿意笑,那就尽情地笑。我无所谓。
她摆脱了他的手,在一朵细碎的小花前蹲了下来,用手轻轻地触摸花身。
他在她身后静静地看,心中有水流悠悠淌过。
他会在闲暇时想起她。他喜欢回忆和她在一起的短暂时光。那是一种美妙的幻觉,像酒后的梦。
他正式约会她。她没有拒绝。她知道有些东西不能够回避,需要经历的必须去经历,即使结果是伤痛。更何况那个英俊的男人竟然在她的已经里渐渐淡了颜色。
破败的画作就让风把它带走吧!给我颜色,画一片明亮天空给你。平淡的面容,坚毅的表情。他像站在尘世的一株树,仰望着无垠的天宇。
如果能在他的树阴里看夕阳西下,有清风、鸟声与我作伴,我想我是幸福的。她看着他的眼睛暗暗地想。
他在她对面喝一杯浅黄的啤酒。她看着自己面前的绿色茶水,那些舒展开来的叶子在水里安静的沉睡。
她去他的房子。整洁干净,全然不像一个独身男子的房子。这是个干净细腻的男子。她微笑着想。
他端一杯咖啡给她。他们坐在沙发上,阳光从西窗飘进来,在茶几上跳舞。
他们在晚餐后坐在沙发上看一部很老的电影《甜蜜蜜》。在转换的场景里,他们一起唏嘘感叹,在电影结束的时候,他们几乎同时叹了一口气。他们相互看着对方,都大声笑了起来。
静。安静。他看着她的苍白的脸,她轻轻闭上眼睛。他的唇落在她的唇上。
他用心将她拥抱,她在他的怀抱里想静静地睡去。
我很困很困,就这样让我睡一会吧。她说。
他用手抚摩着她的后背,让她在自己的怀抱里安静睡去。
她很快睡着了。均匀的呼吸,甜美的笑容。他抱着她望着窗外城市的灯火也闭上眼睛。
在一次缠绵后,他抱着她说,我们结婚吧。我爱你,
她说,好吧。我也想和你一起这样老去。
人生必须经历的大事——婚姻,就像一场演出。只是他们愿意为了自己和家人盛装出演,因为他们彼此相爱。
如果曾经沧海,你还沉在水里,你永远找不到真爱。他用美好的声音读诗给她听。她的心弦被深深拨动,她说,那个深夜,你为什么会停下。
因为你在那里就是为了等我。他平淡的面容上有灿烂的笑。
她将他扑倒在床上,感谢你爱我,我也爱你。让我们一起好好的老去,永远不要厌弃我,好吗?
他抱着她说,我怎会舍得不理你。你是刻在我骨头上的爱,厌弃你就是厌弃我自己。他用热烈的吻封住她的嘴。
美好的夜晚。他们在烈火中拥抱最美的生命相依。
所有的铺陈都是为了故事的结局,就像我们在生命里遇见与经历的人和事都是为了让生命更为完整。
没有经历我们永远不会找到真实的自我与美好的明天。
他看她俏丽的容颜,知道上天给了自己一个美好的完整。在不算长久的生命旅途中,这个鬼魅般美丽的女子将是和自己一起看风景的人。如果可以健康的老去,我愿意看着她花开花落,在月下为她写一首婉约的歌。
只是人生并不像想象中完美。即使你曾经历过苦痛,那也不能挡住它再次叩响你魂灵的门楣。
第二年的秋天,她死于难产,母子皆亡。
她在看他最后一眼时,从眼睛里滚落的泪滴硕大晶莹,像美丽水晶。
她真是神落在尘世的一滴眼泪。他握着她小小的手,轻轻笑了。
笑得撕心裂肺。
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这是一九七四年发生在解放军某基地通信连一个真实的故事。
通信连座落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山窝窝里,山不高但一年四季都是绿色。山上生长着一种松树,矮小枝茂。松树间隙中,还有一些斑斑点点的杜鹃花,每年四、五月份几场春雨过后便腾地燃烧起来。在小山苍翠的底色上,一朵朵、一丛丛、一片片,如火如荼的盛开着。
与小山、松树、杜鹃花为伴的,是一群兵,他们的绿军装与小松树相映,青春与杜鹃花一起一年又一年闪烁着魅力。
每当清晨,一声嘹亮的军号,唤醒了沉睡的小山,军营就沸腾起来。不过十分钟,操场上便排起了整齐的队伍,列队、跑步、喊操声顿时引来了鸟鸣,让早霞染上一片红晕。
通信连有三个排,一排是三个总机班,一群叽叽喳喳的百灵鸟。二排是载波,准男性的世界。三排结构比较复杂,一个电传班,一个传真班,一个有线报务班。
有线报务班有八个女兵,年龄最大的二十二岁,最小的十七岁。都是七一年那批报训队毕业后一起分到连队里的。班长鄂延娜是青岛人,高大白净。副班长郭红是北京人,一口京油腔。平日里没心没肺、爱玩爱闹的就是那个年龄最小的杨莉了。
杨莉入伍时刚满十三岁,因为不够十五周岁,他的父亲(另一个基地军务处副处长)利用手中的便利条件,在填写入伍登记表时,将她的年龄多添了两岁,这样她的年龄由十三岁变成了十五岁。但年龄是装不来的,杨莉除了在生活上很难自己照顾自己外,就是军事训练上也比别人差一些,报训队毕业时差点被淘汰。
部队的生活是枯燥的,每天三班倒。每一个班次都由总机、载波、电传、传真、有线报务不同的人员组成。班长鄂延娜在考虑值班组员的时候,专门把发报技术不是很好的杨莉和发报技术最好的且年龄也最大的克秀玲安排到了一起,还说这是最佳搭档。
克秀玲二十二岁了,家在开封。初中毕业后,因家里就她一个孩子,没有下乡。七一年她的叔父到河南招兵,就走了后门将她招到部队。她娴静,说起话来细声细语,经常帮助班里的同志缝衣服和被子,人缘颇好。杨莉也非常喜欢她,整天姐姐的叫。特别是值夜班的时候,克秀玲一看到杨莉打瞌睡,就让她趴在桌子上睡觉,查班领导一来,才赶紧叫醒她。
就这样,她们俩个的工作从来没有出过纰漏,克秀玲还因为技术过硬,被评为部队的标兵。
突然有一段时间,杨莉发现机房现有的四台收发报机,克秀玲总是坐在发射团的那个机器上,而且与对方长时间的对话,期间并没有收发报文,很多次她还在偷偷的笑。杨莉纳闷就凑了上去,克秀玲将她推开,说他们在练习报务用语。
报务用语是电台与电台之间报务员进行对话的一种特殊电码,由汉语拼音字母组成,只是规定电码中通用的很多被简化了。比如:重复(cf)、同意(ty)。报务员运用报务用语将其发送出去,通过音频传送,达到相互之间的沟通,完成了电台与电台之间的联系。
那一天早上,轮到杨莉整理内务。待全班同志都出早操后,她开始扫地、抹桌子、整叠被子。就在平铺克秀玲的床单时,感到有凸处硬硬地,杨莉便揭起褥子看,原来是一个本子。杨莉没多想,随手翻了起来。一看,心跳顿时加快,脸也红了。原来克秀玲与发射团那个男报务员谈恋爱了,他们在收发报机上使用报务用语谈的话,克秀玲都写进了日记里。
那是半年前的一个夜班,克秀玲给发射团发一份加急电报,由于电报的级别比较高,她就发的快了些。对方抄报人漏抄不少,多次请求重复发电码,克秀玲耐着性子均满足了要求。过后,对方向克秀玲表示歉意,当然也记住了克秀玲的发报手法。
以后的日子,克秀玲越来越奇怪,每逢她值班,和她对班的准是这天抄报的报务员。而且对她格外的礼貌和客气。值班时,一般双方半个小时呼叫一次,都是上级呼叫下级。但他们对班,这个下级却经常非常殷勤的呼叫上级。
这一天,发射团的那个男报务员在双方呼叫完毕,克秀玲准备再见时,要求克秀玲抄电文,克秀玲莫名其妙,但还是拿起了笔。随后,那边传来了嘀哒声。抄完后,克秀玲看到是这样的一串拼音:te bie xin shang ni de fa bao ji s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