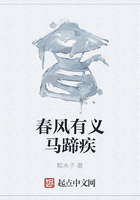两个人的棋力,显然不在一个台阶,但却没有人在乎输赢。
两个人的酒量,也不在一个水平,但也没有人在乎多少。
两个人的身份,更不在一个层次,但却更没人在乎高低。
这就是朋友,真正的好朋友。
这就是兄弟,真正的好兄弟。
儒生模样的男人,面目清秀,五官俊美,肤色如腰间的汉白玉一般,让人感觉很舒服。
此刻正盯着棋盘入神,良久,道:“看样子,这小子此番真弄出事儿了。”
原来,他的心却并未在这棋盘上。
黄衣男子把玩着手里的酒杯,斜依着车窗,漫不经心地看着外边的风景。
原来,他的心,竟也不在这棋盘上。
半晌,淡淡道:“谁知道呢。”
白衣男子伸出修长的手指,懒散的剪着指甲,笑道:“你要是快死了,可别来麻烦我。”
“呵呵……要是你先死了,我肯定送你一口上好的棺材。”
“行啊,就怕到时候你买不起。”
“放心,我管你老婆借钱买。”
“呵呵……你还是好好想想文君的事吧,要是想不明白,死了我都不给你收尸。”
黄衣男子合上双眼,慵懒的伸着腰,似是又要打盹儿。
他不经常这样打盹儿的。
不是他不想,只因他不能。
特别是七年前。
他睡觉总是很轻,似乎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也许更遥远。
他的人很怪,只要和亲近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很困。
只要觉得幸福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困。
或许,这也怨不得他的。
或许,这本就不该怨他的。
两个人注视着窗外的云彩。
很白的云彩。
像极了他们在国子监读书时的云彩。
“我要先回去一趟。”
“哦?”
“我要回家看看。”
“哦。”
“我自己回去。”
“哦……”
起风了。
车厢里并不寒冷。
白衣人却不时的向火盆里添加木炭。
黄衣人也不理他,径自沉沉睡去。
黑暗中,他仿佛看见一袭淡紫色的长裙向自己缓缓飘来。
这长裙是那么的可爱,那么的纯洁,那么的熟悉,又是那么的令人心醉。
七年来,他已不知几百次梦见这袭长裙。
似乎一闭上眼睛,就能如此清晰地感受到她的存在,甚至能够闻到她独有的香气。
或许,这世上,只有他才能闻到这种特别的香气,而每次闻到她,初时都会觉得无比的美好和幸福,而醒来过后,却又只剩下遗憾和难过。
也许,只能剩下遗憾,和难过吧。
这味道,就像是一种,药。
毒药。
一种,戒不掉的毒药。
一种,只有对他才有效的毒药。
情,的确是世间最为厉害的毒药。
两人始终在马车里,倒也落得清净太平。
这一日,两人刚落二十余子,车便缓缓停住。
白衣男子拉开窗帘,眺望远处绵延的城墙,道:“但愿浩然问题不大。”
嘉峪关。
耗费了无数人力财力,历时几代人用血汗铸成的旷世之作。宛如盘龙一般,守护着大明的疆土。
黄衣人感慨万千,他回来了。
毕竟,他还是回来了。
造化弄人。
白衣人见他如此萧索,也只能摇头苦笑。
毕竟,有些事,终究是要面对的。
毕竟,有些事,是只能自己去面对的。
守关的士兵照例散漫地盘查着入关的人。
城门旁已经扣下了二十余个行人。
远远望去,多是些乡下汉子,夹杂着几个衣衫破旧的妇孺和商贩。
不论哪个朝代,不论哪个县城,被为难的,多半尽是些贫困的百姓。
马车驶过关门,赶车大汉并没有慢下来的意思。
却没有一个士兵上前盘问,甚至两个手持长毛的守卫还微笑着目送他们离开。
但这本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无论哪个官兵,都能一眼看出这两匹骏马价值不菲,而舍得用这等良驹套车的人家身份更是不菲。
哪个官差敢去得罪不菲的人家呢。
车外传来一个小女孩凄惨的叫声:“阿爹!阿爹呀……”
不远处,也传来士兵的咒骂声,偶尔夹杂着一个男人痛苦的呻吟和凄厉的哀求声。
白衣人眉头紧蹙,关节作响。
无论是哪个父亲,听到这样凄惨的童声呼唤着自己父亲的时候,都会忍不住怜悯的。
他也是个父亲,虽然他的孩子是个男孩儿,是个从不知委屈的男孩儿。
马车虽已行的远了,白衣猛然道:“老朱,回去。”
这赶车大汉,姓朱。
他竟敢姓朱?
只因当今天子姓朱,早在三十年前就颁布法令,不得平常百姓跟随国姓。
几个士兵正在围殴一个躺在地上的庄稼汉。
周围还散落着几棵白菜。
白菜很新鲜,似乎还能闻到泥土的气息。
只是已然脏了,还印着泥水和脚印。
士兵见一辆马车迎面过来,不由得也是一愣。
见马车奔过来,丝毫没有要停下的意思,心下更是一惊,忙向两旁闪避,列成两队,似是要接受检阅一般。
只剩下一个年纪不是很大,也不是很小的胖子还在用脚狠狠的踢着庄稼汉。
这人不像是老兵,老兵绝不会如此的不识时务。
这人却又不像是新兵,新兵也绝不敢如此放肆。
白衣人下了马车,径直走向呆立在城门的小姑娘。
这小姑娘约莫六七岁,显然是吓的不轻。
白衣人轻叹一声,蹲下身去,拉着小姑娘脏兮兮却又白嫩嫩的小手,慈爱的摸着她的头道:“小姑娘,叔叔带你去找你爸爸好不好。”
这男人的眼睛是那样的清澈,似有魔法一般,只看一眼,小姑娘便感觉到他的善良与宽厚,已完全信任了这个陌生的男人。
白衣人抱起她,转到那士兵的背后,低喝住手。
矮胖士兵本没察觉,被吓了一跳,赶紧回过头来,下意识慌张地抓紧了腰间的刀鞘。
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就好像生命中的习惯一样。
只有胆小的懦夫,才会在一丁点风吹草动下练就这样的招式。
“你!你可知道我姑父是谁么!”
只有更加胆小的懦夫,才会不论何时,都先急着报出某人和自己关系的身份。
但随即瞥见白衣人腰间的汉白玉时,登时面如死灰,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结结巴巴道:“我,我,我我……”
他这一连五六个我字,声音却越来越小,到最后竟小如蚊蝇,早已没了刚才的威武。
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的挪不开半步。
亦或是本就不敢挪开半步。
只有最胆小的懦夫,才会在未交锋前,便吓的失魂落魄,手足无措。
世间的懦夫,不过此三种罢了。
幸好,这世间的懦夫,不过此三种罢了。
但不幸的是,这样的人却做个了官吏。
更不幸的是,不知有多少这样的人,做了官吏。
也许,最为不幸的是,这样的“姑父”,实在太多了。